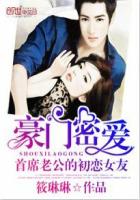“这位员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印堂丰隆、人中端正、嘴唇宽厚,尤其是鼻子,秀而坚挺,鼻头浑圆,乃是少见的大富大贵之相。”
“哦?敝人面相竟这般好?”德荣听得高兴,心中却不以为然。自己逢天变家道中落急转而衰,算哪门子的大富大贵之相?
道士盯住德荣看了片刻,又道:“不过,观员外印堂略显晦暗,两眼无神,怕是新近遇了什么祸事。”
听他这般说,德荣立刻被勾起了兴趣:“道长何出此言?敝人新近并未遭遇什么祸事。”
道士微微一笑:“员外不是刚从吴中一带来京城投亲么?”
“啊?”德荣又是一惊,“道长从何知晓?”
道士笑得神秘兮兮:“山人自会计算。贫道见员外虽然运势一时走低,可观面相确是个有大福缘的人。目下当务之急是禳灾。”
“怎么个禳灾法?”
“禳灾,关节在于禳补受损的福缘,员外若是有意,可随贫道炼丹。贫道凭靠员外的福缘添些修为,员外借炼丹禳补福缘。”
德荣性喜烧炼,今日又是第一回来宣南坊,探访玉虚观只是临时起意,自认与这道士全无交集,见道士张口就能说出自己底细,惊愕之余,肃然起敬,视其为高人。
“只不知道长这丹怎么个炼法?”
“你出劣金,我炼出好银送与你。你得银子,我添道行修为,各有所得,你看如何?”
“道长可否与我演示一二?”
“好说,好说。”道士从案几下的小包里取出几两铅汞,丢进丹罐,然后迅速炽起炉炭,炉膛里块粒状的铅汞很快熔化成了糊状。
道士神秘兮兮地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一个纸包,用小手指甲掏了一丁点白色药末,洒进丹罐,随即收起纸包。再看丹罐里的铅汞,咻地一下就变了颜色,成了雪花雪白的好银。
“妙啊!”众看客齐声喝彩,德荣亦两眼发直,脚再动不得了。
道士面现得色,侃侃而谈:“此乃母银生子之法,先取银子为母,多少不拘,用药炼养在丹鼎中。须九转,火候足了,先生黄芽,又生白雪为丹头。启炉时,扫下这些丹头,只消一黍米大小,便可成金成银,母银却是不少分毫。”
德荣心动,询道:“那要多少母银?”
“母银越多,丹头亦越多越精。”
“如此…….”德荣虽然心动,却不禁踌躇了。些许银子他还有些,但刚到京城,人生地不熟,没有地方炼丹。女婿那边铁定不允每日家中腾云起雾,儿子更是视烧炼为洪水猛兽,就算随这道士学艺,也应从长计议。
“敢问道长尊号?”
德荣抬头询问,他心有旁骛,打算先问清楚道士来历再作计较,但他的目光很快被另一个人吸引住了,以至于道士报上的尊号完全没听进去。
那人年约五旬,身量长大,体格壮健,虽苍髯花发,却面色红润,气色极佳。看容貌,年轻时必定是个俊俏人物。他头顶赤帻,包住圆大的发髻,可见发量颇丰,穿了一身素净的白色葛布衣裳。他不知何时出现在围观的人群中,宛如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
这位老人,德荣认识。
就是初到京城那日,在澄清坊和东长安街交界口处,自己乘坐的马车与对方乘坐的马车险些撞上。剑拔弩张时,还是这位老人主动示弱解了尴尬。
德荣见对方人物风流,当时就起了攀交之意,只是各奔东西,,引为惆怅,竟不想今日又在这玉虚观偶遇。
老人站在道士身后,垂眸朝丹罐里瞅了瞅,带着浅笑摇了摇头,一言不发。这举动落入德荣眼里,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虽然不知老人摇头浅笑究竟是何用意,但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是对道士的肯定,这使得德荣又瞻前顾后起来。
尚不等德荣理出个头绪,那老人有了动作。但见他一言不发,又是不屑地一笑,再手一背,昂首离去。
德荣见状,不假思索,下意识一抬脚就跟了上去,直惹得道士在身后“哎哎哎”气急败坏地叫唤。
“这位兄台,敝人这厢有礼了。”德荣紧追了一引路才赶上老人,冲着对方的背影深深一揖。
老人显是以为德荣在唤旁人,脚不停留,继续赶路。德荣只得又紧赶几步,上前恭恭敬敬道:“前面这位兄台烦请留步。”
老人终于止步,回过身来,上下打量了德荣一番,确认并不认识对方后,脸上浮起不解的神色。
“敝人袁德荣,见过先生。”德荣三度见礼。
“老朽有礼了。”老人拱手还礼,问:“老朽可与阁下相识?”
“不识。”德荣满脸堆笑,“敝人初到京师那日,在内城险些与先生的马车相撞,今日又在此地偶遇,也算是有缘。”
“你……”老人略略一怔,但很快就忆起当日的情景,亦不禁莞尔:“原来是你。”他轻抚长髯,含笑而视,但看起来并无要通名报姓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