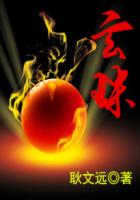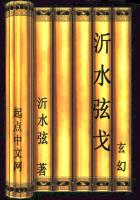在汪家嘴人的记忆中,永远都不会忘记五年前的那个下午、也就是汪木元出道捡垃圾卖为生的那个下午。
这天下午,天气还不太热。
一个头戴大草帽、身背拾破烂背篓,走路一靸一趿的矮个子老头,走进了“诺尔你”的慈竹林盘。
坐在歪颈子酸枣树下看报纸的“醉秀才”,扫了一眼来客。立马起身,微跛着、踉跄着,以他独有的步伐向前一拱,立定。惊呼:“汪木元同志,你当真去捡垃圾卖啊?”
来者取下头上的大草帽,搧着风。“嘿嘿”两声哈笑,“捡垃圾卖丟脸啊?我捡着很多尚好的苹果......”言罢,从背篓里拿出两个苹果,双手递给“醉秀才”。
“醉秀才”一见那脏兮兮的苹果,连连摆手。“不想吃、不口渴,我有茶水......”
“将才,你说啥子话喃?看不起我,认为我不该去捡垃圾卖?没得办法,我只有这个本实。”
“什么话?没有那个意思......”
“四川人都说啥子,你一个人偏要讲什么,陕西骡子学马叫。”
“大家都在说普通话刚才、刚刚,唯独你‘木沙罐’一个人说将才、将才......”
“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乡话说不得了?一方一俗。”
见他二人在扳嘴劲,从公路上走进来一个腆着肚皮的大汉,浑身的肥肉在汗水里颤抖。“吃胀倒了,有精神多想想怎么致富。”
“我就是不想说啥子,啥子和傻子是一个音,说得心里不安逸。”“醉秀才”辩解。
“安逸”是个见不得闹热的角色,飞跑过来。搭讪:“管他是啥子还是傻子,只要锅儿里有肉煮,就安逸得板澡。”
汪木元瞟了“安逸”一眼,“遭球喽,不能嗨在这里,捡不着破烂,锅里没有米煮。”
“安逸”扰兴犹酣,指着他三人。“一看,就晓得谁是当官的——头大耳朵肥,就晓得谁是当官的。”
“说哪样的歪话?我长得胖,是我身体健康而心情欢喜。吔——康而喜?我就用这个绰号。”嚄,他给自己取绰号。
嘻嘻,好耍。
“等于零”在一旁哭丧着脸,“我和他相比就像一具僵尸。”
“带宝”是个弱智者,时常说出一些高一句矮一句的话,让你半天想不清楚。
此刻,他拍拍布满垢泥的光冬冬身体。训斥:“你潲皮、倒炉子,人家是支书哒,当然要吃得肥而大胖。你干筋筋,痩壳壳,一顿要吃两缽缽,哪有那么多东西给你吃?”
“毛子狗”捏着长牌从那边扑过来。“一付贼相、二讽二讽的‘木沙罐’,当真去当伸手大将军啊?”
接着,从牌桌那边又扑过来一群人,这些人纷纷将长牌、扑克牌、麻将扣在牌桌上,一起跑过来讪趣。
不过,这些人比较文相。齐声呼叫:“老祖祖,捡垃圾卖好耍么?”
“老祖祖,捡垃圾卖一定好耍得板澡?我说对没有?嘻嘻......”“哈包”尽量做出一付哈痴痴的表情,扭动着干痩瘦的身子,慢悠悠地晃动着她的痩脸痩脑壳。“当真说对了?”
“哈笑”“咯咯......”抖出一长串银铃般的笑声、又像鞭炮在空中炸响。“老祖祖,捡垃圾卖翻梢了,捡到两个烂苹果只请你们党员吃,不请我们老百姓吃?”
“请你吃,你吃。”汪木元真的选了两个稍大一点的苹果,递到“哈笑”手里。
“哈笑”一看那递到手中的脏兮兮的苹果,就像捧着一堆屎一样,急忙塞给身旁的“哈乐”。
“哈乐”更像火炭到了手里一样,撒开五指,那两个苹果“噗”地掉到地上,滚了很远。“茣当金包卵,两个烂苹果!”他故意乐得双脚一颠一踮,结起舌头乱说,
“吃、吃不得,这东西吃了要生儿,哈哈儿就要生、生出来,**都要屙肿。”
“哈哈......”
“嘿嘿......”
“嘻嘻......”
众庄客嬉笑扰乐,前俯后仰;哈笑万声,笑倒山庄。
汪木元勃然大怒,“爱吃不吃,别拋洒神物。看不起老子,老子还看不起你们,一天到晩都在哈笑。”捡起那两个苹果,背着拾破烂的背篓,一靸一趿地要走。
“诺尔你”拦住他,鬼眨着眼睛,尖起他老鸭公一样沙嗄的嗓音。“老祖祖,你猜我要说那样的话?嗄嗄......”
“事不关已,让你的锅儿吊起。”汪木元走出两步,扭头又补充一句。“你去看看,你老娘的锅儿吊起没有?”
“啊唷,老祖祖......一个党员怎么这样对待老百姓,你知道他老娘的锅儿
吊起在当钟打?铛,铛......”“大惊妖怪”极兴致地编排、表演着,扭动着肥胖的身躯,一伸颈一缩脖,一眯眼,转圈,双手在头前鼓掌,弄出来特夸张的表情。
“小惊妖怪”一抿嘴,“嘻嘻,老祖祖捡垃圾听了很多神话,变精灵了,晓得挖苦我们了。”她摇晃着那颗美丽的头颅,笑得左边做揖右边打躬,泪花飞溅。
“烂嘴巴”阴着脸,还没有来得及表演,汪木元巳经远去。
“啬家子”板着面孔。训斥:“你们这些年轻人只晓得过嘴巴瘾,他虽然是个‘木沙罐’、是个二讽二讽的人......骨头里硬气得很.”
退休的八字先生“二神仙”,谁也不怕,他不仅有钱还有人势,他给许多当官的都算过命,万一他把谁家的酸菜坛子踢翻,有人给他撑起。另外,他的小女儿在官场也混得可以。
他十分响亮地喷了一下鼻翼:“他可是老祖祖的辈份,对老祖祖不能吊二啷铛。哈笑万声,不知究竟,你们真是汪家嘴的五精灵噢!”
“醉秀才”、“钟老咬”、“想幸褔”、“我文明”几兄弟在一旁铁青着脸,无言。
不知何时,支书兼村长的“康而喜”已经回到他的福宅,在小二楼上看见这些情形,慢僈转过身去。
说我疯说我痴,世人笑我看不穿。这是哪部电视剧里的台词?
汪木元是个“满心蹄”,走得一靸一趿,走路却始终拗起个脑壳——你们看不起我,我还赖得理你们。老子是老共产党员,虽然没有水平,思想觉悟比你们高。饿着肚皮也应该去帮助别人,捡着两个烂苹果也应该请人分着吃。再者,我是老祖祖的辈份,未必还向哪个低三下四!
特痴特儍,他是不是患有精神上的神经病?
三伏天气,虽然新兴的资阳市区的各条街道上,花园处处,小榕树、法国梧桐树绿蔭蔽日,仍然十分炎热。
正午时分,街道上行人尤其稀少,甚至沒有多少车辆行驶,绝大多数的居民,都躲在家里享受电扇或者空调。老天爷似乎患了神经病,大地像扣在蒸笼里一般闷热。
唉,这热死人的天气里,日子实在难过。
唉,热得不行了,干脆跳到河里淹死算了。
这是刚才发生的故事。
这位头戴破草帽,身高四尺,靸趿着脚步的丑老头,背着一个拾破烂的背篓;右手拿着一根穿插废纸类的小钢钎,左手提着一个雪碧瓶子,走几步就要喝一口,那不是可口的雪碧,而是带着消毒味儿的自来水。
他亍立下来,扯下斜搭在肩上的汗帕子,闭上眼睛,忙去擦拭那溢漫到眼角的汗水。之后,又弯腰挤捏这条发黄变硬的汗帕,脚旁立刻积下一滩臭烘供的汗渍。
他蹙眉四顾,多么巴望着哪个行人、或者从身旁驶过的汽车里,扔出一个或者几个易拉罐、饮料瓶......嗨,就发财了!家里的几口人就能吃上一口饭了......
来到一家中型的中餐馆。他喝干了最后的一口自来水,拗着头,摇晃着他的短小身材,靸趿着脚步进了这家餐馆。举着雪碧瓶晃了几下,示意讨口水喝。一位漂亮的十七八岁的服务女生拦住了他。
“爬远点儿,一身崩臭!”
听到这“一身崩臭”,他觉得受到天大的侮辱,脑壳里不晓得哪根神经在抽搐。
“呯”将烂背篓往地上一惯。“将才,你说的啥子话喃?啥子叫一身崩臭?说清楚点儿!看不起劳动人民,你老汉是不是劳动人民?咹?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点精神......”
看见这个丁点儿高、拾破烂的老头说话如此激昂,餐馆里所有的客人都乐了。
“啧啧......不简单,一个拾荒者会背诵***语录。”一位小老板模样的中年人,脸醉得像猴子的屁股般殷红,端着酒杯走到他身旁。“你当真会背诵***语录?整两口酒,再背诵两段***语录,怎么样?”
他伸手挡开酒杯,“背就背,未必害怕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我们有了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背诵得好,整口酒......”那人笑眯眯地问。“你是啥文化程度?”
汪木元伸手夺过酒杯,一飲而尽。笑笑:“实在口干了。文化么?大字摸摸黑,小字认不得。那阵儿,努力诵***语录嘛。”他憨憨地笑着,没有了刚才冒火的气息。
众人捧腹,忙着将嘴对着地面,生怕嘴里的饭菜喷到对方脸上。
“你当真是党员?”那人又斟了一杯酒端过来,脸上露着几分讪笑的神情。
“将才,你说的啥子话喃?不是党员?咋样?——捡破烂又咋样?不是偷不是抢,革命分工不同,劳动光荣!”他拗起个脑壳,目瞪对方。
“哦噫,老牌子的共产党员,难怪这么高的觉悟。”那人酒醉兮兮的脑壳鸡啄米似的点着。
人们不笑了,像是在思索什么,有人在摇头,有人在点头。
“哪个山花子在这儿扰乐本店经营?哈哈......‘木沙罐’,几百年没有见着你喽!干上拾破烂的工作啦?”
“拾破烂?你的耳朵放牛去了?将才,这一位老板说的——是拾荒者,把大家丟了的东西,收集起来,支援国家建设。‘黑煤炭’当上大老板呀?”见了这个人,汪木元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啥球大老板,是我的儿子开的中餐馆。”被叫着“黑煤炭”的老者应喏着,并夸赞。“你觉悟高、太高了。走,我用花茶慰问你......”他才不嫌这个老几一身崩臭,拽着他那脏兮兮、汗漉漉的手,拉到后堂坐下。
在人们诧异的目光中,别提他的表情有多么地得意。
喝够了茶水,吹够了电扇的风,他起身作谢,准备离去。“黑煤炭”进屋抱出一套衣裤,还有一付墨镜、一双大半新的皮凉鞋。恳切地说:“去洗个澡,拾破烂也要摆出一付架式,别潲了共产党员的脸皮。这套衣裤是我儿子的,凑合着穿吧。我是临时来给儿子看店的,他出差了,经后我不在这儿,你也可以来耍。”
“木沙罐”洗了澡。换上帅哥穿的衣服,戴上墨镜,脚蹬皮凉鞋,,一下子感到那么地精神涣发。只可惜,人太短小,裤腿袖口挽了好几圈。
他看见自己拾破烂的背篓也换成新的,别提心里有多么感动,嗫嚅了好一阵儿,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感谢话。
“黑煤炭”姓严名太,其人面如煤炭般黢黑,常常被小青年误认为是非洲人。现任严家沟的村支书,和汪木元同时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当年在县委礼堂宣誓,有人讪笑“黑煤炭”与“木沙罐”的尊容,他俩脸红筋胀地回答:“我们人丑心不丑。”
这句话好象也是一种誓词吧。
踩茅坑的共产党员,这可是汪木元昔日的荣誉。
入党时,他虽然没有创造功劳的能力,却坚持每天早出工晚收工,尽量为农业社多劳动一会儿。难能可贵的事情——他利用早晚的时间,为农业社踩沤了几大坑绿肥。在化肥还是土地贡品的时候,这可是不小的贡献。
可是,土地下户后,他由昔日的收钱户,变成了衣食困难的人。像“安逸”、“毛子狗”那样的补钱户,年关都要找他借钱的人,摇身一变都有钱了。肥猪一群群地卖,蔬菜一架车一架车地往城里拉。“望月亮”、“钟老咬”、“我文明”、“想幸福”等都买起火三轮,往城里销售自己的蔬菜,银水“哗哗”地流来。
不知多少次,他恨自己太木拙:真正的“木沙罐”,喂猪猪发瘟、种菜菜发黄、种粮不够吃。瞎眼的老娘一天比一天衰老,一场病下来要用很多的钱,信用社再也不贷款给他。
“毛子狗”更是人前人后地挖苦,“贼样的,‘木沙罐’老祖祖,哪天去当伸手大将军,别忘记带上我;你是党员,讨口也要带上我......”
他蒙上被子哭了三天:我潲党员的脸皮喽!
眼看就要揭不开锅,瞎眼的母亲叹息:“木儿,怎么办呢?唉......”
最后,他一跺脚,咬着牙说:“饿死才被人看不起,去捡破烂卖,没有啥好羞的!”
从那天起,背上拾破烂的背篓,已经整整五年。
嘴上说不羞,至今,他都头戴大草帽,见了汪家嘴的人远远地躲着。
眼前。
他的眼睛为之一亮:看见服务员把一盆一盆、没有吃完的东西倒进潲水桶,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动过。他急了,“老朋友,你好事做到底,把倒进潲水里那些东西送点给我,我有重要用处......”
严太得知他的重要用处后,特地用一只熬制鸡湯的瓦罐,盛了一罐高挡的残湯剩汁。把他送到大街上。叮嘱,早些时间收工,天热,恐怕这些东西变味。你......每天下午都来这里,我把东西给你准备好,我回家去了,也叫我的儿子给你准备一点东西......”
望着他那走的一靸一趿的背影,严太久久地拄在那里感概。“光荣呀光荣......如今做这种光荣之事的人已不太多唷!”
莽苍山麓,柏树成林,葱郁蔽日。
飞走的麻雀飞回来、白鹭飞回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群群竹鸡,这种鸟酷似斑鸠,,羽毛比斑鸠漂亮,但不像斑鸠那样胡乱地“咕咕”。遗憾的是与麻雀一道飞走的喜鹊至今不想飞回来。
莽苍后山
也就是落魂崖这个方向。与娇子大道的结合处,有一条通往汪家嘴小平原、汪家坝村,到太平镇的公路。这条公路蜿延着从“诺尔你”的慈竹林盘外通过,站在公路上,远远地能看见落魂崖、落魂潭的风景。慈竹林边还有一株歪颈子酸枣树,这株酸枣树的对面,延伸出一条水泥铺设的小公路。
这条小公路从幢幢小二搂、小三楼的小花园前经过。
一块宽约八丈,长约五十丈的荷塘横在这些楼房的前面,风景煞是无限。这块荷塘是村长兼支书“康而喜”经营的,今年才从省农科院引种、种植。
美名:“带花长”良种藕。初夏时节就荷花绽放,远远望去,碧綠苍翠中似桃花粉彩,簇立着许多婷婷玉立的仙女。
塘中立着一块丈余高的木牌,上书:支书“康而喜”示范——观光荷塘。
这块观光荷塘,不仅给“康而喜”带来经济上的未来之喜,也给汪家嘴村民带来神韵般美妙的蛙声。
夜色降临,蛙们、干蜞蚂、癞蛤宝、蟋蝉等,天然音乐团的成员,给人类奏出了最合谐的音乐。让人们枕着这音乐,进入安逸、舒服、巴适的梦乡。
当然,“康而喜”的梦比别人的梦更香。
乡村的夜晚,蛙声、虫鸣遮掩了一切。
这些小二楼、小三楼分别用褚色、绿色、白色、黄色、奶油色的磁砖、或者马赛克装饰外墙,地面都镶着彩色的地板砖,白色的内墙上油着许多中外壁画,让人目光诧异。
这些小楼的庭园里分别种着姿色迥然的花草:月季皇后、美人蕉、一串红、凤仙花、海棠花、杜鹃花,还有叫不出名儿的家花、野花。
仔细一看,还有道景色令你大吃一惊:这些小楼的大门旁都挂着一块红漆牌子,长约四尺,上书黄色字体。例:“舒服”、“安逸”、“醉秀才”、“钟老咬”、“望月亮”、“想幸福”、“我文明”、“黄南瓜”、等。
即使不大受听的绰号也仍然挂牌不误,如“大惊妖怪”、“小惊妖怪”、“哈包”、“哈笑”、“哈乐”,不过,在这些牌子后面添上了“之家”二字,画了一张大大的笑脸,弄得像个俱乐部似的。
这些人家的老爸老妈不高兴了。“好人不当,当坏人。”
“哈笑”的老爸“箩篼客”,指着牌子怒叱:“哈笑之家,我们一家人都在哈笑么?”提着扫帚要打“哈笑”。
“哈笑”跑出几丈远,笑弯了腰。“爹噫,这不是找乐趣么,说明我们一家人爱笑,心宽嘛。一笑多活二十年......打个哈哈活百年!咯咯......”
支书“康而喜”,挂了一块镇政府一样大的牌子,上书“康而喜”之家。他当官的都敢挂这种牌子,气得散居在公路对面的“毛子狗”、“烂嘴巴”、“老鸭婆”也挂出自己不大体面的牌子。一看,就是又歪又恶又不剃脑壳的人,谁敢欺负?
“诺尔你”挂的牌子最响亮:“诺尔你嬉笑山庄”
弄得三沟五岔的乡亲跑来观看,新闻记者也前来采访,问其原因。汪家嘴人异口同声:“嘻笑快乐吧!”
汪家嘴小平原,是镇上、区上的蔬菜产业区。尤以“红沙番茄”酸甜适中、细腻化渣,遐尔闻名;“红沙罗卜”也很受欢迎,富含丐和磷,十分利于老人和孩子的骨骼健康,也利于消化与止咳化痰。
然而,当成渝高速公路通车后,反馈来的现代文明的信息,让汪家嘴人变得躁动不安起来。
——夜晚,仰看着汽车总站和十九层高的广电大楼上,那闪烁着的七彩灯光、以及高速公路上如龙游般的车灯,他们彻夜不眠。
白天,人们不自觉地汇集到“诺尔你”的慈竹林盘里,嬉笑扰乐、喳天冒古、惺尔河山、不亦乐乎,急急殷殷地期盼着:汪家嘴哪天被开发,这里倾刻间变成城市,让大家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爱“鬼眨眼”动作的“诺尔你”,把自家那块“诺尔你嬉笑山庄”的牌子,挂到了歪颈子酸枣树上,让这里名正言顺地成为“嬉笑山庄”;他把来这里打牌、吹牛、惺尔河山的人通通称为“扰乐庄客”,并自封为扰乐庄主。
更具特色的还是“舒服”家的风景。
他是个发迹的生意人,买两辆“富康”轿车请师傅打的,自己在家里当老板。另外,还购了一辆二手的白色桑塔娜代步游玩。
他的打扮与众不同,屁股上挂了一个“大哥大”,哪怕热得只穿火腰裤,也要把“大哥大”栓在屁股上一甩一甩的。很多人都在一夜之间玩上手机,他还特显他的“大哥大”,哪怕这个大哥大已经功能不全,哪怕手机就揣在裤包里,“大哥大”照挂。
他的“天天红”小花园,只种红色的花:月季皇后圈着海棠花,杜鹃花、一串红,红色的美人蕉。
嗨,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花类种种。
他的口头禅令你哭笑不得,无论别人是哭还是在笑。
一见,首先问人家:“你舒服么?”,然后补上一句“非常舒服。”
还有让你稀奇的,他如法泡制,独具匠心的调教了两只大鹦鹉,鸟儿吃饱了、喝好之后,在大大的鸟笼里高歌。一只问:“你舒服么?”
另一只回荅:“非常舒服!”
也不知道这两只鬼鸟哪有这么好的精神,一天到晚都重复着这两句话。
遇着隔壁邻居老子和儿子拌嘴,男人和婆娘角逆扯筋,这两只鬼鸟也在鸟笼里扑腾着翅膀,一前一后地问责。“你舒服么?”、“非常舒服!”
有一次,“黄南瓜”的老爸“弯脚杆”感冒了,叫儿媳妇吴艳艳倒点儿开水吃药,她没有动作,气得“黄南瓜”搧了她一巴掌。
吴艳艳惊叫唤,两只鬼鸟也跟着惊叫唤。“你舒服么?”、“非常舒服!”
若不是“舒服”的“憨老爸”挡着,“黄南瓜”提着鸟枪要除害呢。
“你又不是雀雀,何必跟雀雀一般见识,我都听朽了,叫得老子点都不舒服。”
然而,小公路前行七八十米的转弯处,却有这样一户人家:三间茅屋倒了一间,其模样就像匍伏在地上的病牛。
这就是“齁包婆”刘翠华的家,蜷伏在幢幢小楼的夹缝间,真是天可怜见。
这破茅屋的后墙不远处,就是温柔的紫沙河,顺着河堤走捷路,也能走到她的家。
这光景,与之周边,氛围实在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