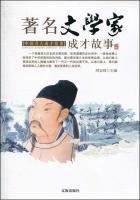这个当下的悲催的爱情故事从这里开始。
这是十多天前,紫沙河边,出现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裤腿挽到膝盖,手持一根小竹杆,打捞着从上游漂流下来的,别人洗菜时废弃的莴笋叶、白菜叶。
有时,她要弯下腰,发出一连串的咳嗽声。
紫沙河上有坐小桥,由四块水泥预制板拼结起来,做为村民耕种的机耕道。
来到距离小桥二十多米远的落魂潭边,她迟疑着不敢向前走。她听说这潭里淹死过孩子,还有恐怖的传说——这潭里有妖怪。
但是,看到有那么几片莴笋叶在水里旋转着,这几片莴笋叶还很嫩呢,一定是洗菜人不小心被河水飘走的。用这几片嫩莴笋叶……给妈妈煮一碗菜汤喝多好呀!
妈妈快死了……
只见这位小姑娘,用竹杆在水里试着深浅,一步一步地往前挪着,用小竹杆比划着,还是够不着那些旋转着的莴笋叶,又向前挪两步。嘴里嘀咕:“向前、再向前、一点儿……”
眼看着那几片莴笋叶就要被卷进漩涡中,小姑娘一急,往前伸探出身子。就在这时灾难发生了,她失去重心,跌进深水里。只扑腾了几下,这个昨天晩上,只吃了几口冷稀饭的孩子,就这样,在落魂潭中漩转着往下沉……
大哀哉之歌响起
心欲碎
泪涟涟
小小菜叶水中漩
是谁是你夺走她
恨只恨苍天无眼
唏嘘大地缺情寰
心欲碎
泪涟涟
命如菜叶水中漩
向谁呼救
向谁求援
快来人啦
心欲碎
泪涟涟
救命啊
小小人儿沉深潭
一命呜呼见罗阎
哀哉哀哉大哀哉
晌午,在田园里劳作的人们,以及“诺尔你”嬉笑山庄的扰乐庄客们,都回家吃午饭去了。
四野空空无人。
从河对面的一个小小的山坳里,走来一位手提洗衣桶,身材四尺来高的小老头;走路一靸一趿的,却拗起个脑壳,扁脸扁嘴,表情带着几分木然的傲气。
他过着与汪家嘴人隔绝的生活,人们不搭理他,他也懒得搭理他们,更不知道汪家嘴发生的种种亊情。五年来,每天上街捡垃圾卖还是捡垃圾卖。
他的老母亲,患流行感冒,咳嗽得十分厉害,还发着高烧。今天,他在家服侍母亲。
这会儿,已经走到河边喽。他要到落魂潭边去洗衣服,汪家嘴人忌避这儿的阴气,他却不怕。并嘲笑:神经有毛病,这么清凉的水不敢来洗衣裳。
莫非,你——就是这位小姑娘的救星?别走得一靸一趿的,加快你的脚步吧!
他远远地看见,一个小孩在落魂潭边用竹杆打捞着什么。走近却不见人影,揉揉眼睛细看。“唷,将才都看见......人那儿去了?”
举目寻找。
只见那只装着几片烂窝笋叶、白菜叶的畚箕还放在沙滩边,不由得神色紧倒,吸了一口冷气。定睛细看,在落魂潭的入口处,有一个小孩在水里漩转着,眼看就要漩进深潭。
他急了,步伐靸趿却如飞,扑进水里,在水里连扑两圈都没有抓着小孩。他的水性也不行,呛好几口水,才抓住小孩的脚,把她拖出深水。他认出来,这是汪家嘴刘翠华的女儿刘小华。
见小华已经昏厥,他急得拍打着自己的胸脯。“我怎么不早点儿来这里洗衣服?早点儿来救人,这苦命的娃儿呀!”
他想起:人们把落水的小孩放到牛背上吐水的做法。
急忙将小华抱来倒伏在河堤上,并给她揉着肚子。
一会儿,小华“哇”地吐出许多清水,稍后又“咳咳”吐出许多痰来。朦胧中,认出救她的人,是被大家叫着“二讽二讽的木沙罐”。
柔柔眼睛,站在眼前的,仿彿是一个青年人,只有青年人才会不要命的来救她。懂亊的她,踉跄着,跪在河堤上,给他连磕三个头。啜泣:“汪叔叔......谢谢你救我的命。”
停顿稍许。
看清楚了:救她的人,确实是被大家叫着“二讽二讽的木沙罐”。又嗫嚅着问:“称呼你汪叔叔,不会骂我吧?”
汪木元“嘿嘿”一笑,“将才,喊我啥子喃?把我喊年轻喽,我才高兴喔。”
他看着小华那黄瓜皮似的脸色。心想:这娃儿怎么这样痩?瘦得一身光骨头,轻飘的要被风吹走......
小华的身体摇晃着,去沙滩边,端起畚箕向前走。向汪木元凄憷地笑笑,又一次说,“汪叔叔.....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我要回去给妈妈煮菜汤喝.....”
这个笑容那么地天真,又显得那么地悲凉,更显得那么地无助,眼角分明泌着夺眶而出的泪。一个刚从黄泉路上回来的小孩,立刻想到,她那垂死的妈妈等待着喝她煮的菜汤......
她跌倒了,那只装着几片烂菜叶的畚箕甩出去很远。
汪木元上前扶起她,把那些烂菜叶拾进畚箕。疑惑地问:“小华,将才、你说......你要回去给妈妈煮菜汤喝?”
小华又一次跪在地上,泪水从她那皮包骨头的脸庞上,一波一波地往外涌,无声无息......
“你们母女到底怎么样啊?”看见她这样的表情,汪木元似乎明白稍许,心里不由得一紧,“你妈妈病得很严重啊?”
“汪叔叔......我妈妈快要死了,她三天没有吃饭。齁包病又复发,外加流行感冒,齁喘声就像打雷一样响。她真的要死了,呜呜......”说到这儿,小华再也忍不住,放声痛哭。
虽然是痛哭,对于这个昨天晩上,只吃了几口冷稀饭的孩子,她的哭声又有多么响亮呢?
“将才,你说啥子话喃?怎么不请‘光亮’医生,给你妈妈治病?”
“呜呜......妈妈不让我去请,说、说欠他太多的药钱。噫哽......”哭了一会儿,又补充说,“我也不敢去学校,怕老师追问学费......”
“不请医生看病,你妈躺在床上等死啊?你......还小,还要读书,还要长大呀......嗯唷......”汪木元也哽咽起来。
“汪叔叔......我们母女还活得下去么?谁来管我们呀?......”
公元一九八六年,中秋节这天,汪家嘴出现了一件令人称奇、羡幕、甚至唾涎三尺的美好事儿。
五八年支援农业的下乡户后裔曾根,在广洲打工,得意洋洋地带回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婆娘。
“钟老咬”、“醉秀才”、“舒服”、“安逸”、“康而喜”、“毛子狗”等汪家嘴人把曾根家那三间茅屋快挤破了。
曾根买了几斤酥心榶,举行了一个简易的婚礼,请众乡亲多多关照他的来自远方的奴隶。他说;“我的爱人来自凉山洲会理县的一个小山村,我们是在打工时认识的,并订下终身。名字叫刘翠华,初中文化,父母双亡,无兄无妹,和我一样属于苦命人。敬请众乡亲督促,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
人们一边嚼着酥心糖,一边打量着眼前这位美女,不看不惊艳,一看眼惊闭:
窈窕身姿让人迷
高挑身材眼惊奇
苹果脸型泛红霞
碧桃眼中汪汪水
双眼皮下明月至
樱桃小嘴笑微微
白皙皮肤泛着嫩
胸脯玉影婷婷立
呀,天上飞来金凤凰,天上飞来的大美人儿。
同属下乡户后裔的“钟老咬”,笑着回答:“我们两个难兄难弟,你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你对他不好,弄到我家去——我供养。”
“毛子狗”也举着手说:“要得,这么漂亮的婆娘谁都想供养,我也报个名!”
他翘着的二郎腿抖两下,“我看见美女就头昏眼花,看见美女就分不清东方西方。”
三十岁的“舒服”,扁扁嘴,你们的老婆还要请我供养,敢去打别人老婆的主意?”
“瘦大嫂”、和“二百六”立刻凑过去。“今晚上我们就要你供养,你娃娃娃不哭才怪......”
“安逸”比他们要年长一些,不好意思说得太痴,还是嘻皮笑脸地湊上一句。“各人抱着各人的老婆不闹才是万万褔......”并用眼神瞟瞟他的老婆“胖大妞”。心里说:我的婆娘也很漂亮噢。
是的,那时的汪家嘴人还很穷,供养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成问题。
经过自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辛勤劳作,过年那天能杀只雄鸡公,割上几斤肥片子猪肉,打上几斤烂红苕酿的酒喝喝,就非常的阿弥佗佛。谁还敢打别人老婆的主意,请你坏都坏不起来。
穿着旧军装的“醉秀才”,一言不发地吃着糖、喝着酒,严肃无比的样子。
曾根的父亲、母亲都死于饥荒的年辰。他也无兄妹,自称苦命人。
第二年的六月,小华来到人世。夫妻俩诀定不外出打工,好好在家抚养孩子,供她读书,希望女儿将来有个好的前途。
然而,芸芸众生中,有的人的命运就在眨眼之间,坠入苦难无限的深渊。
五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曾根去城里卖菜,大雾之中被一辆狂奔的小车撞死,车主逃逸。
当时,刘翠华正患重感冒,气急攻心,昏睡多日,高烧多日。由于无亲无戚,也就无人照顾其病痛。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太漂亮了,“毛子狗”对她的姿色早就唾涎三尺。
正直的“钟老咬”也不敢接近。有一次卖菜和她夜晚才归,引起诽议,曾根还盯过他的捎。
所以,为避遭闲言碎语,人们选择远而亲之,最终在人们冷漠的关心下,落下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被人称之为“齁包婆”。天气骤冷骤热时,其齁喘之声尤如闷雷轰鸣。
但是,她却郑重地向世人宣称:从此不再嫁人。而且把小华的随父姓改成随她姓,一定要把年仅八岁的小华撫养成人。对于一个患严重支气管哮喘的女人来说,别提生活有多么艰难,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女儿上学的费用竟然靠饿着肚子,去变卖那点儿可怜的口粮......
在泣血中呻吟
苍天,这里还有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儿。
在汪家嘴一幢幢小二楼、小三楼拔地而起,大家开始享受小康生活的时候,在人们的欢声笑语震天价响的时侯,人们似乎忘记了他们母女俩的存在。
又有谁伸出援助之手呢?又有谁挺身而出,把扶危济困当着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你也许没有饿过肚子,不知道喝着凉水渡日是什么滋味;当闻着从别人锅儿里飘来炒肉的香味时,心里饥美着能吃上一块肉该多好啊!倘若当真有人给送来半碗回锅肉时,所表现的不仅是声声谢语,而是在心里一遍遍叨唸:好人呀好人呀!
寒风在空中肆虐,空野奇冷无比,无人行走。
天色变得十分惨白,没有一丝生活的气息。
刘翠华挑着半担粪水,彳亍难行,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把颈引向天空,长“嘘”一声“喔哟”,重重地喘息一会儿。又重新启步,粪桶里尤如有鲤鱼在跳龙门,粪水射出老远。
“妈妈,歇一会儿......歇一歇再走。”小人儿肩上扛着舀粪水的瓜当,一步一趋,陪伴在母亲的身后。见她这么艰难,抽泣着:“菩萨呀......保佑我快些长大,长大好供养我的妈杩!”
停了停,小华象想起什么似的。“妈妈,这么难受,不用去地里浇麦苗,买尿素肥料来撒,别人都是这样做的。”
“女女......我们哪有钱去买化肥,又有谁肯赊钱给我们,你看人家的麦苗又青又壮,我家的麦苗又黄又小......喔哟......二天我们吃风呀。”
在这寒风加小雨的天气里,这一病一小,一步一挪动的身影,哪里是寻求生活呀,尤如是奔赴他们生命的刑场。
煮晚饭时,小华向妈妈央求。“一天都没有吃饭,饿惨了......多加一点儿米。”
“不能呀......每一顿都要省下一点米,卖了给你交学费。今天两顿合着一顿吃,多削一根红苕、多加一碗水......捱到我女儿长大,日子就苦出头了......”刘翠华背靠着墙壁,喘息着,说着安慰女儿的话。“唉......趁我现在还能动弹,一点儿不能能动弹的时候该怎么办哟......”
这忧愁而绝望的话语像针一样刺进小人儿的心里,她不禁一个寒颤。
“老天爷,咋兴这样对待我们母女......”
灶门,火光映照、映照着她那张稚嫩、凄苦而又乞盼着什么的脸庞,串串泪珠洒落。
----她还是一个只有八九岁的孩子、应该什么都不懂得,只知道饿了要吃饭的孩子、只知道躺在父母亲怀里撒娇的孩子,然而命运的摧残,竟让她幼小的心灵感到撕肝裂肺般地疼痛。
“女女......不哭啊,要坚强!......”
“没、没有哭......你看,我在笑呢......”小华扭过脸来,一脸的泪花飞瀑。
这一夜,母女俩谁也没有睡好。
怎样才能活下去呵......唉!
“红罗蜜蜜甜,看着看着就过年。”
看着人家的小孩举着双手在欢呼雀跃,看着人家用柏树桠柴薫制着香肠、腊肉、腌鸡的情景。小华吞嚥着口水。对妈妈说:“再过几天就过年了,我好想吃点肉,去街上买点最不好吃的槽头肉肉......回来吃。”
“实在没有钱呀......”
“就买丁点儿,别的人家......挂那么多肉肉、我们家丁点儿都没有......”小华摇着妈妈的双手,乞求着。
刘翠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搂过女儿,滴滴泪洙洒落。“女女吔,钱又不是草纸,天上不落地上不生。嗯呜......”母女俩相抱而泣。
忽然,小华仰起头,揩去脸上的泪,大声说:“我有办法了,有钱去买肉肉啦!”
“有那样办法?”刘翆华吃惊地问。
“砍柏树桠柴去卖,好多人往城里运柏树桠柴,城里有很多人要薫香肠、腊肉。爸爸卖菜留下的小架车我也会拖......”小华俨然如一个大孩子的口吻。
“唉......我也想过这办法。妈妈沒有能力去剔柏树桠枝,你也爬不上树呀。”
“我有办法,把鎌刀绑在竹杆上往下拉割......”
“还是我女儿聪明!”母女俩高兴得互相亲吻。
然而,当她们用尽吃奶的力气,在自留山上,从高高的柏树上割下来的那些树枝,却只能用钩绳綑着,象蚂议搬家一样,一点点往山下拖运。
然而,母女俩长嘘短叹、声声呻吟,用架子车拉运到城里的柏树桠枝,竟然无人问津。因为,马上就过年了,城里人为准备过年的腌制品已经薰制的差不多。
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母女俩拖着这车柏桠枝,一身湿漉漉的,从西门拖到东门。小华哀求似的叫卖着,“谁来做做好事,买走我们的柏桠柴。行行好吧......”
“啊哟,快来躲雨吧!”一位老大娘见她们这么惨象,撑着雨伞跑出来,扶着一步一喘息的刘翠华进了她的家门。
“天可怜见,怎么是你们这样的人弄柴卖?一病一小的......”
“老奶奶,我们太遭孽......帮帮忙,把柏桠柴买去嘛,随便给多少钱都可以。”
“我给二十元钱,卖不卖?”
“老奶奶,你真是菩萨呀,少给点儿钱也可以。”小华高兴地摇着老人的手。“这下可好了,我们可以买一点儿肉肉过年啦!”
“唉,我也是遭过难的人......”老人的表情有些哽咽,付钱时又多付了五元钱。
就这样,在求生存的路上,刘家母女默无声息地熬到了第五年。
听不到她们有丁点儿的笑声,甚至听不到她们母女说话的声音,听见最多的是她们“嘤嘤”的哭泣声。没有人关注她们是活着还是死去,没有人伸出丁点儿援助的手。
小华今年十三岁,瘦壳棱铛的样子,除了一双眼睛忽睒忽睒地亮着,看不出她有多少年少的生机。菜黄色的脸庞上没有一丝血色,有的只是自卑和懦弱。看见别人的孩子吃着糖果、穿着新衣服欢天喜地的样子,她远远地躲着、望着,说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是嫉妒还是仇恨。
在学校里,更是沉默得像一只影子,呆呆地听老师讲课,不与人对话,如果有人欺侮她,便会扬起她那皮包骨头的拳头,从不哭泣。
刘翠华显得十分苍老,俨然一个六十岁的老妪。体力消耗更大,每走一步路,都要发出惊天动地的哮喘声,甚至要扶着墙壁才能走路。
她不知多少次站在破屋外,仰望漆黒的夜空,掩嘴啜泣。生怕惊醒在睡梦中哭泣的女儿,生怕自己伤心绝望的哭泣声让汪家嘴人知道,看她们母女的笑神。
如果女儿能生活自理,自己就可以撒手西去。现在......还不行,她还太小,一个人孤单单活在世上,受了欺侮谁来安慰她。
女女呀,真是太难为你,还要你来供养我。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我们母女能活到哪一天噢!
这天傍晚。
小华放学回家,手上提着一小綑她撬扯的草药,看见妈妈蹲在墙角,呜呜咽咽地抓扯着自己的头发。脚边已扯下一大绺头发,还在使劲地抓扯。“女女......妈太对不起你!”
“妈......扯脫那么多头发不痛么?”小华丟掉手中的草药,伏身去抱妈妈。“我、我长大了,我供养你......别哭,别哭......熬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太阳的......”
这个星期天。
在启明星的陪伴下,小华背着一扁背篓草药,行走在进城的路上,走累了找个阶坎子坐下歇歇。
集市上。
一双乞盼的眼睛盯着行人,一个稚嫩的童音吆喝得那么凄凉。“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快来买我的草药,栓得大把......伍角钱一把。快来买呀,卖了钱......还要买米回家,还要给妈妈买治病的药。快来买呀!”
是叫卖声、是乞讨声、是求助声?
不少行人驻足,询问、购买,热泪盈盈。
小华高兴得快飞起来,一数,杂七杂八的钞票竟然有十二圆钱。到药店给妈妈配了五圆钱的药,又到米店买了五圆钱的米,剩下的二圆钱,购买了一包盐,好长时间都没有吃过盐。还有五角钱,给妈妈买了一根油条。
刘翠华不知道多少次倚立着门框,望眼欲穿地盯着公路。喃喃而语:“女女......快回家来,该回家来啰,莫不是遇着坏人喔?”
女儿兴冲冲回到家,第一个动作,抱着她一阵狂吻。“妈妈,我长大了,能供养你了!”
从扁背篓里拿出米。“我给你配了五圆钱的药,还买了这么多米......你闭上眼睛,猜猜还买了啥好吃的?”刘翠华睁开眼睛,一根香喷喷的油条喂到了她嘴边。
“唉呀,我又不是小孩,女女吃。”她用手挡开,眼眶里泌着幸福的泪。
“妈妈吃一口,我吃一口。”小华搂着她的脖子,撒着娇。“我也长大了。”
女儿买回家的三斤米,要盘算着怎样才能吃到下个星期天。在无人看见的时候,刘翠华拄着竹棍,从紫沙河边掐回“过江藤”、捡回别人扔掉的烂菜叶,掺合着熬粥。
小华是上长的人儿,无论怎样也要让她多吃一点儿东西,就是这野菜粥她也要忍嘴少咽。每顿吃饭都说“我吃饱了”、或者说“我吃过了”,她站在一旁,见女儿吃的狼呑虎嚥,她笑了。
笑得那么凄凉,笑得那么苦痛,悄悄扭过脸去。
这个星期六的傍晚。回家,小华放下书包和挖到的草药。长吁一声:“妈妈,我饿惨了......有吃的没有?”
刘翠华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回答。“在锅里......用凉水凉着呢。”
小华揭开锅盖,一看。“这是早晨留下的半碗稀饭,你一口也没有吃。妈,你会饿死的......呜呜。”
见女儿呜咽着,她微微仄了一下身子,声音很微弱。“女女......
你还小,你要长大......能看着你早一天长大,妈妈就放心了.......嗬嘿哧哧......”
像是气息供应不上。停了停,她又补充说:“妈妈饿不死的......命大。”小华端过那半碗已经变味儿的野菜稀饭,走到床前。“你不吃,我也不吃,你饿死了,小华就没有妈妈啦......”用调更喂一口她,自己吃一口。
小华没有哭。
刘翠华喘息声声急,吞燕着那变了味儿的野菜稀饭,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女女呀......你买的三斤米,一粒也没有了,又要断顿了。对不起......”
小华用手去揩妈妈脸上的泪,十分坚决地:“我决定——不读书了,去撬灯笼花,鱼鳅串到街上卖,每天有几块钱的收入,吃孬点儿,我们也能活下去。”
“只能这样了,苦了我的女女啊......”她泪水滚急、串串跌落在饭碗里。
小华却拍着胸脯这样说:“再捱两年,我十五岁,可以去打工,那时你就可以享福,咬紧牙齿也要活下去,我的妈妈哟......”
俗话说:又冷又饿,日子难过。眼目下正是伏天,又热又饿,日子更难过。
“唉,睡吧......”小华摸着前额,“我觉得头脑重乎乎的,遭流行感冒了,学校里有许多同学都咳得要死要活......”说着说着,觉得喉咙里奇痒难忍,咳得嘶声蛙叫,一长串“咳咳咳......”
她捂着咳呛得紫色一片的脸,笑笑。“就像在演戏一样。”
“昨天,我就感到胸口上压了一块石头,喘得更加难受......嘘嘘.“刘翆华也双手捂着胸晡。
“没有吃的,还要遭病......不晓得我们能活到哪一天?”小华在梦里也这样说着。
刘翠华的哮喘声像闷雷似的轰鸣着,“呼嗬嘿哧......”胸脯抽搐得老高。听见女儿的梦话,更感凄凉,流泪不止。“女女......你是不会死的,死的应该是妈。你还小......咳得这么恼火,该怎么办呀?”
她抖嗦着身子,挪动很久,才挪下床;向前挪了两步,感觉双膝软得支撑不住身体;忙俯下身撑着床边的木柜,慢慢挪向墙边,撑着墙壁挪向一只木箱,从箱里取出一只精致的玻璃罐,倒出两个小药包,笑容立刻露出来。
手上捏着小药包,比刚才精神,回到床边也没有刚才那么艰难。推醒小华:“女女,快......起来吃药”
“哪来的药?我不吃......”
“我......药罐里找着的感冒药,快吃呵。”
小华服药后,一头倒下,又昏昏大睡。
她也挪上床去睡,为避免哮喘声悚扰女儿,她用一只手掩着嘴唇。
不知什么时候,小华睡醒了。发觉门外阳光很强烈,翻动身子,立刻咳得死去活来,手指一掐太阳穴。“嘿,头不痛了。”
走到院坝里,见很多人家的烟囱都在冒烟。
“唷,睡舒服了,睡到第二天晌午......”她伸伸懒腰,回视屋内。“妈妈怎么没有醒来,齁喘的声音更加吓人......”
小华有些慌张,折身进屋,用力推搡刘翠华,“妈妈,快醒醒,你感觉怎么样?我去请‘光亮’医生......”
刘翠华无力地摆着手,无神的眼珠在缓缓移动。“女女......你感冒好些啰,妈就高兴,给你说......嗬嘿哧......哧。就是妈要死了,也千万......千万别去请‘光亮’医生,欠他太多的药钱......太多,很不好意思。嗬嘿哧......哧......”
她时不时地张开乌黒的嘴唇,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没有这个动作,似乎立刻就会咽气。
迟疑了一会儿,她那张浮肿、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庞上,露出了求生的表情、这表情又显出几分的不自然。“女女......你的身体立得住么?”
“立得住,要我做哪样亊情?”小华读出了妈妈眼里的神情。
“我......三天都没有吃啥东西,假意思吃过了、吃饱了......就是想让你多吃一点。嗬嘿哧......实在饿得受不了,死又死不了......”刘翠华张开乌黒的嘴,许久才说完这些话。
“去......河边捡点儿别人扔掉的烂菜叶......回来煮点儿汤来喝。”
小华哭着扑在妈妈的身上“怪我,怪我粗心大意......没有发现你的这些动作。不吃一点儿东西会饿死的,你是重病人。呜呜.......”
少顷,小华抬起头说:“我们去找人借一点米嘛......”
“不能呵,那些人要说-----妈的坏话,会给别人家里带来麻烦。嗬嘿哧......我的病情加重好几天了......不然我也会去河边捡烂菜叶、掐野菜。无论如何......要捱到你长大,妈才肯去见阎王爷......”
说完这些话,她剩下的力气似乎已经不多。
“我们这么困难,怎么没有人来管?汪家嘴未必没有一个好人?莫非......你把大家都得罪了?”小华睁着迷惑的眼睛问。
“要管......早就有人管喽,现在而今,各人挣钱都很忙。我哪里敢得罪大家啊,你长大就会明白......唉唉唉......”面对女儿的提问,她只能用有气无力地“唉”声来回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