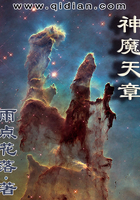常贞越飘越远的思绪被敲门声打断了,门外传来舅舅的声音,“贞儿,在学习吗?饭已经做好了,快下来吃吧!”常贞赶快把舅舅拉进房间,将刚才的冠礼之事一一告知。梅风是唯一知道常贞身世以及妹妹梅雨的真实婚姻情况的人,所以常贞将此事告知于他并无不妥。梅风听罢,语重心长地说道:“你父母难得见你一次,所以这次去一定要好好陪陪他们。你哥那头不用担心,我来应付就好。一会吃饭的时候,你不要多嘴,好好配合我,别给说漏了,知道吗?”常贞连忙点头,然后两人一起下了楼。
楼下的餐桌上早已摆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上桌之后,常贞不敢说话,一是舅舅刚才嘱咐的事,二是怕表哥仍然在生自己的气,只好不断地往嘴里填饭,结果就是两腮鼓鼓的,活像只仓鼠。而梅直君确实如常贞所猜测的那样,还在为他那不成器又不上进的表弟闷闷不乐。剩下的梅风一直都在寻思着如何开口说贞儿冠礼的事,所以也保持着沉默。一桌子三个大男人谁都不说话,气氛简直诡异到了极点。
最后还是由户主打破了这迷之尴尬,清了清嗓子对着梅直君朗声说道:“那什么,你姑姑和姑父回来了。”梅直君听到这话也顾不得生闷气了,放下筷子道:“姑姑姑父回来了,上次不是说要在非洲待七八年呢吗?”“哦,好像是国内有个紧急项目把他们召回来了,具体的都是机密,你姑姑没细说,我也就没问。”梅风尽可能地自然地回答着儿子的问题,“所以啊,明天贞儿就得去见他们,毕竟这么久没见了嘛!”梅风咽了口饭继续说道。常贞见状赶紧接茬,“是呀是呀,我特别想我爸妈。你说他们非得扔下亲生儿子反而去养活那些野生动物,真讨厌!”最后这句话常贞说得十分真切,毕竟自己与父母聚少离多是真实情况,没有造假。
梅风还没来得及继续说,梅直君就不乐意了,“怎么说话呢?姑姑姑父是那么厉害的野生动物学家,工作是忙了点,但他们看望你的次数也不能说少。至少我当了那么多年记者,还从来没见过干这种特殊职业的父母有比姑姑和姑父对孩子更上心的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眼看着梅直君的语气逐渐流露出训斥的意味,梅风赶紧接过话茬,“所以啊,这难得的相聚更是不能浪费,你说对不对,贞儿?”常贞用了可能是他这辈子最中气十足的声音回答道:“是。”梅直君也心疼弟弟没有和父母过多的相处过,赶紧问到:“他们到哪儿了?我开车去接吧!”常贞不知该如何回答,眼看着要露馅儿,梅风赶紧替他回答道:“不用,他们没回津州。这次回国时间有限,只会在常州停留几天,就是你姑父的老家,贞儿明天坐火车过去就行。”梅直君没有抬头,吃了口菜继续说:“那我明天送他去火车站。”常贞嘴张了一下正要拒绝,梅风抢着说道:“这么大的孩子了,他自己去就行。”他怕自己这较真的儿子又要说出什么让人难以回答的话,没有停顿的接着说道:“而且你也有事要办,明天替贞儿请个假,到学校。”
梅直君不解地看着自己的父亲,问道:“刚才还说他长大了呢!怎么不让他自己去请?”常贞也适当的发挥一下作用,软软的说着:“明天我一大早的火车,而且我们那老师从来不信任学习不好的学生,我要是自己去,一定会被他认为我在逃课。所以啊,哥,你最好了,而且你一看就是正人君子一个,你帮我去请,我们老师肯定就答应了。”可爱的弟弟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梅直君心中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长出一口气后无奈地说道:“知道了,记得替我向姑姑和姑父问好。”见到梅直君此状,常贞和梅风相视一笑,眼神会意。这舅甥二人又一次一唱一和地糊弄了这家里唯一的不知情者。
晚饭过后,三人各自回到房间里,常贞由于冠礼的事,心绪多了起来,但很快就被困意袭卷,进入了深度睡眠。第二天寅时,也就是凌晨三点,乌月和青月就带着一众侍童驾着四架马车来接常贞了。被接的那位虽然知道今天会很早,但还是没想到早得这么丧心病狂。为了不耽误吉时,乌月等童子只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常贞弄醒。最后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常贞终于醒了,乌月和青月赶忙把常贞扶上了车。
这辆马车车厢宽敞,车轮和把手均镶有玉饰,驾车的四匹马皆为黑色,但是毛色之漂亮难以言喻。这车对于常贞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自己每次与父母相见之时,不是自己坐着这车去见他们,就是他们坐着这车来见自己;陌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似乎也没有几次。所以常贞对这辆马车的感情是既期待又厌恶,只怪这马车一出现就既代表着相聚,同时也预示着别离。不过本该因相聚而感到期待的常贞此刻却因为起床气而对这辆马车满满的都是厌恶。
被派来打点的童子们似乎更加高兴,对于常贞那明显的不能再明显的起床气,他们不知道是没发现还是不介意,总之就是一拥而上给常贞梳头更衣。童子们很快便给常贞换好了代表童子身份的采衣采履,缁布制成的采衣,搭配上红色的锦缘和宫绦,显得不那么沉闷,更多了一份少年气。然而包括乌月和青月在内的一众童子都是修行了千年左右,保持着十岁童子的模样,而常贞已经十七岁了,头发更是因为短发而无法梳成总角,这使得他不知道从哪里透露出一股违和感,总之就是十分滑稽。
常贞正因为自己的这幅怪模怪样而在内心煎熬着的时候,童子们一个个化身为顶级花痴,不停地说着,“果然是常家公子,真真是一表人才”,“我那么多年都没见公子一面,今天见一眼真是死也无憾了”,“只穿着童子采衣便是这般潇洒,不知加冠之后会是何等风华”。总之就是句句不离“我家公子”,把常贞夸的天上有地下无。本来就不禁夸的常贞听到这些极度的赞美,更是飘飘飘然起来了,双方就这样保持着“一群愿意夸,一个愿被夸”的状态行进了一路。驾车的童子说着“公子,已经到了”的时候,车里还继续其乐融融着呢!听到到达的消息,乌月一拍大腿,指着青月就骂道:“我们忘了给公子介绍每位宾客的基本情况了。主公明明吩咐过了,青月你昨天不是玩了命的要说吗?怎么今天全忘了。”青月听着这话自觉有些愧疚,但是转念一想,“不对呀,乌月你不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吗?还好意思说我呀!”
“你……”
“我什么我。哼!”
看着两人又要吵起来,常贞赶紧劝阻,“没关系,到时候我就说我自幼长在人间,所以不知诸位的大名。那些既然都是大人物,应该不会和我这个后生小辈计较吧!”乌月摇了摇头说道:“公子有所不知,不识得其他宾客倒还好说。可是若不知主宾和赞者,那可真是大大的不敬,毕竟他们可是要为公子戴冠的,而有了这层关系,日后必会有诸多往来,怎么能一开始就对人家不敬呢?”
这边正说着呢,忽听驾车童子报,“主公和主母出门迎公子来了”。车内的讨论戛然而止,常贞心想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于是掀起帘子下了车,诸童子一见公子如此也都赶快跟在公子后面下了车,但谁都对刚才所说之事担心不已。常贞抬眼看到久未谋面的父母正站立在大开的朱门前,父亲还是那样英武挺拔,即使有高大的双阙立于身旁也并无大碍,母亲柔美的容颜也与记忆中的并无不符,仿佛只有常贞一人身上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
乌月仍然在常贞身后对刚才的事担心不已,一个人自言自语道:“那二位那么难伺候,可别干出割席之类的事啊!”莽撞的青月难得精明一回,没好气地说道:“冠礼上主宾和赞者那是最重要的客人,肯定会独坐,怎么可能和别人同坐一张长席,绝对不会有人割席的。”乌月听到这番解释,一边气恼自己急糊涂了,一边又稍稍安了心。其他的童子们也都就刚才之事各种议论。但是常贞完全听不到这些,朝思暮想的父母就在眼前,不知是近乡情更怯还是怎么的,他竟然感到无法挪动双腿。
相比于常伯漭的淡定,梅雨已经要哭出来了,看着逐渐成长为男人的儿子,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口中喊出的那声“贞儿”带着令人心碎的哭腔。听到母亲的呼喊,常贞不再迟疑,快速走上前去抱住了她。一直沉默着的常伯漭对着自己的妻儿说了一声“进去吧”,声音与他那英武的外貌相反,蓄着整齐浓密络腮胡子的嘴中发出的声音竟然是这般阴柔甚至是尖细。
三人一起走过庭廊,先去了位于整个宅邸中轴线上的祭殿。本来应遵循“左祖右社”的规矩把自家先祖和天地日月分开祭祀,但是常家人丁稀少,只因妖仙一流道行越高,修行时间越长,生育的欲望就会越低,而常家迄今也只有三代共三位而已。殿中所供的那位便是常贞的祖母,不过常贞从来也没有见过她;而常家一门均在月下修行,所以天地之间只供奉月神,继而干脆就将这二者合在一起供奉,也就是常贞即将参拜的这座祭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