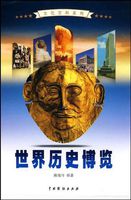....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转眼间,便是三年过去。
离中秋还有十日,院子空地中,一名英挺少年正端杆凝立,剑眉斜扬,目光低敛,嘴角因为抿的太过用力而发白。身姿状如骑虎,纹丝不动,一双手臂上,肌肉贲张,仿佛藏有千斤巨力。
忽然间,一只山雀冒失闯了过来,盘旋一圈后,仿佛感受到空气中的杀气,奋力扑动翅膀,想要飞离此处。
目光突凝,如同睡狮猛醒,林翘腰身微动,双手一拧一转间,丈长白蜡杆如巨蟒捕食般猛然挑起,虚影闪过,杆稍一点即收,发出声“咻”地破空厉啸。
捕风式!
半空中血肉飘洒,那只雀儿已被这一击戳得粉碎!
“好枪法!翘哥儿这一枪,俺老汤可万万接不下!”
站在空地旁观看的,除了脸色越见蜡黄的师父王进外,还有位锦衣大汉。见到林翘这疾速如电的一击,不由鼓掌大赞,脸颊上疤痕道道,看起来甚是渗人。
三年来,在师父王进倾心传授下,林翘把一套心意六合枪法练得精熟,颇有些圆润如意、随心所欲的味道。此时听得对方称赞,心下高兴,面上露出腼腆微笑。
“多谢汤师叔夸奖,那个,说好的短刀呢?”
金钱豹子汤隆,以后的梁山好汉之一,现也在延安府老种相公门下,与师父王进为同僚,关系极好。祖上世代以打造军器为生,手艺十分惊人。
汤隆有两大爱好,一是酒,二是赌。常在酒后拉着林翘关扑作乐,上次输了后,无奈答应新打制把寒铁短刀送给林翘。
此时听得林翘又故意询问,汤隆尴尬地打个哈哈,道:“翘哥儿尽管放心,俺老汤应下的事情,什么时候做不得数了?这不就送过来了?”
从怀里掏出把黑鞘短刀,汤隆带着炫耀道:“俺花了近半月,把经略府库存寒铁尽数精炼,方才打制出来这柄短刀,不是俺夸海口,以此刀锋利,削金切玉直如豆腐!”
闻言林翘目光一亮,赶紧接过短刀,见连柄长近一尺,入手沉重,刚一离鞘便寒气逼人。刀身颜色黝黑,脊背微向下斜,刀尖却又略呈弧形上翘,锋刃处暗纹层叠,对着日头一照,似有水波流动。
SOG索格超级黑刃!林翘在后世最喜欢的战术刀!这时见短刀完全按照自己画出的图样打制,不禁喜的心花怒放,反复打量,不舍得撒手。
“呵呵!汤兄弟别惯坏了孩子。”见得汤隆耗费精力替徒弟打刀,王进不由乐得呵呵直笑,岔开话题道:“翘儿,单论枪法,你确实已精熟无比,不过,劲力收放上还有些欠缺,仍须好好打磨啊。”
等王进教导徒弟几句后,汤隆见时候不早,便催促一起去同僚府上饮酒。
而林翘则要去城外练习骑术,当下自去到后院马厩,牵马出来,装好鞍具,同容伯打声招呼后,出城直奔宝塔山。
这匹枣骝马,还是师父王进从东京带来的,年岁已老,体力速度都有些不济,遇到需要人马配合的招式,演练起来就很困难。而林翘家道中落,这些年全靠城外三十亩水田支撑,极是拮据,哪里能买的起马匹。
宝塔寺附近有片平整空地,在上面练了会双腿控马之术,林翘便有些意兴萧索,当即来到路口一处茶寮,把枣骝马系在外面,自己准备要碗茶喝歇息会儿。
这时正是响午,虽已快到中秋,天气却依然炎热。宝塔寺外行人稀少,茶寮外也只停着辆马车,两名客商打扮的汉子正坐在棚内喝茶歇脚。
两名客商一穿黑袍一穿红衫,样貌粗豪,眼神机警,见的林翘进来,都是紧张地抬头打量,等听得对方与店家相熟,这才松缓下神情。
大碗粗茶,喝在嘴里虽苦,却极为解渴。林翘刚喝到第二碗,忽听得外面脚步声密集,接着有人大叫道:“那厮鸟在这里!”
话音未落,两名客商均是神色大变,探首向外瞧了眼后,呼地站起,想要夺路而走。却已经晚了,只见门口人影闪动,六七名手舞棍棒的大汉冲了进来。
这群大汉们皆都穿着皂色劲装,身手矫健,配合娴熟,喝骂着扑向两名客商。几个呼吸间,穿着红衫的客商便被乱棍打倒,脑袋上血流不止,趴在地上软绵绵的不再动弹。
黑袍汉子虽然勇猛,却好汉难敌众手,斗得几个回合,被人抽冷子用长鞭缠住脚腕拽倒,随后被大汉们一拥而上按住。
这时,一名锦衣玉带的青年急步走进来,示意手下把黑袍汉子捆好,然后甩动着根水貂皮马鞭,冲对方威胁道:“青花骢藏哪去了?交出来,本衙内担保你无事!否则,定叫你后悔生在这世上!”
“呸!”黑袍汉子满头赤发,胡须焦黄,神情很是彪悍,丝毫不惧落入对方手里,大骂道:“狗衙内!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段爷爷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算好汉!”
“找死!”锦衣衙内立时翻脸,马鞭唰地甩起,冲着黑袍汉子就劈头盖脸狠狠抽去,鞭鞭见血,不一会便把对方抽得皮开肉绽。
连续抽了十多鞭,锦衣衙内方才停下,恨意仍是难消,转身又照着趴在地上不动的红衫汉子踹了几脚,见到没有反应,奇怪地弯腰瞧了眼后,脸色立变。
红衫汉子双眼瞪得多大,却呼吸全无,脑袋下汪着大滩鲜血,分明已经气绝!
似乎没想到会闹出人命,锦衣衙内一双小眼滴度乱转,忽然将身上一块玉佩解下,塞到红衫汉子衣襟内,然后叫道:“好啊!这贼厮鸟偷了本衙内玉佩,怕见官吃板子,竟自个畏罪自杀了!”
我靠!有这么无耻吗?
从皂袍大汉们冲进来后,林翘就与伙计躲在茶寮角落,事情过程看的一清二楚。这时见锦衣衙内如此栽赃脱罪,不由得心下痛骂、
锦衣衙内叫了句,获得手下们一片迎合,却还是觉得不妥,转又打量起茶寮内的外人。等看到站在角落里,皱着眉毛一副反感模样的青衫少年时,目光猛然阴森起来。
腰系黑缎缠带,头戴皂角纱巾,眉眼清秀,身躯强健,一件普通的淡青劲袍竟穿出股英挺不凡的味道。
对方这副练武打扮,绝不是一般百姓人家出身,莫不是经略府哪位将领的家人?这可糟糕了,军中赤佬们跟当地府衙向不对付,怕不愿帮自己遮掩住这条人命。
一张酒色过度的青皮脸来回变幻,锦衣衙内忽地开口问道:“小子,你是经略府哪家的,叫什么名字?那贼厮偷了本衙内的玉佩一事,你可看清楚了?”
管谁叫小子呢?想要让自己作伪证是吧?打错算盘了!
林翘一双剑眉皱得更紧,心里腻歪到了极点,嘴唇紧闭,根本不理对方。
若不是师父一再交待,不许在外头依仗武艺惹事,就凭你栽赃陷害草菅人命,非把你揪到衙门去不可!
这小子竟无视自己?锦衣衙内怔了下,猛然大怒,狭长双目中一片阴狠,瞪着对方喝将起来。“耳朵聋了?本衙内问你话呢!”
你才聋了呢!
冷冷瞧了眼面目狰狞的对方,林翘依旧沉默不理。而站在身旁的伙计吓得够呛,哆嗦着拉住林翘衣角,劝道:“小哥儿,这是廖太守家的衙内,快给赔个不是,他们……他们会杀人的!”
知府家的衙内?那又怎样!自己又没招惹他,干嘛要去给这等无耻小人赔礼?!
挣开伙计的拉扯,林翘扫了眼地上的红衫汉子尸体,愤慨不平下,终受不住对方无法无天,管起了闲事。责问道:“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你们就不怕官府捉拿问罪?”
一言既出,众人均都惊诧,锦衣衙内更是奇怪地看着林翘,似乎没料到还有人敢指责自己。呆了下后忽地放声大笑,怪声叫道:“好怕怕呀!小杂毛要拉本衙内去见官啦!孩儿们,怎么办啊?”
边上大汉也是哈哈哄笑,发狠道:“官府?官府便是俺们廖衙内家开的!小杂种别蹭鼻子上脸,敢惹衙内?哥几个活剥了你!”
尼玛!嘴巴吃大便了,怎么这等臭?
听得对方如此张狂,满嘴喷粪,林翘心火噌噌狂冒,转眼便不可抑止。那还顾得对方是延安府父母官的衙内,目中冷意如冰,盯着那张略显浮肿的青皮脸,缓慢却异常坚定地吐出两个字。
“放屁!”
什么?皂袍大汉们有些不信自己耳朵,这名还带着稚气的少年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回骂廖衙内?
上一次,黄团练使家的小儿子羞辱廖衙内是青皮狗,结果被当着他爹黄团练的面,用鞭子活活抽残废了!怎么,这小子仗着是经略府的人,就敢与廖衙内做对?
在众大汉们如看死人的目光中,林翘神色平淡,冷峻依旧。而廖衙内气得暴跳如雷,几步跨过去,目露狠毒,手中马鞭呼地挥动,兜头盖脸抽向对方!
唰!鞭梢打着圈儿,劈头盖脸罩了下来,破空声噼啪作响,落在身上,必定连血带肉撕下大块!
好毒辣的鞭子!
廖衙内最爱使鞭,侵淫极深,对自己这一鞭信心十足,这时脸露狞笑,仿佛已经看到对方清秀面庞上血肉横飞的惨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