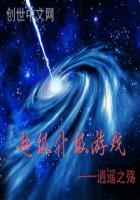国都圣城,枝头花残,柳色青青,才歇了一场风沙,又迎来一场急雨。
夜已深沉。一个骑手由南而来,身上背着一个锦缎包裹,马背上插着一面红色大旗,马蹄声碎。禁卫军统领看见马背上的红旗,急吼吼的叫了起来:“紧急军务!快!打开城门!”
城门缓缓打开,骑手进入圣城,直奔宣武司而去。马蹄踏在积水中,水浆四溅,雨声虽疾,却挡不住马背上的红旗招展。
宣武司,总领帝国军务,昼夜有人值守。雨夜风寒,闷得有些无聊的轮值裨将喝了点酒,酒意微醺,忽然听到外面鼓点一般的啼声,下意识的丢掉杯盏,站起身来。
骑手跳下马背,奔入宣武司中,直闯门房。骏马无人驱使,又向前冲出一段,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骑手闯入门房之中,将包裹取下,交给轮值裨将,有心再交代两句,却也是眼前一黑,昏倒了过去。
眼看事态紧急,裨将也顾不得倒地不醒的骑手,就着昏黄的灯光打开包裹,从火漆封印的传信筒中取出一卷纸,展开来看。纸上寥寥数语,看得裨将胆颤心惊,酒醒了大半,一脚跨出门房,火急火燎的叫了起来:“快!快去请朱大人!”
朱韬,大安帝国宣武左使,掌管帝国军务,已是花甲之年。人上了年纪,容易失眠,再加上他一生戎马,身上多有创痕,每逢天阴下雨就格外的难熬,就像有千百只蚂蚁在骨头缝里啃噬一样。因此,虽然已是午夜过后,朱韬却还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他听到外面的急报,连忙穿起衣服,披了一个蓑衣,跨上战马,赶往宣武司。到了地方,他从裨将手中接过战报一看,大惊失色,微一沉吟,也顾不得改穿官府,穿着便装打马奔向皇宫。
值夜的内侍看到朱韬这等模样,很是不喜,拉住了他的马匹,挡了他的驾:“朱大人,且不说您深夜闯宫有违规制,就看这身装束,也是于礼不合啊!天子陛下已经睡下了,您啊,还是等明日朝会之时再行觐见吧!”
朱韬心下大急,嚷了起来:“滚开!你这狗奴才!军情紧急,片刻都耽搁不得,我要立刻面见天子陛下!”
那内侍把脸一沉,不咸不淡的说:“朱大人当真好大的官威啊!我固然是个奴才,那您哪?您不也是天子陛下养的一个奴才吗?”说到这里,他又把头摇了起来,换了一副不解的神情,口中说出的话语却更是刻薄:“我这个做奴才的,可是真的搞不懂你们这些当大人的!有什么紧急军务?帝国军政不是把持在您的手中吗?这不是您的分内之事吗?食君之禄,却不能为君分忧,莫不是忘了做奴才的本分了吧?”
“你……!”朱韬大怒之下,抬起马鞭抽在了内侍的身上,大声喝道:“你身为天子近臣,怎的如此不通情理?军情如火,误了时辰,你担得起吗?”
那内侍吃了一鞭,面色一寒,眼角抖个不停。自打他领了这份差事,任你位高权重,谁人见了他不都得毕恭毕敬的,笑脸相迎?他是谁啊?他是天子内侍,虽然官小职微,可毕竟是天子身边的人啊!不说其他的了,就说这面见天子,很大程度上都要看他的脸色。
旁人面见天子,无不乖乖奉上银两。唯独这个朱韬,仗着执掌军机事务,却是一分银钱都没孝敬过。平日里也就罢了,可是现在更深夜重的,又下着雨,天子好不容易才睡下了,你说见就见哪?门儿都没有!什么紧急军务,什么刻不容缓?一句话,小爷不爽,你一边儿等着去吧!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朱韬居然如此放肆,敢拿马鞭抽自己!这一下,他觉得自己高贵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冒犯,也顾不得什么天子陛下睡没睡了,扯着脖子喊了起来:“来人哪!朱韬私闯禁宫,图谋不轨,给我拿下!”
禁宫侍卫应声而出,各执兵刃,把朱韬围在了中间。看见这副情形,内侍的心中暗暗得意了起来:“朱韬啊朱韬,你不是看不上小爷吗?这一次,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那可就怪不得我了!”
想到这里,那内侍目光中流露出怨毒的色彩,躲在人群后面,嘴角挑起老高:“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将他拿下!”
侍卫们正待动手,就听到身后的寝宫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天子陛下的贴身侍卫从里面走了出来,对着众人连连摆手。还不等那内侍反应过来,天子陛下就穿着睡袍从寝宫中走了出来,皱着眉头问:“怎么啦?”
禁宫侍卫收住攻势,跪倒在地。内侍也连忙换了一张很是谄媚的笑脸,卑躬屈膝,低着头说:“陛下,朱大人夜闯禁宫,我等拦他不住,起了一些争执。不想竟惊扰了圣驾,还请陛下恕罪!”
“哦?”天子陛下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又身居高位,本该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可眉宇间却有着说不出的疲惫。他看了自己的内侍一眼,没有吭声,又向前走了两步,对跪在地上的朱韬说:“朱卿,何事如此惊慌?可是那普兰特帝国又来犯边了吗?”
朱韬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这才回道:“天子陛下,不是安南,是扎西!”
“扎西?扎西又怎么了?”天子很是不解。
朱韬偷偷打量了一眼天子的神色,小心的组织了一下词句,小心翼翼的说:“穆老将军送来急件,说是洛特帝国的大军已经攻破城防,连下南阳、赤水两座雄关了……”朱韬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取出边关急报,托在手中。
“什么?!”
天子大惊,也顾不得什么威仪了,急匆匆上前两步把边关急报抓在手中,转身回了寝宫:“掌灯!快掌灯!”
那内侍满以为天子会对朱韬施以惩戒,没想到他对此竟然是问都没有问一句。这让他心里有些泄气。尽管如此,听到天子的吩咐之后,他还是屁颠屁颠的跑在前面,点亮了烛火,仔细的伺候着天子坐下了。
天子坐在案旁,将文书展开来看,写的是:“臣穆冬启奏:春三月初九日,有洛特帝国两万军,连夺我南阳、赤水二关,请天子圣裁!”
看完了这份边关急报,这位天子陛下冷着脸,很长时间都没有言语,心中却已是思绪翻腾:想我大安帝国,煌煌万里疆土,威德加于天下。两年前,岳林丘焚毁玄黄丹,普兰特帝国借机兴兵,引来临海城之败。现在,竟连洛特帝国都远渡重洋,前来犯我国土。三百年来,天子受命承天,帝国威服四海,何曾受过这等屈辱?若非是长老院中那群老东西诸多掣肘,朝堂之上虎狼当道,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想到这里,天子陛下心怀激荡,重重的一拳敲在桌案上,这才心绪稍缓,转念又想:这洛特帝国,莫非真以为我帝国无人了吗?也好,就借着这个机会让天下人看看,猛虎虽老,也还是有几颗牙齿的!等我撑过去这一阵,彻底掌握了政权……哼!
天子想到这里,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把手往桌案上一拍,站起身来吩咐道:“给朕更衣。”说完,他又对那内侍说:“你,去让人撞响景阳钟,敲响登闻鼓,朕要临朝!快去!”
听天子如此说法,那内侍猛然有些后怕了起来。景阳钟也就罢了,说到登闻鼓,那可都是万急之时召集群臣的器物,轻易不会动用。莫非……莫非真的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吗?
想到这里,又记起自己先前将朱韬拦在门外,这万一天子陛下追究起来……想到这里,那内侍一个激灵,趁着天子还没有追究的意思,忙不迭的跑了出去。
不一刻,钟鼓齐鸣。清越的钟声在夜雨中格外悠扬,雨点般的鼓声直震人的心头。听闻钟鼓声响起,拱卫圣城的禁军人喊马嘶,圣城之中但凡是有资格上朝议事的文武官员都急急的整顿好装束,齐奔承天殿。
承天殿中,灯火通明,文武聚集,天子高坐王位。
群臣正要见礼,就见天子从王位上站起身来,一甩衣袖,冷着脸说:“算了吧!”
群臣不解,一时间跪也不是,站也不是,面面相觑,小声的议论了起来。
天子看着自己的这满朝文武,很是自嘲的笑了一下,背着手走下御阶,边走边说:“诸位大人,朕让人击鼓撞钟,扰了你们的美梦,实在是对不住的狠哪!”
群臣一听这话,知道事情不对,连忙齐齐跪倒在地,口称惶恐。
天子却像是没看到一样,继续迈动自己的脚步,也继续说着自己的话:“两年前,临海城中玄黄丹为祸,岳林丘将军前去收缴,普兰特帝国犯我边境,我军一败涂地。当时,你们是怎么说的?”
也不待别人回答,天子就自顾的把话接着说了下去:“你们说,敌军势大,不可力敌。还说我军之败,不在将领无能,只在军械不利,只要给你们两年时间,定能一雪前耻。朕,信了!”
说到这里,天子脸上浮现出自嘲的神色,转过身子向王座走去,口中仍旧是说个不停:“现在,两年过去了。帝国花下去了多少银子?朕想知道,朕的军队呢?你们用来一雪前耻的精锐呢?”
听了这句话,负责帝国军备的炼器司司正壮着胆子接了一句:“启禀陛下,帝国军备,现在已经堪称一流,就算是普兰特帝国再度兴兵来犯,也定能让他有来无回!”
天子停住脚步,斜睨了炼器司司正一眼,抬手将穆冬边关急报摔在了他的脸上,断然喝道:“简直就是一派胡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