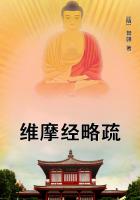萧绰于上京城外二百里迎着耶律贤的灵柩,当时便昏厥过去,施救半晌,才悠悠醒来,呼天抢地地哭,一日之内昏厥数次,众臣耐心解劝,方慢慢止啼,扶灵柩停缓缓朝上京归来。
灵柩到京,室昉率众迎于潢川岸边,众亲王,公主,驸马,嫔妃及文武百官匍匐道路,霎时,哀声大起。
耶律斜轸道:“诸位先莫悲哀,现在要先安顿好先皇的灵柩,接待好各国前来吊唁使臣,以免别人说我们的笑话。”
众人于是收住泪护着灵柩进了上京。
次日,耶律隆绪在偏殿接待了众臣和属国使节,萧绰坐在一侧听取政事,一应公务皆由她裁决。当时,恼了一人,大声说:“先皇未明,大辽社稷岂能付于一乳臭未干的小儿?”
萧绰错愕,抬眼望去,嚷闹者却是皇上的叔叔,先皇的弟弟耶律质睦。萧绰正欲开言,只听见荆王耶律道隐也随声附和:“江山大计,岂同儿戏,宜由有德有为之人居之。”
韩德让厉声道:“有先皇遗诏,谁敢违抗,立斩。”遂令内侍取出遗诏,朗声读道:
朕自幼不幸获疾,身羸体弱,及长习武骑射,纵横驰骋,本指望强筋壮骨,抗疾弭病,不意天不存恤,反令朕积劳成疾,以致不救,天算寿夭,不可逆也。
然大辽中兴未至,民无安康之保,国有强敌窥伺,朕大限尽,而愁无穷也,皇子年幼,威信未立,涉世不深,处事天真,此朕之大优也。所幸梁王秉性忠厚,心怀仁慈,聪明卓识,德才兼备,继承大统大辽中兴有望,社稷百姓有福矣。愿诸卿善辅之。皇后睿智英明,胆识不让须眉,雄魄胜过武曌,谙悉国事。朕大限之后,一切政事悉由皇后裁决之。
耶律斜轸怀才抱器,沉稳练达,堪付大事。韩氏一门,数代尽忠,德让数次救朕于危难,智勇双全,忠肝义胆,令其辅佐梁王,必能竭虑进智,不负朕望。耶律休哥勇猛英雄,谙熟军事,南面之事付之,万保无虞。室昉,马得臣,邢抱朴俱有济世之才,经纶之手,宜解其桎梏,释其手脚,其必为大辽中兴奠石筑土,强国富民也。
朕弟质睦,自幼聪慧,能诗善赋,幼与朕最善。然朕登大宝以来,国家大事日重,兄弟之情日疏,以致曲解不和,此乃朕痛心疾首之病也。朕今生无补矣,朕走之后,诸王子待之应如父,诸臣待之应如朕,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三关之地本非辽土,连年征战,士疲民乏,伤亡惨重。士卒皆父母所养,寄父母所望,一旦战殁,家人失望,造孽深重。吾儿继位以后,宜体恤民情,靖边富国,切勿妄生战端。至嘱,至嘱。
遗诏尚未读完,已有二人晕倒,一是萧绰,二是皇叔耶律质睦。众人慌忙救起,喂汤喂药,挼搓掐按,弄了半天,二人才悠悠醒来。萧绰泪流满面抱着耶律隆绪大哭道:“先帝何去之急哉?弃朕之娘儿于不顾。如今母寡子弱,部属雄强,边境未靖,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韩德让,耶律斜轸匍匐道:“皇后安心,先帝临终托臣等大事,臣等肝脑涂地无以为报,请信任臣等。”
正在这时,涿州刺史耶律虎古上前指着韩德让说:“你一汉奴,先皇如何能托孤于你,遗诏有诈。”
韩德让纵身一跃,闪身夺取了一名侍卫手中的铁钺,直往耶律虎古头上一砸,耶律虎古猝不及防,被砸得脑浆迸裂,倒地毙命。众臣一阵惊扰,纷纷按刀作发。只见耶律斜轸已掣出宝剑护在萧绰,耶律隆绪面前。室昉击了两掌,殿外呼啦啦地跑进一群全装贯带的侍卫亲军。殿中顿时安静下来。韩德让取过一把佩刀,只一刀枭了耶律虎古的首级,掷出殿外,令人将首级悬于城门外示众。众人惊骇,两股战战不止。
耶律质睦双腿一曲,跪在阶下,道:“罪臣该死,,数拂逆圣命,皇兄念及手足之情,不罪逆臣,已是万分宽容。想不到皇兄如此仁爱,愚弟顽钝,愧疚万分,无颜苟活于世,皇兄等等我,我随你来也。”质睦说罢,欲行自杀,众人把住,一面好言相劝。耶律质睦,这才指天划地,振振发誓:“从今而后,质睦一心效忠皇上,若有二心天打雷劈。”
质睦此言一出,撼动群臣,皆发誓效忠新帝。乃上皇帝尊号为昭圣皇帝,尊萧绰为皇太后,改国号为大契丹,大赦天下。昭圣皇帝下诏:复皇叔耶律质睦宁王之爵,进室昉为丞相,以南院大王耶律勃古哲统领山西诸路事,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奚王和朔奴为副都统,萧道宁领本部军驻守南京,委韩德让总宿卫事,耶律斜轸为北枢密使。文武百官悉进爵禄,恩裳有加。又将耶律贤的遗物分赐给诸臣,众人噙泪谢恩。
宁王质睦请示陵寝之事,萧绰道:“他皇叔不说此事,朕也要找你商量,先帝在日曾倡导节俭,然生死大事,岂能草率?朕欲请皇叔总理此事,虽不要铺张,也不能简陋,免得让他国人见了,说我契丹寒碜小气。”
耶律质睦点头称是。
过了两日,要为耶律贤做超度法事。萧绰与耶律隆绪率文武百官前往节义寺进香礼佛,方丈慌忙将萧绰等人迎人寺内。走进寺门,是一数十方丈的大院子,院子中间立一巨碑,碑上镌刻着契丹字汉字铭文。萧绰扫了一眼,便再也挪不动脚步,驻足在碑前细读起来。不一会儿,只见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其实,碑文只是记述述律皇后断腕殉夫之事:天显元年七月,太祖耶律阿保机驾崩,皇后述律平哀痛欲绝,意欲以身殉葬,后经大臣苦劝方止,最后砍断自己的右腕置于太祖灵柩之内,其情可感日月。因此,建此寺立此碑以彰其德。寺内有一楼名断腕楼,便是述律皇后断腕之处。
萧绰看罢铭文,呼吸艰难,步履蹒跚走进断腕楼内,里面供着述律皇后的塑像,萧绰久久端详着述律平,缓缓环着塑像走,边走边叹息。最后拜别出来,回到蕞塗殿,萧绰便晕倒在灵柩前,众人千呼万唤方才转醒。萧绰以头抵着灵柩哀哭道:“皇上,你好狠心啊,你扔下寡人,叫寡人怎么活呀,你等着,寡人随你一起去天堂,寡人一路上照顾你。”说罢抽出佩刀自刎。
耶律斜轸一把夺下佩刀,萧绰只以头撞击灵柩,一时头破血流。耶律隆绪死死抱住,大声哀求。众臣一起跪下劝其节哀。
萧绰哭道:“夫妻如同阴阳表里,无阳,阴无所立,无表则里无所附,今先皇已去,朕何以独存?”
耶律斜轸说:“太后难道忘了先帝的嘱托吗?”
萧绰泣道:“朕如何忘得了。”
耶律斜轸说:“先帝临终托太后以国家大事,今天下未靖,先帝尸骨未寒,太后却以身殉小义,有负先帝之望而寒志士之心也。”
萧绰说:“朕心甚昧,方才看了铭文,实感淳欽皇后之德。想先帝在世,与朕伉俪情深,恩爱和美,今遽离去,朕如何舍得,直叫人痛不欲生。淳欽皇后能以手殉葬,朕如何不能以身殉夫?即不能身殉,也要效仿淳欽皇后砍下一只手,给先帝作伴。”
说罢,萧绰抓起地上的佩刀朝左手腕剁去。韩德让急忙伸手抓向佩刀。萧绰一怔,忙收刀势,但刀刃仍从韩德让手心划过,鲜血立刻染红了衣袖。萧绰知道耶律斜轸有一套空手夺白刃的功夫,没想到韩德让不顾断手的危险来夺刀,幸亏,自己眼尖,不然他的手指就要被截断了。就在萧绰惊愕的一刹那,她手中的佩刀被耶律斜轸夺去了。
韩德让叩头泣道:“太后切勿凭一时之气,坏了国家大事。臣受先帝厚恩,无以为报,愿以身殉。”
经韩德让一说,当时,灵柩前数名大臣及侍卫皆愿身殉以谢帝恩。渤海挞马竟不待诏允,自刎于灵柩之前。萧绰忙令人救起,这时,赵妃,公主胡骨典,奚王筹宁,北大王普奴宁,惕隐屈烈,吴王稍,宁王质睦俱嚎啕大哭,争着殉身。
萧绰跺脚道:“罢了,罢了,朕赌一时之念,险些误国,尔等俱国家股肱,岂能摧折,从今而后,断不能以人殉葬,逝者已矣,生者何辜?”
萧绰又令太医好生医治调养渤海挞马,并赐旌旗数面,插入挞马府门之上,以彰其忠,并令文人作赋记述此事,选上等佳作置于耶律贤的棺椁之内。
自此,内政调和,君臣和谐。韩德让,耶律斜轸不负先帝所望,竭力辅佐朝政,不敢丝毫懈怠。耶律隆绪虽然聪明,但毕竟年幼,大事皆由萧绰决之。萧绰坐于朝堂之上称孤道寡,煌煌赫赫,发号施令,果断英明,颇有武后之风。
一日,朝中无大事,早早散了朝。萧绰心中高兴,难得有如此闲暇。几个月来,一直处于悲痛之中,一直忙于耶律贤的丧事,心情被压抑得艰于呼吸。现在,耶律贤的后事已料理得差不多了,不用每日去守灵了。此时,耶律隆绪被师傅室昉领到御书苑去了。政事也不必事事亲躬,有韩德让,耶律斜轸左右膀,她也放心让他们处理。萧绰在御花园里信步乱走。此时,春意日浓,百花吐蕊,衰草返绿。萧绰边走边欣赏,忽然想起南京的事来,再过一些时日,栀子花就要开了,洁白如玉,清香袭人,叫人爱恋难舍。还记得每日折几支插入韩德让案头的花瓶里,偷偷进去,偷偷溜出,欲露还羞。每次进去极力按捺着砰砰乱跳的心,生怕一不小心吵醒了熟睡的他。她喜欢看他惊喜的模样,天真得像三四岁的孩子。光阴荏苒,一晃就二十多年了。想起来,恍若昨日。那是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呀!可是,从那以后,什么都变了,虽然韩大哥还是那个韩大哥,一直爱她,宠她的韩大哥没变。他一直不肯成家,她心里明白,他的心思全在她的身上。这让她高兴,更让她心痛,亏欠他太多了,无法弥补。
正走着,萧绰听见篱笆墙外有人说话,一声短一声长地叹息夹嘈,萧绰不禁驻足静听。
只听一个妇人长叹一声说:“我们女人就是这命,那刘玄德说过,女人就是一件衣裳,想穿想脱,由男人的便。”
另一个妇女接口道:“谁说不是,生就了让男人使唤的命。”
又一个妇女反驳道:“那不一定,先皇帝不是处处听皇后的?”
但听一个妇女压低声音说:“这也是命,女人命硬了有什么好?克夫呀。武则天命硬,一手遮天,唐高宗被她克了。如今,皇后命硬,先皇帝早死,多半就是她克死的。”
“可不是,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她整天寡人寡人地叫,皇上哪经得起如此诅咒?”
“这回她真成了寡人了。”
萧绰大怒,一脚踹开篱笆,只见几个妇人席地而坐,见了萧绰,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跪在地上瘫成一团。原来是几个近幸的妇人与伶人挞鲁之妇在一起胡诌。萧绰气得浑身发抖,任凭几个妇人如何告饶,喝令侍卫将她们拖走。
萧绰令人将几个妇人带到大殿,命人将其各掌嘴五十,直打得那些妇人满嘴流血,牙松齿落。萧绰仍怒气难消,令人将其牵入牢中关押起来,待后处置。自己气忿忿回到寝宫,越想越气,脑门如锥般地刺痛。这些人分明是讥笑她是个寡妇,无中生有编排她克夫,好像耶律贤的死罪过在她,她是杀人凶手。而她未进宫之前他就孱弱得不行,能活到今天,都是她一心调养得好。他身子不好,不能操劳,她帮忙分担一些,这有错吗?现在倒好,反而落人口实。做女人真难,难道真的只有俯首听命,给人当衣服的命?当年,一道圣旨不容分说地将其接入宫中,进宫之后服侍一个病人。皇上固然很好,但他毕竟是皇上,嫔妃若云——有很多衣服——想穿哪件就穿哪件。
想到这儿,萧绰又想起韩德让,只有他始终如一,痴痴的宁可担着性命之忧与她偷情,也不移一丝之恋。他就如一个傻子一样,一心一意只想着如何去爱她,宠她,保护她,他是她的奴隶,也是她的保护神,默默的为她做一切事,却别无所求。虽然,他恨耶律贤,可看到心上人地位不断上升,他心中由衷为她高兴。这些是他不能给的,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似乎成了萧绰的累赘,因此,在他们偷情的时候,他显得缩手缩脚,沉重的负罪感压迫着他。自耶律贤驾崩迄今,他们还没有真正地接触过,虽然,她从未真心地爱过耶律贤,但想起皇上对自己的好,皇上的死还是让她心如刀绞,提不起幽会的兴致。昔日幽会时,她总怨耶律贤是个障碍,如今障碍清除了,她却感到她与韩德让之间似乎立起了一堵墙壁。每当她想起往事时,有一股愧疚之情漫溢上来,而在昔日,她在偷情时她甚至因此而得意,把它当做报复耶律贤手段。而今天,那帮长舌妇的一番胡言乱语人她大大的震怒了,她们胆敢如此嘲笑朕,幸灾乐祸,好,寡人要看看你们如何面对痛苦的。
萧绰越想越气愤,令人将宫中的有妇之夫齐抓起来,严加刑讯。一时间,宫中哀声大作,冤声不断,数百人被投入大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