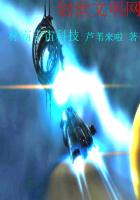当我睁开双眼时,双手已铐上手铐,在一辆囚车上,路途颠簸,不知运往何去。
车上四人,包括我在内,对面是两个染着红发的青年,靠着车箱与我对面而坐,从面上,应该不到三十岁,另一个人与我并排而坐,大块头,一身彪肉,年纪跟我差我不多,二十几岁。
在这一刻才意识到任务已经开始了。
我透过铁网向外看了一眼,天快黑了。
刘小军这酒果然好东西,要是哪天失眠,借来喝也是不错的。
我用脚踢了一下旁边的大块头,笑着说:“兄弟,我们这是要去哪?”
大块头似乎不喜欢我跟他打招呼的方式,一股脑儿爬起来,瞪着我说:“找死?”
真是一个带刺的主儿。
在这环境我必需装作很**的样子,冷笑一声,说:“在这别装横,有本事出去单干。”
我话一出那大块头一把抓住我衣襟,眼睛像刀一样地盯着我说:“等我。”
这**样还能不能跟他做朋友?我站起来挣脱大块头的手,用同样的眼神盯着他,“能不能出去还是个问题。”
“不一定哦。”对面一个稍瘦一点年轻人说。
“哦?”我疑惑。
“闭嘴。”大块头喝止了两个年轻人往下说。
看样子他们是一伙的。
白眼狼你也太什么那个了,一点背景不交待,也不告诉我囚车上这三个何许人也,你们也太瞧得起我了吧,让我自力更生。
在教导队第一周便是学习挣脱术,为了加大难度与更快掌握,教练会将我们带上手铐或铁链关进铁笼扔到浅海里,为了活着,你必须要在一分半钟从里面挣脱出来,不然,你会死在里面,当时,就有一个战友没有挣脱而永远沉入大海。
车一直开着,天已黑了,淡淡的月色透过铁网撒了进来。
想要跟他们成为朋友除了与他们同流合污之外还得有一项让他们佩服的手艺。
我挣脱手铐,站起身,走到铁网旁向外张望,这时,我余光注意到那个大块头在看我,并表示出惊讶,我是故意引起他们注意的。
“你……”大块头表示出很意外的样子。
“想走吗?”我对大块头说。
听他向对面两个年轻人大声呛就知道他的地位比他们高。
“你手铐怎么回事……”大块头说。
我轻蔑一笑,走到大块头旁边,蹲下,说:“想出去没?我观察了一下,四周是一片林子,现在出去是最好的时机。”
我这一说他似乎忘记之前单干那事。
“是吗?”大块头说,说完站起来也向外看,外面一片漆黑,但能肯定是一片林子。
“走吗?”我说。
他在心里掂量了一下说:“走!”
“好,那我问你你知道这是什么车吗?”我说。
“什么车?”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车。
我在彪汉后面的墙上敲了一下,说:“这是合金钢,一般的狙击枪无法击穿它,除非火箭筒,这种车通常运压一些重刑死犯,以防路上被劫,坐上这车的结果只有一个,死!”
我这一说,大块头立刻紧张起来,看来我说的话他信了。
“那怎么才能出去?”彪汉说。
“我自有办法。”我说。
看样子大块头相信我了,便故弄玄虚在车箱里走了一圈,摇摇头又点点头,他见这样子吓出了一身汗。
我想,白眼狼既然安排我与他们在一起,为了博取信任一定会让我放他们出去,放长线钩大鱼的道理不可能不懂。
“我不确定能不能打开,但可以试一下。”我说。
“那试一下。”大块头很急的样子。
看他现在这熊样,不由想起他傍晚那**样子,真想揍他一顿。想归想,任务更重要。
我看了看对面两个年轻人,意指他们怎么办?
大块头一看我表情心领神会,说:“不用管他们。”
“十四哥,你……”其中一个稍瘦一点的年轻人说。
年轻人话没完便被我一掌将其打晕。
“为什么不带他们一起走?”我说。
“多一人多一份负担。”
这多么凸显军人与黑社会之间的区别,不管在什么环境,生离死别也好,永远不会抛弃兄弟,就算牺牲自己。
我从衣服边角抽出一根银针,一边帮他解手铐一边说:“哥怎么称呼?”
“叫我十四就行。”大块头说。
“这不是你妈给你取的吧?”我开玩笑地说。
他看着我的眼睛,打量一番,充满怀疑,想了一下说:“地龙兄弟中排号十四。”
对了,就是他,地龙帮。
当手铐被我解开的瞬间,我看到他脖子上有一条龙非龙,蛇非蛇的纹身,大概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地龙。
“排十四,那你们有多少兄弟?”我试探他一下。
“你问的话有些多。”
看来取得他的信任还需时日。
我走到车箱门旁,试着用力推了一下,有些晃动,应该是从外面栓住的,又用力一推了一下,外面有一个松脱的撞击声,看来白眼狼刻意安排的,没有上锁,只是拴住,估计用力连续推几下应该能推开。
我回到彪汉身边,假装很难的样子说:“外面加了两把大锁,你在这耐心等一下,我有办法解决它。”
“那快点!”大块头很紧张。
“好的。”
他越急我越喜欢。
欧阳厚黑第一准则,借他人之手将他逼到悬崖边然后拉他一把,博取别人信任。
我一边推门一边用余光观察十四的表情,他站来,来回踱步,一下走到铁网旁眺望外面,一下走到我旁边问我要不要帮忙,一下又坐原地。
正这时,车突然停住了,门也开了。
十四一见门开,立刻想冲出去,我拉住他,说:“再等一下。”
“车停了,他们会杀了我们,杀了我们,你懂吗?”大块头吓得想哭。
“别急,再等一下。”我说。
没到靶场就把他吓成这样,时机应该差不多了。
等了一泡尿的功夫,车继续上路。
我想,刚撞门那么大声押送的人没道理不知道,眼下车这么慢,停车肯定是他们给我暗送可以走的信号。
“哥,我们走。”我说。
我话刚说完他就跳了下去,我跟着也跳了下去。
跳车是每个步兵必须掌握的要素之一。
车速三十多码的情况下,没有经过长时训练,肯定有受伤,只是严重程度而已。
十四在高度紧张下一跳只是崴了一只右脚,我想他必定受过专业训练。
我跑到十四旁边,假惺惺地问:“没事吧?”
“崴一只脚而已,没事,我们走。”十四说。
一阵风吹来,看了一下天,哟,要下雨的节奏,在车箱里一直没注意,这一下车才察觉,天怎么这么黑。
“我看这天可能要下雨了,我们得找个地方避一下。”我说。
他一听跟着看了看一下天际,说:“是啊,哪里避?”
“你看这四周,石头多,山形各异,附近应该有山洞。”我说。
“走走看。”十四说。
走着走着,一道惊电横空划过,把整个大地照的通明。这一闪,让眼快的我看一个黑压压的山洞。
“前眼有洞。”十四说。
没想到他也看到了。
我扶着十四直冲山洞。
一道闪电,一声雷。
刚走到山洞,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好险,再晚一点就成了落汤鸡。”我笑着说。
十四抖了抖身上的灰,对我的话露出不屑的样子,等了十几秒,说:“谢谢。”
“什么?”我说。
“谢谢你救我。”十四很平静。
“举手之劳。”我说。
“是吗?”他突然看着我的眼睛,一脸怀疑,“你是什么人?”
我想了一下说:“什么什么人?”
“你当过兵?”十四说。
我想只有中国部队才能培养的出一眼就被人识破的军人,简直毫无掩饰感。
“是的,曾经当过几年。”
“为什么抓你?”
如果我的回答不合理,直接让之前做的一切付之东流。
“杀人。”我说。
“杀了什么人?”
十四一直盯着我的眼睛。
我假装苦笑一声,说:“杀了一名警察。”
他移开视线,没有咄咄逼人的架势,感叹一声,说:“终有一天我会杀光所有警察,为在天之灵的兄弟报仇。”
我不敢往下接话,怕一接话,言多必失。
过了几分钟,雨势渐小,看了一下天,比之前亮了不少,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停了。
“我看这雨下不久了,走吧。”我说。
十四看了我一下,没有搭理我。
我看情况有点糟,有恶化的趋势,便假装关心,“脚好些了没?”
依然没有搭理我。
我一看情况有些不对,二话不说,立刻蹲下,拿起他的右脚,左一圈,右一圈,三个来回,一声骨响,说:“走一下看怎么样?”
他试着走了两步,说:“谢谢。”
看来他不接受我的好。
安静地过了十分钟,雨虽然变小了,并没有停,我们的衣服都湿得差不多了。
“你打算去什么地方?”他突然问我。
我不可能明说要跟他去地龙帮,只能矜持说:“不知道。”
“你一身功夫,不如跟我走?”
“可以吗?”我说。
“饿不死你。”
终于上套了。
在这一会儿,内心别提多高兴,以为他不说话是对自己起了疑心,这下看来,至少现在是信任我的。
突然,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我与十四不由被这枪声惊的站起来,相互一望,我说:“不会靶场就在前面?”
“他们肯定知道我们逃走了。”十四刚平静下的心又紧张起来。
我明显听到他心跳的声音,说:“跑!”
山间都是石头,又下了雨别提多滑,有几次我都差点摔倒,而十四一直跑在我前,看来他确实针对不环境练过。
我自以步兵出身,走山路跟走平路一样,可与他比起来自愧不如,在几次下坡,几乎是他拉着我走。
一直跑,不知过了多久,雨已停了,在一片杉木林里,我实在没力气了,瘫坐在地方上,这简直比我当兵训练还累,说:“他们应该追不上了。”
我这一说,他跟着瘫坐下来。
“我们跑了多远?”十四有气无力地说。
“不知道。”
为了跟上十四,我几乎拼上了全力,哪里有心思记跑了多远。
“今天真把我一辈子步都跑完了。”十四说。
“哈哈!”我应承一笑。
“我们必须天亮之前下山。”
“为什么?”我说。
“下去就知道。”
我呵呵一笑。
突然,十四后面传来“沙沙”声,是蛇。
“不要动!”我说。
“什么东西?”十四紧张地站起来。
“蛇。”
我轻手轻脚绕到十四后面,果然是条蛇,还不小呢,这下可以充饥了。
我脱下上衣,展开,集中注意力,一蹬腿,扑了上去,抓个正着。这蛇好大的劲,花了不少时间才捏住头,一放开衣服,立马卷住我的手臂,靠!
我在地上快速摸起石头,往头上一锤,脑袋没了,鲜血喷了出来。
“哥,喝一口。”我把蛇拿到十四旁边递过去说。
“我怕那东西,你自己喝吧。”
“很补的。”
一开始我也很反感这东西,吃过一次,竟然迷上了。
喝光蛇血,剥掉皮,生吃了几口,不错,又递给十四,说:“要吃一口没?”
他见我吃得挺香,不由咽了一口唾沫,说:“味道怎么样?”
“吃一口不什么都知道了。”
他吃了一口,还没嚼就吐了出来,骂道:“什么东西,这么臭!”
这东西就像臭豆腐一样,闻起来臭,吃起来倍儿爽。
休息大概十多分钟,他执意要走,估计这会儿饿得不行了。
继续赶路。
一路上,十四没说过一句话,他不说话,我也不好多嘴,有时走他前面,有时走他后面,就这样,翻过几座山,在一条小河旁有发现一个住着十几户人家的村子,他如鱼得水一般,三步并作两步朝村子跑过去。
找了一个最偏远的人家冲进去,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发现一把斧头靠在墙上,十四拿起来掂量了一下,我看不懂他这是什么用意,便没有支声。
不,不,他这是,他往人家房门走去,不会是杀人?
我跑到他前面,挡住他说:“什么意思?我们是逃犯,不能……”
他打断我的话喝道:“滚开,我心里有数。”
我不能让他在我眼前杀人,一手抓住斧头,说:“警察也许就在附近。”
他瞪着我,松开斧头,说:“去给我弄个手机。”说着往我们逃来的路上瞅了一眼,接着说,“我得联系我的兄弟。”
这行!
“他们在这附近?”我问。
他点点头,没有吱声。
在江湖上走,最讲究的是一个“义”字,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有兄弟不要命的过来劫囚车,在两个年轻人说不一定时,就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他以为他做的很隐秘,在我眼里像玻璃一样透明。
“你等一下。”我说。
手铐可以打开,普通房门锁当然不在话下。
进入房间,房间里睡着一个女人,女人旁睡着一个小孩,看到她们,突然想起自己。为了生活更好,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外地打工挣钱,留下我与母亲。父亲走了之后,一到晚上总感觉天特别黑,不敢一个人睡,就像他一样,喜欢将头藏在母亲的腋窝下。
我在房间大致走了一圈,没发现手机,又拿起床边的衣物掂量了一下,依然没发现,这时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喜欢将贵重的东西塞在枕头下,伸进去,果然,在枕头下面摸到了手机。
当我把手机拿出门的那一刻,内心不由一痛,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以前自家进了小偷,明明看见,却不敢做声。
在门口,我对里面的女人小声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想她一定听见了,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明明看见,却不敢出声。
“哥,给。”
我将手机递给十四。
他接过电话,按了几个数字,放在耳边,没有回应,又按了几个数字,没有回应,又按了几个数字,“嘟,嘟,嘟……”
“在什么地方?”
电话终于接通了。
“好,我马上过来。”
我听不见那边说了什么,所以不知道要去何处,就跟着十四沿着小河边向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