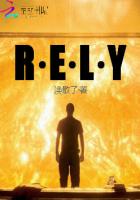王雱拖着大黑伞一路奔驰来到了张浩文力消失的地方。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
王雱微一挑眉,盯着地上的一滩血迹。
这摊血迹里还未凝结,显然是有着文力。
王雱嗅了嗅空气中的残留的气息,又用手指沾了点血放在鼻尖上闻了一下。
他收起了大黑伞,脸上面露凝重,紧握着伞把,环顾四周。
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这样做,看起来似乎很蠢。
但王雱不是一个蠢人,在太学中能够稳居前十的人不可能是蠢人,他只是在警惕,从空气中残存的气息基本上就能判断出这是张浩的血迹,这不得不让王雱警惕伤害了张浩的人是不是会杀个回马枪。
就这样过了很久,寂静的大街上依旧是寂静的,平静的令人感到心悸。王雱的身形悬停在街道口,脚未沾地,然后缓缓落下,青衫渐静,不再轻颤,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看着街边偶尔的一两个路人经过,王雱叹息一声,于是又撑起了大黑伞,寻着整个户县文力最高深的人而去。
他寻找的自然也只能是苏轼。
……
……
张浩在鬼杨柳前停下了脚步,有些震惊的朝着里边探了一眼。
幽静的鬼杨柳巷道里满是血腥的味道,杀声震天,人头落地就像西瓜落地般迸迸直响,无尽的尸体血液汇集到一起,顺着巷道汹涌而出。
残肢断臂在充满血腥味的风中颤抖,然后拖出道道残影,一群黑衣人手持弯刀,在小巷里上横冲直撞,一刀就将一个少年劈成了两半,血水冲天而起,像瀑布一般。
在巷道的门口,张浩抬起头来,看着发狂逃奔的男女老少从自己的身侧而过,看着杀红了双眼的黑衣人追袭而来,想躲闪,但是浑身上下却动也不能动一下。
随着喀嚓一声,张浩的大好头颅飞天而起,滚落在冰凉的青石板上。
在这个蒙着血水的地上,张浩的头颅似乎看清了那位很是让人惊艳的女子,**着身躯,在这群黑衣人的**中苦苦哀求………
“不,不要!”
张浩在梦中惊醒了。
张浩睁开了眼睛,望着天花板,松了一口气。
原来只是梦。
看着已经完全湿透的枕头,随后他试图用手拍拍自己的脸蛋,想让自己清醒一会儿,但随即全身上下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这股疼痛像是从骨头最深处传来的,如同被万箭穿心一般。张浩疼的几乎差点又晕死过去。
“公子,你先别动。”耳畔传来一道柔美的声音。
张浩勉强将头转了过去,疼的他一咧牙,但还是看清了面前人的模样。
果然是上次在鬼杨柳巷里边遇到的那个女子。
还是如同上次见到的一般眉如春山,眼如秋水,像月宫里的嫦娥下了凡尘,尽管脸颊上被不知道从来的泥土弄的黑不溜秋的,但一颦一笑之间还是让人能感受到第一次见面时的绝代风华。
“姑娘如何称呼?”张浩想虚空凝笔,凝了半天,却丝毫感受不到体内哪怕一点点的文力,看来也是被下了什么药了。
“公子你先别动,你伤的太重了。”少女在一旁看着张浩的举动劝阻道。
“叫我烟葭就可以了。“
张浩抬头张望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像是密室,两丈方圆,四处没有一处缝隙,只有最上方有着用铁锁锁住的出口,有一个悬浮在半空的铁盘,上面呈着点食物,看着是用来送食物用的。
张浩不由的苦笑了一声,这布置几乎是缜密到了极点,先是重伤自己,再下药让自己凝不出文力来,自然就爬不到上面的唯一出口,而就算万一凝出了文力,也不知上面的情况如何,想逃出去几乎是千难万难。
“姑娘,他们没有为难你吧?“张浩看着烟葭的俏丽脸蛋,试探性的问道。
“暂时没有。“烟葭叹息了一口气道。
她知道自己的面容对于男人的**力,原本被绑架的时候就已经作好了自尽的准备,好在这些黑衣人不知为何没有对自己动手动脚,反而让自己下来照料这位公子。
她听说过此人的名字,是苏大学士的弟子,也曾见过一面,至少看起来风度翩翩,又身受重伤,毫无还手之力,远比在上面的狼窝虎穴要好上许多,也就没有拒绝。
张浩看着密室岩壁上摇曳的烛光,带些道歉的语气说道:“这次怕是我牵累你了。”
“是祸躲不过,冥冥之间自有定数,烟葭可能命中就有这一劫,公子不必如此客气。”烟葭淡然道。
“烟葭姑娘说的有理,倒是我落了俗套了。”张浩哈哈一笑,但眼神中却尽是苦涩。
“听你这口气,姑娘像是精通佛法?”
“精通算不上,只是家母经常去佛寺上香,也经常在家里面唠嗑佛法,小女耳濡目染之下,也学了一点罢了。”
张浩哦了一声,没有什么兴趣继续谈下去了。
大宋儒学才是正道,读书人以其他学问为偏学,虽说佛学在大宋有一定信徒,但是在儒学的压制下始终成不了气候,反倒是西夏吐蕃大理三国佛学昌盛,但是西夏与大宋已经打了数千年,无定河边的骸骨怕是已经化成了沙子了。
昏黄的油灯灯火拖出两个长长的影子,映射在烟葭和张浩的脸上,不由让人心生烦躁。
沉默许久,烟葭抬起了俏脸,朱唇微翘,问道:“小女有一事不明,不知公子为何会被这些人生擒?是得罪了人么“
张浩盯着烟葭的俏脸看了一会儿,觉得有些不大礼貌,于是转过头来,又是疼的发出了一阵呻,吟。苦恼道:“我也不知,在下从小一直和师父在山间隐居,只是受友人之邀,拿着信物去户县南蛮一叙,却没想到被人暗箭偷袭,连一招都没放出来就被生擒了。“
“何人给的信物?”
“客栈的掌柜。”
烟葭眨了眨如秋水一般的眼眸,好奇的问道:“可能是小女子想的太多了,不知公子是否真的“认识”那位友人,或者说那信物是不是真的?
张浩听出了烟葭语气中的其他含义,摇了摇头。
“那友人和在下独处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而且文力远在在下之上,若是想抓我早就有机会了,何必等到现在,更何况他身份尊贵,不可能做出这等事情来,至于那信物,在下能感受的到是友人的文力,应该是不会有错的。”
烟葭见张浩毫不留情的否决了两种可能性,也没有气馁,只是直起身子来,隐约露出粉色长裙下白生生的小腿,走到一旁将已经快要燃烧干净的油灯续满了油。
张浩知道现在的关键是自家根本不清楚到底做了何事就被若说得罪人,在县衙倒是得罪过那个现在连名字都记不得的秀才,可张浩不觉得他有这么大的能量来调动至少二甲进士以上的人来生擒自己。
望着周边严严实实的墙壁,又看着自己左臂和大腿上的纱布,张浩又是苦笑一声,这不由让自己回想起了八年前的时光,自己也是这么躺在床上的。
而且都是好看的女子在照顾自己,这不禁让张浩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慨。
晃了晃脑袋把这些不切实际的联想抛在脑后,张浩安静片刻,才又说出一句话:“姑娘,我来到这里大概有几天了?”
烟葭听到这个问题,不由笑了起来,声音宛如春风一般:“公子您莫非是糊涂了罢,这里暗不见光的,小女子也看不见太阳,怎能知道现在过了几日呢?”
张浩摇了摇头,盯着烟葭好看的眉眼道:
“这也未必,现在他们大约送了几次饭了?”
烟葭先是一愣,随机恍然大悟。
“若是一日两餐,现在已经过了十日了,若是三餐,则是七日。“
张浩长叹一声,没有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