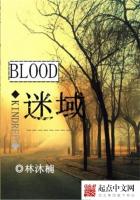我依稀的记得,那年我五岁,周遭的一切和现在相比都如破铜烂铁般的老旧,贪玩、懵懂、无知与欢乐应该可以彻底代表那个年纪。那是一个下午,太阳已经临近西斜,已经玩疯的我捧着刚从田地里摘来的野草冲进屋里,急着向我的奶奶汇报自己的成果以换取养着兔子的奶奶开心的笑容。
爷爷那时虽已年逾古稀,身体仍很硬朗,正在屋里倒背着手向奶奶说着什么。而急不可耐的我直冲向爷爷的背后,直到那把屠过无数牲口的小刀划过我的左眼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捂着脸在地上尽情的哭嚎,同时在屋里的还有几位叔伯,看到我的反应先是一惊,紧接着就冲向我,爷爷虽已老迈,反应却是极快,听到我在他背后哭喊,猛的转身丢掉手中的小刀就抱起了我,一把拉开我捂着脸的手仔细观看我伤在了哪里。
我还在爷爷的怀里嚎啕大哭,也能感觉到疼也感觉不到疼,此刻屋里的一众亲人们都围在了我的身边。大家观察了许久都没有发现我的脸上有任何的不适,不禁长出了一口气,还有一个年岁稍大的叔伯开了个玩笑:”幸亏孩子的脸没事,这要是伤了孩子的脸,以后孩子娶媳妇可就难喽!”
那位大伯还咧着嘴想说些什么,被半跪着抱着我的爷爷狠狠瞪了一眼,才低下头止住了声。爷爷操着乡音很重的土话问我:”娃儿!哪里难受给爷爷说!”我看着眼眶有些发红的爷爷和身体有些许发抖的奶奶,刚才心中那股欢乐早已烟消云散,又看向围着我的叔伯们,心中又有些欢乐与激动,当时的我们兄弟姐妹众多,能够得到除父母之外其他人的关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我又在爷爷的怀里躺了约莫半分钟的时间,感觉了一下身体,对着爷爷摇了摇头。
爷爷看我摇头意思是没事,又看了一下丢在地上的刀,已经岁月沧桑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奶奶也对着我笑开了怀,转身进了里屋,围着我的叔伯有几人长出了一口气,众人便各自回到自己刚才的地方继续刚才的事情了。爷爷把我从怀里扶起,又仔细打量我一番后把我领进了里屋,此时,奶奶已经笑着最里屋拿出了一大串葡萄,爷爷又一次把我抱在怀中,揪下葡萄,剥开葡萄皮一颗颗的喂我,葡萄在当时的北方可是堪比黄金的东西。
众人中包括我在内都没有注意到我红的不正常的左眼,只以为是我嚎哭之后的正常反应,吃完葡萄后的我满怀着一颗激动的心蹦蹦跳跳的心回到了家中,当时我的父亲为了一家的生计在外操劳,我的母亲还是在过了晚饭时间后才知道这件事情,又拉着我仔细看了一番又训斥了一番后才上床睡觉。
有些事情确实不愿回忆,此刻的我站在二十七楼的窗台边,现在正是阳光初照时,我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看着外面劳碌的人们,我的眼中浮现的是我操劳一生的爷爷、奶奶、父母和一众亲人们,而能表达我此刻心情的唯有脸上一红一白的两行泪水。
当晚的我其实是有着一颗异常激动的心情入睡的,被母亲牢牢的搂在怀中。而令我恐惧的是第二天,那也是另所有人所恐惧的,第二天一早,母亲发现我的左眼已经肿胀如球,眼皮已经被眼球分泌的黏液粘住再也睁不开。母亲紧紧的抱着我,跪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嗷惊动了所有人,我只能在母亲的怀中徒劳的安慰说:“妈妈!我没事!”
幸亏当时的交通已算发达,我先是被紧急送往了当时乡镇最好的医院,当时负责处理事务的医生全部都已过来,他们一看到我左眼的样子以及听取了发生的可能性就直摇头,他们不敢强行掰开我的眼睛,只能抱歉的说:”对不起,我们真的医治不了!”在母亲绝望的哭喊下我又被送往大城市的医院中,那是最好的一家的医院。
幸好的是他们在前几个月医治过一例和我差不多的病例,这在这个医院自创立至今是仅存的一例,但那个人远没有我的严重,只能借鉴着医治,而当时的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因为我已经耽误了一整夜的绝佳医治时间。我并不知道当时医治好的几率是小的那么可怕,也许是我的幸运,更不知道母亲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来签下病危通知书的。
由于我的特殊情况,我的家属被告知必须要进手术室,当时什么都不懂的我看着我的母亲以及好几个亲人一同进来,还以为是个好玩的游戏,一路笑着被推了进去。强光打开,照在我的眼上,那是一种钻心的剧痛,虽然那时我的左眼还没有睁开,剧痛之强,令如今已近而立之年的我回想起来都会忍不住全身发抖。
就在我不想玩这个不好玩的游戏,欲挣扎逃脱时,我发现我的四肢连着头部都被进来的亲人们牢牢按住,亲人们眼中只有强忍于眼中的泪水,我用仅仅能够活动的右眼看向按着我头部的母亲,淡绿色口罩下的母亲早已泪流满面,按着我的头部的手都在颤抖。
医生先用不知名的药水给我的左眼消毒,然后掰开我的左眼,在掰开的一刹那我能看到医生浑身都抖了一下,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也许是为了能够好好的手术,医生呵斥了我母亲一声,让她按稳点,这是手术,一点失误都不能有。我开始明白了一切,当时的我其实是什么都不明白。
右眼望去,母亲只是泪流满面的点头,望向医生的眼神中却满是感激。我绝望了,喊尽了所有亲人的最亲切称呼,所有人回答的都只是一些安慰的话语,以至于当时乃至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恨透了他们,认为他们是我见过最可恶的人。躺在手术床上的我也尝试着动了几下,试图能从中找出一个突破口,可惜一切都牢如钢铁。
我只希望这是大家对我开的一个玩笑,那光真的很疼。然而没过多久,一只在我看来无比巨大的针头出现在了我的左眼前,当时我的左眼几乎已经看不清任何事物,那是用右眼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