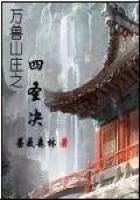如果不是因为要卖出那个单元的缘故,我根本不会再去那处小房子。
房子位于城市南面的主干道上,两幢并列的皇冠样双子楼,典型的投资性公寓,只有40年产权,升值潜力不大。如果放在现在,像这种样子的房子我根本不会去考虑。不过当年年纪还轻,手头并不宽裕,很容易被开发商宣称的“私藏小豪宅”之类的卖点俘获。听到“私藏”的字眼,总会联想到某种隐秘的幸福,个人紧握的秘而不宣的甜美。而我当时的情况,恰恰如此。那年苹果22岁,正是女孩一生中最甜美的时光,而我呢,也才28岁,以为人生就像铅笔画的底稿,任何不满意的线条,都可以用橡皮擦,轻而易举地擦去,或者用修正液涂涂改改,再画上新的图案。当然,最根本的是,房价确是相当的便宜,40平的一室户,总价只有18万,再加上当年只需付两成首付,而我那年可以一次性拿出的现金,最多也就这些。
走进门厅,当年感觉相当气派的大堂,现在看上去肮脏、破旧。由于不景气的缘故,大堂左侧被分割成很多十平米左右的小商铺,出租给商户,卖一些内衣、拖鞋、脸盆、扑克牌、方便面、关东煮之类,来买的无非是在附近电子厂打工的外来妹。而现在在大堂里晃悠的,大多数都是这个群体。两个保安无所事事地歪在大堂吧台上,对身边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大堂的右侧是电梯间,两部国产电梯,轿厢实在狭窄,摇摇晃晃的让人担心时刻都可能掉下来。幸好并没有。我曾经的公寓——到今天为止仍旧是我的,但自从苹果走后,我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位于8楼,听上去不错,但因为地处主干道,是实实在在的扬灰层,而且建筑和装修标准都低,房间也没有安装隔音的双层玻璃,晚上睡梦中,常常会被从此出城的载重卡车的汽笛声惊醒。甚至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听到楼下围墙边有个女人的啜泣声。哭声非常近,感觉就在耳边。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经历,你似乎停留在整座城市的喘息声中,不可自拔。电梯打开,里面有个17、8岁的女孩子,应该是从地下室上来的,戴着夸张的假睫毛,穿着假皮草和超短裙,一看就知道是在附近打工那种女孩。她扫了我一眼——给我感觉像被某部POS机扫过,瞬间显示出我并非这个层级的消费者——然后拿出一部大屏手机,眼睛紧盯着上面的显示屏,屏息凝神,手指飞快地在上面划动。我非常怀疑,像这种位于城市边缘的廉价公寓楼,现在已经下沉到某种类似快速消费交易所这样的境地。电梯在8楼停下,门在背后合上,可以感觉到女孩非常狐疑的目光停留在我肩膀上那种灼烧感。走廊里一片漆黑。我跺了跺脚,感应灯丝毫没有感应到我的存在。我只好掏出打火机,给自己点上一支烟,并借着烟头上微弱的红光,用钥匙打开门。
房间里没有想像的混乱。40平米的狭小公寓,进门左手过道上是简易的厨房,右手是卫浴,前面是卧室兼客厅,再往前是阳台,整个房间一览无余。地上有几张包裹家具用的发泡塑料,厨房水槽里留着几枚烟蒂,一体化的卫浴地板上也有一摊深褐色的痕迹,让人猜不透前一个租客曾经在这里干过什么。除此之外,一切还算齐整。我走过卧室,推开通往阳台的落地窗,外面的地砖和小容量洗衣机上都积了厚厚一层灰,似乎这里是很久以前爆发过核战争,而目前处于死寂的星球。我退回房间,打开床边的小冰柜,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当然,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一股混杂着某种腐臭气息的橡胶味。我回身看了看床垫,上面有几处颜色各异的痕迹,大多数像是血迹,蒙着灰,无辜的样子。我站在一边,嫌恶地看着它,不想和它发生任何关系,好像那不是我曾经乐此不疲地在上面翻滚的床垫,而是某种被遗弃的生化武器,只要和它一粘边,就会发生可怕的感染一般。我几乎是强迫症般地拉开床靠墙那边的衣柜,里面有一只不知被谁抛弃的连裤袜,萎在柜底。我看了它一眼,轻轻地把门合上。
我把烟蒂扔到厨房的水槽里,在铝合金的水槽底部摁灭它。没有什么要留下的。这个单元已经出售,明天就将交给新的业主。因此,今天是最后的确认。原本我不想来的,但中介说,好歹这只是走个程序罢了,你去看一下,万一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丢了就找不回来了。这屋子里的一切,对我而言,早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曾经有过的话。果真如此吗?
我又回到床边——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算是童心未泯也好,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挪开床边的床头柜,把它挪到一边,单膝跪地,俯身向床头靠板底下看去:果然还在,是啊,一个萎缩黑瘦的苹果核,被一根细细的长钉,钉在床板下的墙上。
我拔下长钉,小心地取下苹果核,然后靠墙坐在地板上,把它放在手心里,拨弄检视着:完全干枯了,份量轻得出乎意料,奇怪的是竟然没有发霉,在江南这样潮湿的空气中,这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当然,也可能早年曾经霉过,长满了白的绿的长毛,但一年一年过去,它安静下来,成了一具木乃伊——成为曾经见证了我们轰轰烈烈爱情的,枯萎死亡的惟一证据。
我把苹果核靠近鼻子闻了闻,没有任何味道。我又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用舌头包裹住。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无从解释。我只是想尝一尝它的味道。这是在失去她的一切踪迹之后,她的一切都从我生命中消失之后,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可以和她建立的某种联系。这里面不再有爱,也没有了怨恨,我只是单纯地想,再尝一尝曾经统治过我生命那么多年的那种吸引力,它当年是怎样一种滋味。
就在我嘴里,我可以感觉到,苹果核逐渐温暖起来,舒展开来,并且在层层叠叠的苦涩之中,竟然还透出一丝隐隐约约的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