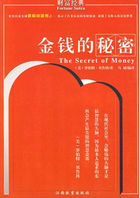忘情坐在七六阁阶前,刚刚踏步了一遍的“梦蝶”也没让他睡意渐萌。握着手中这个新得的酒葫芦,心中甚是开心,复又想到师傅说的那些话语。原来自己早已修道有所小成,只是这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却自然到自己都不知晓,这就要水到渠成么?不禁觉得好笑,只是这笑自己也不知为何。
望着天边的月亮,忘情拧开这个酒葫芦的塞子。一口仙酿银梭一线,落到他的口中。
“好酒啊!”
胸中感觉泛起一丝稍纵即逝火热,一下点燃了他的回忆。
忘情五人齐齐地站在漏滴台前的回廊周围,手里都拿着一个瓢,都是一样的大小,脚下都放着一个一样大小的装水用木桶,上面还系着两串麻绳。一个小鼎约莫拳头大小,里面插着五根寸许长的香,堪堪放置在近漏滴台的栏杆上。
秦梦久踏着几块突出水面的石块走上漏滴台,身后背上那个木桶,右手抓着瓢,立定后闭上双眼,呼了口气,双眼圆睁,再没平时弯弯的笑眼,轻声道了声“可以开始了。”话一出口,小鼎上的一根香就燃烧起来,芬腹浓郁。
同一时候,好多水滴落了下来,秦梦久身子一动,英气勃发,感觉脚下尽是千军万马,眼前皆是万骨朽枯。小嘴微抿,“梦蝶”一踏,手中“穿花”衔瓢不停地舞动中,接着那些下落的水滴。
香冒着香烟,一阵阵地鼓舞着她。忘情四人在回廊看着,心随她动。
秦梦久一步踏出,本是斜斜地偏倚,却直直地前进,手中瓢也是不停,滴溜溜地上下起伏,一滴滴的水珠儿就落了进去。落于身旁的水滴在她地挪移奔袭中尽归瓢中,水瓢往后一靠,就将水倒于身后桶中。
秀目圆睁,精光大作,轻喝一声,身影在高低不平的台上俯仰登降,感觉她手中拿的不是一个水瓢,更像是一根长毛,一突一刺更是残影簇动。接住的水滴越来越多,满了就倒于桶中。
忘情四人在台下看着,都心底冒出一种秦梦久在行军打仗一般,她就像一位冲锋陷阵、铁骑踏破山河的将帅一般,“梦蝶”那潇洒婀娜的步伐在她脚下倒成了节度容与的雷鼓,一步一鸣,裹挟千钧气势。
越战越勇下,忘情几人感觉水滴下落到秦梦久身子附近都缓缓一滞,被她瓮中捉鳖手般一任横扫。
桶里水渐多,香渐燃尽。终于,都停了下来。
秦梦久走下滴漏台,屠之伸手帮忙放下水桶,未满却也不少。
秦梦久呼了口气,想必对自己的发挥还是比较满意,毕竟这是第一次这般施用“梦蝶穿花”。
屠之接着她的顺序上到台上,第二根香一燃,他也就动了起来。
一本正经的脸上现在更是一柜子的正经罗列着。屠之一步踏出,一个大步跨过一大段距离,身法是很潇洒,可被他如此直接地冲淡了。水瓢从后至前规规矩矩地划出一道痕迹,水滴尽归里去。脚一落地,又是一个转身,折返向另一方踏步而去,水瓢仍是规矩地又一道痕迹划出。屠之就在台上一步一转身地腾挪着,手中水瓢不停,往往都是算计恰当,一伸出就是一一水滴相继而入。
忘情在下面看着屠之,感觉师兄和台下的石头都是一般无二,方方正正的石头,相当稳固。
没一会儿,屠之就结束了。桶中的水比秦梦久少了些,毕竟他那样的方式舍弃了太多机会。屠之也就咧嘴笑了笑,也无他想。
谢邪就上了台去,额前斜飘着的头发无风轻扬起来,双眼难得严肃神色。香燃身动,脚下“梦蝶”踏出,身法却是诡谲邪曲,简直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身影在台上划出各种的曲径,可偏偏速度奇快,在空中一个转身就咋现到另一个石头上,可手中“穿花”明显很是生疏,水瓢常常错过水滴。谢邪眉头一紧,转而眼珠一转,有了应对。只见他更加加快了步伐,只是手中水瓢倒没了那么频繁地递出,背后的水桶随着斜返无常而摇摆微动。他竟一心二用,用水桶的大开口去弥补手中“穿花”的劣势。谢邪一看这法子有效,速度又爆增。忘情四人在下面看着他在台上走着所谓的“弯路”却追风赶月一般掠过残影,神出鬼没地四处挪移。
谢邪走下台来,桶中水倒是前三人中垫底,他嘿嘿地笑着,相当满意了,不过心里却暗下决心,“穿花”得认真修炼并掌握,更不得嫌弃它有些娘们儿。
云紫婵柔柔弱弱地走到台上,感觉背上的桶和手中的瓢都能压弯她身子一般。
她身形一动,碎步挪移,神态甚是柔美,身姿却是娇柔,若曼妙轻舞于九天之上,若娉婷环鸣于碧波之间。多姿而缓缓的身影,或斜倚阑干望断天涯,或撑伞水边一方伊人。那慢慢的步子,却真不是慢慢,而是不紧不慢有度有持。
过了一会儿,她姣好面容挤出一丝愁眉,大煞此般身形。却也不虞有他,左手并拢举指至眉间,仿佛要赶走愁容一般。素指一一张开,一只梦蝶就这么出现。
除了谢邪的另外三人都是震惊的神色,竟然这儿使用“梦蝶”,对云紫婵心生佩服。所有的功法和招式法门会也仅仅是止于会,真正地掌握以及运用才是道。只有平素多加积累,待到湍流险阻之时,才省下苦思对策,才会天马行空地飞来一笔。
梦蝶一出现,愁容就不见。只见云紫婵身影更渐缓慢,可曼妙间水瓢却稀奇古怪地接着了很多水滴。梦蝶就乖乖地在她头顶扑扑蝶翼,五彩斑斓地鼓舞着她,星光点点,她身上著满花衣,姣好的面容更添几分灵与神。
香尽,她双手向下立定,花衣不见,梦蝶不再,只有她微微地笑还停留在嘴边。
云紫婵桶中的水几乎满了,比秦梦久倒是多了寸许。
忘情闭着眼在回廊闪现了几幅画面后,就走上了滴漏台。
只见忘情一开始就左手半圆一划梦蝶乍现,脚下“梦蝶”踏出,手中拧着水瓢“穿花”不停。不一会儿,梦蝶摇落的星光就撒满全身,花衣穿在忘情身上却那么相宜,毕竟他的小脸甚是粉雕玉琢。
忘情想起了早上徐师叔的“考验”,试着分心用左手改变水滴的落向,让它们偏折到水瓢里。尝试了几手,渐渐熟悉起来。这时双手上下翩飞,周遭曼挪。水瓢在手中也是或前递或回转,有如臂使一般。
看着那落下的雨滴,毫无章法可言。忘情却有如神助一般福至心灵,抓瓢若笔,浅浅斜斜地从左至右一书而就。
对,就是这样。忘情心神沉浸在“走墨著情”中,眼前水滴缓如字句,右手“穿花”不停如挥翰。余光一扫,香快燃尽。
赶紧将水桶置于身前,水瓢搁一边,两手手掌朝下平伸,往下一叩,水滴噗噗噗地落到桶中,却是满了。功收,蝶已不见。
忘情刚一下来,就发觉师兄师姐们用一种狂热的眼光看着他,顿觉有点脸红。毕竟自己最后上去,可是占了不小便宜。
这也无需比较,忘情桶中水最多。秦梦久他们四人都过来拍拍忘情,脸上也没不甘的神色,都是比较欣慰,毕竟他需要比他们付出更多。他们可是看过下雨天忘情那惨白无一丝血色的脸,也听过忘情昏睡时的哭泣,也看过他抱书细嚼于夜明珠下的炯目。忘情嘿嘿地笑着,接受着大家对他的拍拍打打。
正在这时,一阵不合时宜的笑声传来,打破了此刻的温馨。
“哈哈,哈哈。”
谢邪忽地觉得好丢脸,不因有他,正是他师傅徐缓的笑声。另外四人也听了出来,都用一副“你们真是一对师徒”的眼神望着谢邪,谢邪更觉丢脸了。
“我赌赢了,哈哈,我赌赢了。哈哈,我好久都没赢过杜师兄了,这次……”
“可师弟你没和杜师兄说你赢了,会赢什么啊?”正是莫纤纤的声音。
“没有么?苏师兄我难道没说这个么?”
“我是和他赌了物什的,你的话,的确没有。”
“啊……啊……我不甘啊。”
“愿赌服输,这个就给你的乖徒儿了。”杜绝虽输了,却也没见他丝毫沮丧。
“忘情,还不谢过你杜师伯。”苏世的声音在忘情耳边响起。
忘情赶紧对着听音厢鞠躬一谢,恭敬地道了声“谢过师伯。”
“不用,你们这些小家伙比我们当年还厉害,哈哈。走,去乱笔老头那儿喝酒去,我们就别杵在这里了,小家伙们就自己玩去吧。”
“走!”徐缓声音宏大,估摸着想把乱笔长老一下喝成家徒四壁。
“忘情,接着。”
话音刚落,一个酒葫芦就从听音厢飞到忘情身前,忘情伸手就抓住。这个酒葫芦与乱笔长老所赠甚是不同,玄色质地显得有些深邃,表饰卷云如浪花朵朵,葫芦腰身上缠着朱红丝带,撇下两溜,红绳一段系在丝带上,另一端绕在了酒葫芦塞子上。
“这是师傅那宝贝酒葫芦,叫‘玄湖’,听师傅说可以装三百斤酒,而且只要打满酒装进去,就可以自行酿酒,端得是个好宝贝。”屠之笑嘻嘻地说着。
“打满酒装进去,还需要酿酒么?”谢邪觉得奇怪。
“不是这意思,即便是俗世里的酒放进去,差一点的酒放进去,玄湖都可以酿出美酒仙酿来。”
“哇,小师弟你以后可以去卖酒了。”
四人又觉谢邪和徐缓真是一对师徒,感觉想法都很奇特。
“要不,我们也去喝酒,反正师傅他们都去喝酒去了。”谢邪即刻想到,尔后四人都望向秦梦久,后者抿着嘴细细想了一会儿。
“嗯,就这么决定了,别喝多了就行,刚好大家也好交流下最近所学。”秦梦久大手一挥,五人就快快乐乐地朝听音厢走去。
五个水面不一的桶放在那里,静静地无得一丝涟漪;五根香齐平平的一般高低插在小鼎的香灰里,像起誓一样行同言致,静静地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