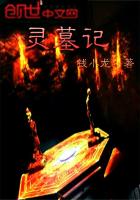自从上次兴贵叔叔过来,和爸爸一闹,我渐渐发现父母对我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妈妈开始带着我去百货商场选购一些时尚的衣服、鞋子,并开始时不时地给我点零花钱。爸爸也不再指挥我做任何事情,甚至晚上起来上厕所,也不会再推开我的房门看我在干什么了。我不知不觉中在父母眼中彻底地长大,平日里去同学家串串门、打打电话、看看足球什么的,深更半夜回来也没事。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和独立,在我内心里有那么一点适应不了,虽然我表面上自顾尽情地享受着。
升入高三以后,学校里功课抓的非常紧,除了吃饭、睡觉、放学路上,都基本在埋头做着各种卷子,第二天上课跟着老师一题一题地修改。我的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上游,但想从滨洲这样的小城市考进好大学,还得削尖脑袋去挤。回到家后,吃过晚饭便开始枯燥地一遍又一遍钻营着老师们出的各种变化无穷的难题。
这一日,爸爸妈妈吃完晚饭后出门散步去了,也就这么一会儿功夫,我可以放下书包,看看漫画书、发一会儿呆......我正兴高采烈地从书桌抽屉里最底下抽出藏着的漫画书来,呼啦一下带出了一个红色封皮的本子,黏住了书皮。这,不就是宁古渡口的瘌痢子送我的吗?我漫不经心地又放在手里打开来,这一次,我被他落款留下的CALL机号怔住了。心里一阵冲动,想用家里的电话呼下试试,也不知道这家伙现在过的怎样?顺便问问这个本子到底怎么神出鬼没地会溜进我的包里......我一看墙上的挂钟,爸爸妈妈也就刚出门没多久,趁着这个空档,我试试?
我提起家里的电话,照着本子写着的号码拨了过去,是个自动台,通了以后提示我挂电话,等候回电。我若有所思地放下了话机,手里攒着本子,开始在客厅里踱起步来,一边思索着待会说些什么,毕竟是长途电话,贵的很,得好好组织一下。我这一来一去把客厅前前后后走了不知多少趟了,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响,可电话一直都安安静静地一点动静也没有,可能是瘌痢子在干活吧,或者没听到,哎!算了算了,这陌生号码又是长途的人家也不一定回呢。正自己安慰自己,爸爸妈妈散步回来了,推开门看见我一个人灯也不开地站在客厅,妈妈吓了跳:“平一,开灯!黑灯瞎火地站那干嘛?”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灯已经亮了,爸爸不知什么正朝我走过来,我赶紧把本子卷成个筒,双手背过身后藏了起来。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向我投来了一道冷漠的目光,又径直走向了厨房。我早已习惯了,从我闹那次以后,爸爸对我就一直这样。我也没再理会他,连忙告诉妈妈我正在背书呢,开不开灯没什么影响,然后就故作镇静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门一关上,我的心口扑扑直跳,心想自己也太莽撞,现在好了吧?爸爸妈妈回来了,一会儿瘌痢子别真的打过来......到时候我当着爸爸妈妈面前该怎么说?
正铺开厚厚一沓卷子,嘀嘀嘀—嘀嘀嘀—门外传来刺耳的电话铃响,我心一凉,完了,怎么办?赶紧起身贴在门上听,刚想了两声,爸爸就提起了电话,传来低沉的声音:“喂!哪位?”接下来一阵安静,只听爸爸嗯,嗯嗯的在作答,我心里一阵发毛,又有一丝侥幸,可能是别人打的吧。正想着,咚咚咚,耳膜震得生疼,爸爸敲着我的门,我赶紧扭开门锁,爸爸一脸惊诧的表情对我说:“平一,你小学同学找你说,老师生病了一起去看望。”我连连应道嗯嗯,嗯,来到电话前接了起来,耳畔传来细细尖尖又带着兴奋的声音,“平一,我是瘌痢子啊!你CALL我哩,我一看滨洲的号就知道是你哩!”我这一听,不禁浑身一个哆嗦,真的瘌痢子回过来了,连忙假装应付起来:“是啊,好啊,知道了!都有谁啊?”电话那头瘌痢子嘿嘿笑了起来:“你小子真能装哩,比我还能哩!好了,我知道了,有空CALL我哩,那个本子把你吓到了吧?真不容易哩,我还有事,多联系啊,平一!”我耳朵里听着,嘴里哼哼哈哈应付着,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直到放下电话,我才感觉额头上居然冒出了汗珠。赶忙用袖子一擦,再转过身来正打算进屋,身后传来爸爸的声音:“平一,进屋赶紧写作业,这些人少说两句。”我一边关上门,一边应道:“好了,我知道了,同学哩!”心想,还好爸爸没有发现我慌乱的眼神,不然盘问起来我两句话就会漏嘴,再不小心扯到宁古渡,今晚肯定消停不了了,宁古渡!成了我和爸爸之间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
第二天一早,我正吃着早饭,一边拿着本书瞅着,妈妈耸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这才抬起头向妈妈望去,“平一,你们班主任上次家长会说鼓励你们高三冲刺期间住校哩,你今天学校里申请一下,回头我和你爸爸给你准备铺盖。”我还以为听错了呢,当时爸爸妈妈可是坚决反对我住校的,怕我高三冲刺时期住校卫生习惯不好生病。难道和昨晚的电话有关?嫌我在家里分心了?管他呢,我连连应了几声好,早就想住校了,班里几个玩的好的都住校,这样可以吃住一起,集体生活多好!
放了学,我如愿以偿地被班主任分到了班级的寝室,一进门,屋里一个人都没,同学们都去食堂打饭了,我赶紧用力把铺盖往床上一扔,抓起饭盒就撒开腿往食堂跑,一路上听着调羹在饭盒里丁零当啷的响声,心里别提多美了!
晚自习结束后,我一个人顺着教室门外的走廊,兴奋地一间一间教室数过来,趁着还未熄灭的日光灯,不时还伸进头去好奇地望一望,看看别班的黑板报。一面又扭头美美地欣赏走廊外校园的夜景。白天的树林、水泥走道、远处的小山坡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又分外陌生,夜幕下,除了阵阵响起的虫鸣,整个校园大地渐渐地安静下来。
我一路吹着口哨进了寝室大楼,门卫大爷已开始提着手电筒在准备关门前的四处转悠,我赶紧随着晚归的人群挤了去,别看这大楼现在变成寝室了,显得老态龙钟。但在半个世纪前,那可是滨洲最好的教室呢。光看看外立面上的布满苔藓的青砖和宏伟伫立的英式教堂风格,就知道了。在历史遗留下的岁月里,几个时代的人在这进进出出,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进门左拐就是通往班级寝室的走廊,并不用爬楼梯,拥挤的人群顿时少了一大半,在这古老的走廊里吧啦吧啦地回荡起各种脚步声,拱形的天花板上亮着被铁丝罩住的昏黄的灯,透着灯光,看见两边墙壁上石灰涂层已经斑驳开裂,仿佛随时会掉下一块来。脚下踩的是青石铺成的走道,湿滑中仿佛漾起浑浊的发霉味道。就这样,同学们陆续进了自己的寝室,脚步声越来越清晰,快走到我的班级寝室时,身后就只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我不禁回头一望,好家伙,一个在灯光下都能黑成一团的人,胸前捧着被子,手指勾着热水瓶和一个网兜,胳膊肘里又挂了个书包,背上还驮着个蛇皮袋......却也步伐轻盈,有条不紊,见我看着他,便冲我嘿嘿一笑,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一时间,已走近前来。我凑近仔细一看,这人个头比我高出半个头,短平发,眉毛和眼珠子几乎看不出来,和黝黑的皮肤混为一体,倒是一头大蒜鼻子塌在了中间,上下嘴唇各翻各的,又厚又长。“同学,你住八班的寝室吧?”他居然显露出了几分羞涩,我连忙应道:“嗯,嗯,我就是八班的原平一!你是?”“你叫我萝卜勺就行,我从小就黑,我妈说我像腌出来的萝不,嘻嘻......”说完用膝盖顶了一下手指勾住的网兜,一个脏兮兮和他差不多黑的足球突然在我面前弹了起来......“我是九班体育专业的,班里住校的少,没单独的班级寝室,学校就把我发配到你们八班来了。”我一听,连声道:“欢迎,欢迎啊!萝---萝卜勺,哈哈!”就这样,两个在同一天住进寝室的小伙子都大笑起来,几分钟前的陌生尴尬早已消失地无影无踪,年轻人真的就是这么的无忧无虑。
萝卜勺的床位和我正好隔壁,稍作安顿寝室里就熄了灯,只剩屋里这几个小伙的心跳咚,咚,咚地弹拨着这看似漫无边际的黑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