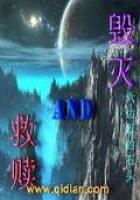楚衍的“叛逆”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心情好时,我会大发善心给他讲那让他云里雾里的太阳高度角;心情不好时,我就在后面狂踹他的椅子。
通常情况下,楚衍和他的桌子都会被我踹飞,然后,他一边扶桌子一边跟前排同学道歉,再回过头看我,温和地问:“怎么了?”
而我的回答永远都是:“没事,给你测测听力。”
因着楚衍的存在,我没有再四处惹是生非,也没有再纠缠卓远。他和“小白兔”在期末时正式恋爱了,消息传来时我正好考完最后一科。我收拾完东西准备回家,楚衍破天荒主动问我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这是楚呆子第一次主动约我,我当然不能拒绝。
楚衍是外地人,对宁安城不甚熟悉,于是,我充分发挥了自己欺生的本领,忽悠他陪我去逛街购物。
傍晚时,我决定去穿个耳洞。这是我的习惯,失去了在乎的东西后,我就会穿个耳洞以示纪念。
其实,割舍我们生命里的某些东西就像打耳洞一样,当时疼得撕心裂肺,时间一久就不疼了,有时甚至会忘了它的存在。
卓远之于我,必须成为一个耳洞。
可是,我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左耳从顶端至耳垂全是耳洞,穿耳洞的阿姨看了一眼直摇头:“没法下枪了。”她指着我只有一个耳洞的右耳说,“要不穿右耳吧?”
我想了一下还是算了,卓远还没有那么重要。
回去的路上楚衍突然问我:“现在还疼吗?”
我一怔,旋即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我忽然眼眶发热,竟有种想要哭的冲动。
所有人都知道伤口终究会愈合,却很少有人明白,有些伤口即使愈合了也还是会疼。就像我四岁时妈妈亲手在我右耳穿的那个耳洞,那是她留给我最后的记忆,让我痛彻心扉,终生难愈。
我指着旁边的刺青店,淡淡一笑道:“跟它一样,久了就不疼了。”
想到曾经差点把卓远的名字刺在手心里的举动,我不禁打了个寒战,然后冲着楚衍坏笑道:“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去把她的名字文在手心里,多浪漫啊!”
楚衍像看神经病似的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就走,耳根处却隐隐泛红。
一进入高三,学习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我依旧每天晒晒太阳、逗逗小学弟,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楚衍似乎也很闲,不论我在哪里逍遥总能遇到他,就连我去楼顶晒太阳都能与他偶遇。
他正坐在地上专心致志干着什么大事,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走过去看了一眼,顿时觉得天雷滚滚--他一个五讲四美的大好青年,不打球、不弹琴,居然折千纸鹤!
我忍不住对他鄙视了一番,他但笑不语。我懒得理他,专心享受我的日光浴。
我喜欢午后的阳光,它让我觉得一切还很美好。我刚走到护栏边,就被人从背后紧紧抱住。我们贴得那么近,我甚至听见了他胸膛里心脏跳动的声音。
“许珩,你别做傻事,他都已经出国了!”楚衍死死抱着我,要把我拖离护栏。
我一听他提起卓远,立刻火冒三丈,狠狠地踩了他一脚:“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其实,我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喜欢卓远,我只是太眷恋身边有个人对我好。卓远之于我,就像我溺亡时抓住的一块浮萍,我对他是末路时的依赖,而不是爱。
而楚衍竟敢在我心如止水这么久之后旧事重提羞辱我!我假装往护栏边挣扎:“你不说清楚,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以示清白!”
楚衍一听我要跳下去,把我抱得更紧了。他的下巴抵住我的颈窝,梦呓般低声喊我的名字。他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垂上,我的心里莫名一阵慌乱,故作轻松说:“你再不松手,我就喊‘非礼’了。”
闻言,楚衍像被电击了似的猛地松开手,连耳根都红得能滴出血来。我被他的模样弄得有些尴尬,微微移开视线,却发现被他踩得乱七八糟的千纸鹤,还有一地玻璃碎片。
“怎么办?”这简直是一脚回到解放前。
楚衍抬头看着我,温柔地说:“你没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