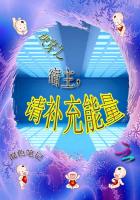金鼓长街,吕氏茶饼铺子。
“没办法、没办法。”邋遢道士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长长的醋黄指甲划过他见棱见角的颧骨,他想了片刻道:“小兄弟若真想……”
“哦?先生快说来听听!”
吕梁风的莲罗纹大袖纤尘不染,他恭敬地附耳侧听。
“办法就是,随我去修道!”
“我做不来。”
“修道很有趣的,你会活得比现在更健康、更长寿。”
“我做不来。”
“不用担心你的父母,每隔半年,我许你回吕家探亲一次。”
“我做不来。”
“我把我毕生的绝学都传授给你,不用怕,我很温柔的。”
吕梁风抽回耳朵正坐,面色严肃地拒绝:“谢谢先生的好意,可我真的做不来。”
邋遢道士急了:“为什么呢?别人磕头求我,我都不肯收啊!”
房间充斥茶饼的香苦,日头漏过方格花窗落地形成不规则的碎光。吕梁风浓黑眼睫微颤,他垂落冷色的宝石眸子,措辞回道:“我……还是想要娶一个妻子。”
邋遢道士拍腿长叹:“唉,冤孽啊冤孽!”
知劝解无望,邋遢道士展开黑糊糊的袖口,抖落袖上脏尘入白瓷茶盖。他一本正经地将茶盖交到吕梁风手上,拾起靠立门前的布帆,推门扬长而去。
“儿女情最苦,桃花债难偿。我见你慧根深种,才起意收你为徒,谁料你贪享图欢、执迷不悟?经此一别,你我无需再见了!”
道士嗓音幽邃,道袍无风飘迎。
吕梁风的眼光从道士远去的背影收回,投于手中一盖子来历不明的炭黑粉末上。这是什么东西?吃的?抹的?摆着瞧的?
不会是道士胳膊上搓下的黑泥条儿吧?
吕梁风小心垂面,想嗅嗅味道,一阵风过,粉末尽数由风吹散。
吕梁风本是极爱干净的人,看到棘手的瓷茶盖子恢复通透白亮,他径自舒眉笑了。也好,他瞧那道士举止怪异,兴许道行不高……吕梁风安慰自己想,成婚生子是平常事,凭他的条件,怎会娶不到一妻半妾呢?
“燕十,我们回家。”吕梁风的一笑,又引发对街一片女子的赞叹和晕厥。
燕十牵马而来,无意间发现吕梁风接近地面的衫摆处染有一块炭黑污迹。吕梁风利落上马,燕十伸手为少爷擦拭。可那污迹像是长在了上面,擦不掉。
“少爷,那人就是诅咒你有三千桃花命的假道士吗?”
“燕十,不得无礼,他是为我好。”
“鬼才相信!不要叫我燕十碰见他,见着一次、打一次。”
.
与大名府相隔万里的临安府,山脚茅屋,潋滟晴湖。
一方小茅屋院前,停着一辆整装待发的小马车。
“桃花。”四十余岁的妇人乌髻斜盘,面不施粉、眉不染黛,五官却异常端贵、清雅。尤其是她右颊挂着一汪不深不浅的酒窝,衬得她一颦一笑分外明动可爱。
“娘!”湖边应声跑来的少女眉眼偏细且长,两只眼角微微上扬。少女的外貌长得与母亲并不一样,但她清丽不凡的谈吐与母亲如出一辙。
“娘,你今日就要走了?”阮桃花看到阮母臂挂小包裹,有些惊讶地问。
“是啊,你爹在城东的码头等我。日落之前,我要赶去与他会合。”
阮桃花笑看阮母,她知道,阮母并不是她真正的养母。
哎,养母如何还分真的、假的?道理很简单,阮桃花有三个秘密,第一个是:她是穿来的人。
对于本体世界,她已记不得太多,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阮桃花在意外穿入“阮桃花”的身体后,认知、逻辑与记忆力随之大幅度下降至两岁女娃的水平。
大概是受脑容量所限?
“来,乖桃花,到爹爹这儿来。”
“咦?桃花怎么不动了?”
“娘!妹妹她拉臭臭啦!”
或是……
“啊,张口,哥哥喂你吃饭饭。”
“咦?桃花怎么吐了?”
“嘿嘿,你儿子喂桃花吃泥巴呢!”
又或是……
“桃花,你看这肚兜漂不漂亮?”
“爹,快来瞧,桃花长咪咪啦!”
“你个臭小子!”
有苦难言的阮桃花一度严重以为,她会不会是在穿越途中,遗失了某些身体重要零部件导致大脑受损、导致她变成了一个傻子?
呼,好在后来,她的脑子随着身体长了回来。
“桃花。”阮母立在明晃如镜的湖岸,对阮桃花说,“娘这一走,可能是半年、可能是一年……娘向你保证,至多两年,我和你爹定会去你姨母家接你回来。”
“娘。”阮桃花搀扶母亲的手臂,启唇一笑,“你和爹此去辽国,凡事要小心,不必担心女儿。我在吕家好吃好喝的,保不齐不想回家了。”
“胡说!”阮母停步车前,“把你送去吕家作‘假儿媳’是权宜之计,为了障人耳目、方便你八姨娘就近照顾你。你和吕三公子的婚事,岂能当真?”
“为啥不能?”
阮桃花鼻梁一根细骨,鼻梁下嘟起唇瓣,吐出的不是任性的嗔怒,而是玩笑般的撒娇:“噢,我嫁进吕家门,夫君没死就出门,别人当我不守妇德、不是好女子,谁还敢娶我?舒舒服服地留在吕家里,作我的三少夫人多好!”
“呵,你啊!”阮母轻戳阮桃花的额头。
她这个女儿虽不是她亲生,却也放在身边养了十来年,二人之间简直比亲母女还亲。阮桃花的心性阮母自然知晓。女儿想得到的答案,总会想方设法得到,即便为之受苦、受难也在所不惜。
因此,阮母不能透露一丝她与阮父此去辽国的真正目的。她怕女儿接受不了。
群峦起伏,湖光飞渡。
阮母乘坐的马车沿着小径,穿入密林远去。阮桃花的雪眸眯成一双月牙,月牙满得汩汩溢出甜笑来。眼前画面勾起她熟悉的一幕记忆。
那是五年前。阮桃花名义上的小表哥、大她一岁的吕家三公子吕梁风,骑着一匹挂有黄铜铃铛的杂色小毛驴,在同一背景下消失不见。
“……桃花妹妹,我会娶你的……”
言犹在耳,少年嵌着宝石眼瞳的真切面容依稀可见,是那么蛊惑、那么深刻、那么——想让阮桃花对着他的人拳打脚踢一顿!
这是阮桃花三个秘密中的第二个。
.
阮母走后的隔天,阮桃花收拾了简单的行囊,独身北上。
按照阮母的遵嘱,她的行程隐瞒了所有人。不止养父手下百十条海船的商头和船工不知,养母这边频繁往来的亲朋也不知,连阮桃花即将“嫁”去的吕氏夫家都不知!
“桃花,你一个人,扮作男装,轻装上路。我叮嘱了八妹切勿声张。等你进了吕家门,权当自己是嫁去多年的媳妇,不要惹人注目……”
阮桃花觉得阮母的故事有些可疑。
阮母对她说:十多年前,阮父在辽地结下一门仇家,仇家近日找上门,扬言要血债血偿。阮父建议她们母女二人一齐避一避,但阮母坚持留在阮父身边、陪他去辽国了结这桩“冤仇”。
但阮桃花没有深究,因为她心里,恰巧也有瞒着阮母的秘密。
五年前,大名吕家的三公子来过一次阮桃花的家。二人互相倾慕,水到渠成地发生了……咳、咳。阮桃花守口如瓶,没有告诉任何人。吕梁风走前信誓旦旦:“桃花妹妹,我会回来娶你的。”
于是,阮桃花傻傻地等啊、等啊,眼看她过了桃李之年,仍不见人来。
托吕梁风的福,阮桃花一个待嫁女孩儿,先尝到了做弃妇的滋味。她不想嫁他了,她想冲到大名吕家去,对他说:“好啊,吃干抹静跑掉了?我叫‘阮桃花’,不叫‘软柿子’!”
正逢阮母提出便利的“请求”,阮桃花乐得答应。
前去大名府,先经汴京城。
自临安北上汴京,路途迢迢,却有一条捷径:坐客船,走汴水,天气好的话,只需七、八日可达。
阮桃花在海上,对着罗盘和星斗,是把行船的好手。一旦下了船,她的方向感变得,不大可靠了。谁让她跟着爹爹在海上生活的时日,比她在陆地的多呢?
那些村庄啊、石桥啊,在阮桃花眼中,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三转两转,好不容易已经转到了汴京城的脚下,阮桃花却走岔了路。
四望野旷,草薄树稀,一间欲歪不倒的小栈立在厚厚的黄土坎上。
“呼。”阮桃花手擦额边细汗。她从小跟着爹爹跑船,船上人各司其责,没空照顾她,阮桃花很小便学会了照顾自己。绕点冤枉路嘛,对她算不得什么苦。
“大伯,来壶凉茶。”阮桃花卸下肩头“叮当”作响的行囊。
“好嘞!”店家接应。
又渴又累的阮桃花提起桌上泥陶壶,豪迈地仰头猛灌几大口,顿觉通身清凉:“哈,真爽快!”
阮桃花掀开壶盖向壶肚子里张望,眼力极快的店家主动为她补上一壶,哈腰问道:“小兄弟,赶远路来着吧?今年不知是什么鬼天气,前日还冷雨打檐,今日就热气烤窗了。不如,来几个小菜,好好休息一晚再走?”
阮桃花又灌下两口解渴的甘茶,笑着谢过店家:“不了,大伯。前面可是汴京?”
“小兄弟要去京师?”店家殷勤指引,“喏,过了那条河,见着一个荒村,再走七十里,能瞧见京师的城郭。”
进了京城,很快能到大名。
一想到等待五年的男子触手可及,阮桃花放下几枚铜钱道:“七十里?不算远。”
店家翻眼看天,距天黑仅有半个时辰,这瘦弱少年莫不是要赶七十里地的夜、路?
小栈内除了阮桃花,没有半个客人。到嘴的生意吃不着,店家很是心急,正要对“少年”苦口规劝,两扇糟朽不堪的枣木门板被人从外推开。
“吱扭——”门扇怪叫,阮桃花随同店家引颈望。
门洞里空空如也,日落前的热气卷着道旁黄土浮上半空。阮桃花眼前一闪——那是她三个秘密中的第三个。
阮桃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