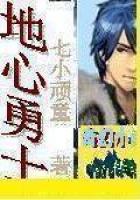即便是常年在飞鲈城地界讨生活的老江湖也鲜有人知道太素宫的存在。
太素山原本不是什么名山大川,夹杂在连绵群山中并不显眼,直到百余年前得道高人素问真人在此开山立派才有了太素山的名号,只不过之于向来排外的飞鲈城,即便是在三京之地如鱼得水的真人苦心经营数十年也仅仅只是挣得一方立锥之地,没能求得闻达,连知晓的人都屈指可数,之后传人几代,不温不火了百余年,虽说曾经也一度获得过几位达官贵人的赏识青睐,有过些许好光景,但最终还是不能如龙虎、天一等道门圣地那样香火鼎盛,绵延传继。
尤其是近十几年,本就香客寥寥的太素宫更是蹊跷地闭了山门,不再受附近信众的香火,一来二去,名声不响招牌不亮的太素宫几乎快要销声匿迹,即便是山脚下几个村庄的村民也不清楚山上的情况。
这一日,太素山上依旧门庭冷落,没什么动静,山门匾额已是明灭不清摇摇欲坠,云雾环绕的主峰伶仃崖上,几个身着文士羽袍的中年人正聚首在宫中正殿内,一个个愁眉不展,似乎是遇到了难事,坐在圈椅上长吁短叹。
“人呢?说没就没了?他是抱了丹的紫府真人?还是凝了天罡的陆地真仙,山上这么多大活人就没一个人看到他?嗯?”
坐在中间主位上皂袍黑巾的中年人鼻腔里一个“嗯”字生生哼出了余音绕梁的气势,让其余几个有资格坐进正殿的师兄弟都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一边暗道一声大师兄修为高深,一边悄悄把目光投向中年人身旁一个同样一身黑袍,面相周正的青年身上。
这青年见众人目光投来,就知道要糟,又得自己上去顶包,眉头拧得和麻花一般,他生性脾气温和,年纪又小,哪里敢忤逆众师兄,否则日后少不得被挤兑,只好小心翼翼整了整衣冠,轻轻咳嗽了一声,出来搭腔道:“大师兄,稍安勿躁,小师弟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虽说……虽说贪玩了一点,但事情轻重应该还是分得清的罢……”
青年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瞥向大师兄,见大师兄一张黑脸越发阴沉,实在是没信心再说下去,只好自顾自收了声,闭口不言。
“分得清?他分得清个屁……”大师兄显然是气急,颇为少见地爆了粗口:“和这小兔崽子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这几天安生一点别他娘的再到处乱跑,他倒好,明天就是冠礼了,现在偷偷溜下山,连个鬼影子都没有,道陵师弟你说说,这叫分得清轻重?哎,还指望着让他负剑游学呢,就怕到时候带下山的剑都让他拿到当铺给当了……”
大师兄轻叹一声,怒其不争的摇了摇头,面色凝重。
“师兄息怒……”青年见师兄语气松动,赶紧劝慰道:“小师弟虽说顽劣,但天资聪颖心思玲珑,在外头也断然不会吃什么亏的……”
“吃亏?我还会担心他吃亏?道陵师弟啊,你还是太年轻啊,在山上那么多年你何曾见到那个小兔崽子吃亏……只求他别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就要烧高香了……”大师兄显然是早已摸清自己小师弟的秉性,心中更是郁闷。
在座众师兄弟中入门最晚也是年纪最小的八师弟莫道陵自认与小师弟关系不错,刚想再开口为小师弟再辩驳两句,便被身旁的素袍中年扯住了衣角。
这素袍中年一脸漠然,倒是与他冷漠的气质相符合,他面无表情站了起来朝着大师兄拱手一揖,缓缓道:“师兄稍安,我这就让三痴去寻他……”
说完,素袍中年也不管大师兄如何应对,自顾自转身慢步走出太素宫,飘飘然拾级而下,一直到再也望不见他背影,剩下几个师兄弟才反应过来。
“二师兄到底是二师兄,玩的好一手金蝉脱壳……”
二师兄姓孔,平日里喜静不喜喧哗,话不多,凡是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因此又被诸位师兄弟私下称作孔有胸,他口中的三痴是个孤儿,性子和他一般,生在如今早已是一片废墟的龙莲城,父母家人都死于战乱,被当年恰巧路过的孔有胸救起,带上了山,也就随了他姓孔,因为被擅长占卜巫医之术的四师兄断为天生七窍只通其四,无惊、悲、怒三情,故而取名三痴,平日里有些木讷,不善言辞,虽说武道上天分极高,但在诸位二代弟子中人缘却是一般,没什么朋友,只和他的小师叔还算是投缘,因此常常被年纪相仿又生性跳脱的小师叔带到后山猎些野味,小到野兔飞鼠,大到熊罴猛虎,几乎都已经遭过他的毒手,每次大师伯责罚下来,也是他傻呵呵的受着,从来不迁怒到小师叔头上。
三痴从小拜在孔有胸门下学剑,九岁时就得入剑庐求得一柄西阙,长六尺,柄长七寸,刃宽六寸四分,重逾三十斤,比起寻常大刀都要重出不少,背起来看着像是块重盾,却能在他手中运使如龙蛇灵动,举手投足间有攀龙掷象的力气,按照四师兄所说,以三痴的根骨,每通一窍,武道便妥妥能再上一个境界,如今三痴已是十四的年纪,身高有丈余,体形雄壮如天神下凡,武道也已踏入一品,稳稳当当的金刚相高手,不说摆在外头走到哪里都是被当做祖宗一般供起来,即便是在怪胎云集,以“轻天下武夫”自诩的太素山二代弟子里,也能牢牢占据三甲的位子。
孔有胸从伶仃崖上下来,脸上挂着平日难得一见的自矜神色,回到太素山中最为奇骏的朔望峰,找到正在草庐中打坐入定的三痴,一个巴掌把他拍醒,就让他带着剑下山去找他小师叔,而且还特意叮嘱了一番,说此次不同往日,就算用绑的也要把小师叔给绑回来。因此健步如飞远看好似道家缩地成寸神通一路下山的三痴身上除了一柄用粗布包着依然难掩锋芒的西阙之外,还多缠了一捆浸过油过过火的二指粗麻绳。
飞鲈城离太素山约有六七十里路程,一半山路一半官道,如果是普通樵夫走上一圈怕是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即便是官驿快马也要小个把时辰,不过对于体力脚程都堪比牲口的孔三痴而言这六七十里路程不过是一炷香的时间,背着三十斤重的巨剑转眼到了飞鲈城下,也只是面色微红,运起山上基础的吐纳口诀《三五都功箓》转瞬间就能平复。
飞鲈城地处青州要冲,是洪武王朝四十八枢城之一,百十年前王朝鼎盛时,穿城而过的燕水河上商船花船客船往来日夜不断,豪客富贾于河上宴饮,倒酒入河,让飞鲈城满城飘香,如今虽然在税赋重压下有些不复当年的盛世景象,但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十几个传承百年的世家还是能撑起飞鲈城这只瘦虎的骨架。
孔三痴背着一柄西阙自然不可能从城门入内,他为人木讷,但毕竟不是真傻,虽说王朝法令并不禁绝民间私带兵器,但这也指的是文人士大夫的细巧佩剑,不是他背上这种大杀器,自古以来侠以武犯禁,如果他就这么大摇大摆背着西阙入城,只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无数武林人士视作跗骨之蛆的锦衣卫盯上,所以三痴最终寻了个无人的角落如同猿猴一般轻巧攀上城墙,随后直奔飞鲈城最大的青楼倚翠轩。
倚翠轩紧靠寸土寸金的南门巷,环境清幽,四周都是达官显贵豢养小妾或外室的私宅,偶尔来宠幸一番,也都是脚踏飞鲈城抖三抖的大人物,能在此地树立起如此规模的产业,背后的能量自然不会小,传闻洪、赵、顾等几大飞鲈城世家都有参股其中,因此多年以来从不曾出过什么乱子,孔三痴已经不是第一次来此地寻他的小师叔了,算得上熟门熟路,才走到倚翠轩门口,就有眼尖的迎客龟公认出他来,一脸热情的迎上来。
这倒不是因为孔三痴是什么出手阔绰的世家子,纯粹是借了从不把银子当银子花的小师叔的荫头,事实上整个太素山上除了他小师叔以外上至山主师伯下至三代记名弟子几乎都是身无分文的状态,反正都是些世外高人,要这些黄白之物也少有用处,就连修建草庐都是几名二代弟子亲自动手,不请帮工。
“孔大侠,好久不见,可是来寻苏公子的……”迎客龟公满脸堆笑,见风使舵见人菜下碟的功夫自然是他拿手。
小师叔姓苏,单名一个怨字,尚未置字,孔三痴点了点头,随即跟在龟公后头进了倚翠轩。
由于还是下午时分,因此倚翠轩并没有多少客人,只有一些自命风流的文人雅士坐在厅堂内听曲,抚琴的姑娘并非当红头牌,但也算样貌清秀,琴艺不俗,只是匠气稍重,偶尔与几个自她出道时就殷勤捧场的恩客目送秋波,也是妩媚的很,若是头一次流连这烟花场销金窟的雏儿只怕已经是被迷得晕头转向神魂颠倒了,毕竟自小就被买入青楼调教驯养,魅惑迷人的本事都不会差。
“没卵子的怂货,敢和爷爷抢女人?也好,让爷爷教教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三痴才走进厅堂,还没来得及望见这抚琴的姑娘究竟长个什么模样,就先听闻楼上的雅室内传出一阵粗鄙骂娘声,以及今日驻轩的红牌师襄姑娘的尖叫,这让他身旁的迎客龟公立马变了脸色。
虽说倚翠轩说到底还是做皮肉生意的勾栏场子,但比起那些纯粹只做腌臜勾当的青楼来,也算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即便是有酒后争风吃醋的客人红了脸,也顶多是叫嚣两句“有辱斯文”之类不痛不痒的话,随后在其他地方找回场子,绝不至于骂出粗口,更不会撸起袖管打架,能上二楼雅间的自然都是不缺银钱的金主,况且这个点,在雅间里头的也只有两拨人。
一波乃是从西边雍州来的豪客,出手大方,但脾气模样显然都不是好招惹的主,而另一波,自然就是孔三痴他师叔了。
孔三痴听见西北口音浓重的骂声,下意识抬起头来望向二楼,却见到一个身高足有九尺的虬髯大汉正双手举起一个穿着文士袍子的消瘦青年,一把丢下楼来,这一下若是摔实了,只怕以这青年的身板免不了伤筋动骨,若是摔得不巧砸着了脑袋,只怕连性命都要交待在这里。
什么深仇大恨竟然需要下此狠手。
咦,这被丢下的不正是自己的小师叔吗?
孔三痴看清了已被虬髯大汉用力掷下的青年的脸孔,一张有些木讷的脸上当即露出厉色,说时迟那时快,也就是转瞬间的功夫,才进厅堂距离二楼还有三四丈远的孔三痴脚下一踏,震得整座倚翠轩都是一晃,雄伟的身影眨眼间冲起,一把接下了小师叔。
这几乎是江湖中传说八步赶蝉一般的身法让整个倚翠轩都为之一振,不仅闹事的虬髯大汉一脸惊愕,就连那些个纯粹外行看热闹的文人都是一阵惊呼乖乖这世上原来还真有飞檐走壁的高手,也只有那被救下的青年一脸淡然跳下来,一改之前雅间内灿笑表情,就好像刚才差点丧命的不是他一般对着孔三痴沉痛叹息道: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年月,汤药费可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