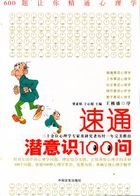菲比是第一次来中国,堂的记忆还停留在他年幼的时候坐着辫子电车去外婆家,所以两个人的行程完全依赖于文鸢。文鸢给他们两一人配备了一个国内的电话号码,想了想又把夜椎的号码也存了进去,万一找不到她,能找到夜椎也好。
菲比的中文要比堂好许多,她看着夜椎的名字说,“这个人是谁,是你的男朋友吗?”
文鸢笑了,“他是我哥哥。”
“可是你们不是一个姓。难道你妈妈姓夜?”
“他是我爸爸收养的孩子。”
菲比与堂同时点了点头,颇有深意的对视了一眼,堂揶揄道,“那我们应该赶快告诉贝利让他过来。”菲比作势打了一下堂,却也跟着笑看着文鸢。
菲比和堂住的酒店在石门一路,文鸢刚下租的房子在常德路,倒也不是很远。堂心血来潮租了一辆自行车,他说可以骑车领略这个城市的风情。可惜他只骑了一次就被马路上来来往往你拥我挤的车潮吓得退避三舍,并且声称永远不会在早晚高峰出门了。
夜椎的效率是高的令人咋舌的。有一天文鸢陪两个老同学玩了半天回到旅店,愕然发现房间已经空了,服务员正在打扫,她上前问她的行李呢,服务员说另一位与她同住房客已经办了退房了,并且留了字条给她。
留言上简单明了的说明了,她的电话关机所以他未通知她就把行李搬去了新租的房子,让她收到留言后电话他并直接回新的住处。
文鸢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不由得摇头叹气,果然是电话没电了。
她到前台借了电话打给他,那端夜椎却闷闷的说一个叫做堂的外国男子打电话给他,并说在吴江路附近迷路了,让他去接。他已经在路上了。听完文鸢扑哧一笑。这个堂,哪里是迷路啊,分明是想见一见夜椎嘛。之前就跟她提了几次了,但她知道夜椎不喜欢应付陌生人所以就躲过去了,不料堂居然来这招,菲比也不拦着他。
文鸢赶到的时候三个人正坐在露天吧台吃烧烤,堂的面前还摊着好几瓶啤酒,笑声爽朗。夜椎好耐心的陪着他俩,脸色却阴晴不定。菲比看到她,很高兴的招了招手。
“吃烧烤啊?你们不是说今天要早点回去休息,累了大半天了嘛。”
堂讪讪的笑了笑,又若无其事拍着夜椎的胳臂道,“这不是逛着逛着迷路了嘛,幸亏有你哥哥在。”一看到堂拍到夜椎的胳臂,文鸢几乎是下意识的冲过去推开了堂的手。三个人都怔了怔,不解的看向她。夜椎的嘴角不经意的扬了扬,想笑不笑的样子,然后朝着文鸢努了努嘴,文鸢一低头,才想起来他伤的是右臂,堂拍的是左臂。
“他前两天打球手受伤,碰不得。”文鸢尴尬的向堂和菲比解释着。
“哦,打球啊。打什么球,以后我们一起啊。”堂兴致勃勃的问道。
“橄榄球。”
“康乐球。”
两人同时说道,说完,四个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我平时喜欢打康乐球,前几天被朋友拖去玩橄榄球充数,结果就受伤了。”夜椎不动声色的圆了回来。
四个人说说笑笑便吃到半夜。先把两位外国友人送回酒店,文鸢才拉着夜椎回新住处。
收拾完房间,文鸢打开电脑,正巧发现菲比也在线,于是便带上耳麦两人聊了起来。
“看得出来你哥哥很保护你的。”菲比正在涂着指甲油,快干风扇呼啦啦的转着。文鸢开了蓝牙,也一边排书一边嗯了声。
“不过他毕竟是你爸爸的养子,而且他给我感觉很阴沉。塔拉,你们家发生的事我很遗憾,但是我希望你能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成为受伤者。”
“谢谢。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夜椎是我的哥哥,不管爸爸在不在,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愿意相信他。”
那头,菲比叹了口气,“既然如此,我要你记住,我永远站在你一边。”文鸢无言的点了点头,哪怕没有声音,她相信语音那端的菲比还是可以领会她的。
夜椎洗完澡出来,坐在狭小的客厅里,嘴里咬着绷带,一只手在包扎。文鸢瞧见了自然而然的从他嘴唇边扯出了绷带,接过了手。“我说你,可不可以稍微依靠我一下,虽然我这个妹妹比较没用,但你也不用每次都把我当成透明的啊。”
夜椎若有似无的点了点头,默然不语。文鸢叹了口气,坏心的手上一用力,夜椎却只嘶了一声,既没有抬眼瞧她,也没有埋怨半句。
“表叔到底为什么打你?”文鸢心里头还在纠结着这件事情,表叔一个中年残疾坐在轮椅上的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把夜椎伤成这样吧,除非夜椎傻傻站在那里任由他劈任由他砍,可是夜椎怎么看也不像如此迂腐之人。
夜椎还是不说话。文鸢有点恼了,用剪刀把剩余的绷带咔嚓剪断,暗较着劲乒乒乓乓的收拾着东西。夜椎默然无语的站起身往自己的房间走去。然而,背后的低气压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转过身,就看见文鸢一动不动的坐在卡其布的沙发上,手里还拿着那把剪刀,她的眼眸睁的大大的,空空然的目视着前方,她的身体下意识的蜷缩着,眼眶含着一层雾气,始终却不曾落下一滴泪来。
夜椎的左手无名指颤了颤,几秒钟,他的眼睛像猫一样凝聚成一条线,许然,他暗暗做了几次深呼吸,手指握成了拳。再慢慢松开的时候,他的眼眸恢复了一贯的清冷和沉寂。
“有些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但是我也不想骗你。是你说过,你应该担负起责任的,现在你最大的责任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不要把自己卷入莫名其妙的灾难中。”说完,他转身进屋,躺在了床上。
文鸢重重吸了一口气,视线滑过夜椎的房间。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从来都不知道,从小到大他就一直那么安静如影随形的跟随在她身边,用他自己的方式陪伴她并保护她,可是,可是他却从来也不了解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渴望的是一个同伴,一个可以彻夜聊天,一个可以打开心门,一个可以互相谩骂甚至殴打的亲人,而不是像那样,永远仿佛自上而下的由远及近的带着疏离与冷漠的仅仅给予外在的保护。
夜椎,他更像一个管家,一个保护人,一个忠于职守的卫士,而不像一个活生生的哥哥。
夜椎躺在床上,慢慢的闭上了眼睛,他是在休息也是在睡眠,他的睡眠很浅很短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9岁那年,宋家明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刻历历在目。他永远无法忘记,不仅仅是因为出色的记忆力,而且是因为宋家明的那个诺言,惊沉必须去医院接受治疗否则他也许活不过几天,他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所有的希望都落在夜椎一个人身上,因为他是最有可能被收养的孩童。
那一年,他大约9岁。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年纪,不知道自己出生的日期,他是一个一出生就被遗弃的孤儿。惊沉13岁,卡夫卡8岁。他们生活在菲律宾的一家幼儿养殖场,没错,是养殖场并不是孤儿院。因为生活在里面的孩童都不受政府的保护,不为人所知,来历不明,他们从记事起就接受惨无人道的训练,像角斗士一样,亦或者更像是刺客。7岁以后他们就可以入场进行公开角斗,并表演给带着面具的观众看,加在他们身上的赌注往往一注天价。
养殖场的孩童没有一个超过14岁的,14岁以后的孩子去向不明。他们有时候也被恐怖组织收购作为暗杀者或者牺牲品,多数的孩子都死在了14岁以前。
角斗和对杀表演也分个人场和团体场,而惊沉,卡夫卡,夜椎三人则是团体场的王牌之一,他们三个孩子性格各异也是最早懂得分工合作的,惊沉负责掌控全局,卡夫卡负责突刺和主攻,而夜椎则是暗杀及歼灭。三人合作下来彼此间赢得了尊重和亲密,也一次次的死里逃生。然而在一场强团对决中,惊沉还是受伤了。卡夫卡的主攻陷入了对方的包围,被完全的隔离开来,卡夫卡暴躁的性格注定了他缺少应变和防御的能力,夜椎那个时候已经杀红了眼,团队之间很少有人清楚其实他是左撇子,但是那一次中一大半的人都是被他左手掐断颈动脉的。
惊沉远远的看着,局面已经完全脱离他的掌控,他也来不及提醒夜椎救援卡夫卡了。就在对手已经掐住卡夫卡的脖颈,卡夫卡几乎窒息的时候,惊沉冲了过去,他推开了所有人,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卡夫卡,也许对他来说整个团队不能没有主攻。等到夜椎肃清全场的时候,卡夫卡只是嘴角流出鲜血,但是,惊沉的一条腿却被折成了奇怪的造型,而他的胸口也一片殷红。他的一根肋骨断了,刺进了胸腔。
这场角斗赛可谓空前绝后的精彩,赌注也一再翻倍。角斗结束后,照例,那些带着银灰色面具的观众可以肆意挑选养殖场的孩童,购买或者租用。卡夫卡和夜椎被推到了挑选区,而惊沉则被教官拖进了休息区,没有治疗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卡夫卡咬着牙看着夜椎,他们曾经发过誓,谁也不能被挑走,谁也不能抛弃彼此,但是这一刻,他们心底都清楚,要救惊沉就必须有人被挑选,因为养殖场是不在乎这些孩童死亡的,死了一批还会有新的一批,所以他们不会救治,他们能够指望的只有挑选他们的观众了。
果然,夜椎惊采绝艳的表现已经引起了好几拨观众的青睐。主动权轮转到了夜椎的手中,教官甚至私自加码,眼眸中是毫不掩饰的贪婪。为了增加加注的乐趣,教官尝试着让夜椎自己提出筹码来。
“能够救惊沉的人,就是我的主人。”这是夜椎的原话,也引起了一片哗然。最终,出资将惊沉送进当地一家私人医院的人,就是宋家明。一个会出现在养殖场的观众,夜椎心底早就隐隐的猜测到,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宋家明曾经也亲口对他说过,那个孩子,并不是我的女儿,但是总有一天,她的心脏和眼睛都必须要交给我。夜椎只是漠然的点了点头,对他来说,只要惊沉能够活下来,其他的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哪怕让他亲手杀死那个女孩,他也不会有丝毫的迟疑。
可是,他真的不会有丝毫的迟疑么?这个疑问,在他心里越来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