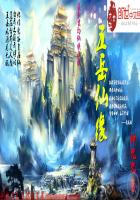那天后来下了很大的雪,明明是艳阳八月天,却偏生变成了天寒地冻。
白若梨在长安谷外满天风雪里跪了一天一夜,大出血又晕了三天,终在黎明前夕拖着孱弱的身体离开。不过,也并不是一无所得,她额上的印记已由淡淡的鹅黄变作明黄,虽不及白丹一的凝实,但到底也修得了金仙之位。二十岁的金仙,实力已在白家几位长老之上,巨大的潜力更是众长老拍马不及的。
这期间,长安谷内所有人都被困在了白丹一布的结界内出不来。就连素来与白若梨走的最近的白若水,也因着这诡异的天气被派去长安谷北面的苦寒之地查明原因去了。
突降大雪,白家众长老一致认为是极北的苦寒之地出现了什么毛病,又因离的最近便派了人过去。
离了长安谷的地界,一路向南,白若梨打算去昌州花家看看。
如今,别说腾云,她连御剑也是不能,只得雇了马车,走走停停,慢慢晃过去。不知有心无心,她的路线避过了兴义。
如是走了半个多月,她的身子也将养的差不多了,金仙自身的修复能力到底不是散仙能比的。
夜晚,白若梨宿在树林里,倚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
因自身恢复,她辞退了车夫,打算自己御风过去。
成为金仙,意味着可以御风而行,她还未试过,正好练习。
万籁俱寂,夜寂静的可怕。
“本君还道白七小姐活的惬意呢!今日怎么这般不济了?你那小情人呢?你那所谓的朋友呢?”宸月的声音出现的突兀,带着慵懒和饶有兴味。
白若梨眼未睁,头未抬,懒懒地道,“我素来知道这世间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却不想魔君这样的身份也干这落井下石的宵小勾当。”明明是懒散的语气,说出的话却刻薄如刀子。
宸月也不恼,只低头笑道,“这热闹本君看着甚好,甚好。”
听了他的话,白若梨却是颇恼怒,倏地睁开了眼睛,抬头怒视他,“原来魔界之主这么清闲吗?”
“那是因为本君圣明,魔界自然是十分的太平。”
“魔君说这样的话不会脸红吗?据我所知,不久前魔界才刚刚发生了大规模叛乱,魔王重玉虽败却带手下逃了。这个节骨眼,不正应是肃清的时候吗?”
“笑话!本君堂堂魔君,会怕区区一个重玉小儿?本君座下十二位魔王,叛出一个重玉,还无需担心。魔界的事交给手下人即可,哪里需要本君担心?”
“事事交由手下处理,宸月你还真是我见过最清闲的魔君!”
“黄口小儿,满嘴胡言!本君成为魔君之时尚未有你,你哪里见过其他魔君?”
“……”白若梨竟是一时无言。
宸月却突然开口,“没人要你,你随本君回魔宫吧。本君封你为后。”
魔君宸月就如鬼君陌离一般,也是没有妻妾子女的孤家寡人。但不同的是,宸月连同谁传绯闻都是不曾传过的,也未曾见他对谁特别对待过。因此,每每有人暗自揣测,宸月其实是不喜欢女子的,甚至连男子也是不喜欢的。
但事实上,魔君他老人家不曾心动过,自然不知道喜欢一个人该是怎样的,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的那份喜欢。饶是对白若梨,他也只是觉得这个人不一样,和这个人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不讨厌。
原是想要将自己的好感表达给白若梨的,但他的话怎么听都像是在施舍一样,偏他自己还不知道。
白若梨自然也感觉出他话中施舍的意味,勃然大怒,“魔君,你这话什么意思?施舍我吗?你以为我会感恩戴德,巴巴地跟你回魔宫?你做梦!收起你虚伪的施舍,我白若梨不需要!”
“不识抬举!”宸月一扫衣袖,转身就走。魔也是有自尊心的,魔君他老人家自尊心更盛,自尊心不允许他多做丝毫解释。
望着他离开的背影,白若梨摸了摸鼻子,有些摸不着头脑地喃喃出声,“莫名其妙。难道说,因为叛乱让向来自诩圣明的魔君大人深受打击,一不小心患上了失心疯了?”
当然,这话她可不敢当着宸月的面说,她害怕宸月一个失手让她连渣都不剩。
前半夜,因着宸月的到来,很是不得安宁,白若梨遂转移阵地,挪到了树冠上接着睡。
后半夜,她刚睡着,树下又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两方皆是凡人,上演的是仇家追杀的戏码。白若梨遂不插手,打定主意,双手报臂站在树尖看热闹。
追杀的是二十几个黑衣蒙面人,被追杀的年轻男人抱着孩子还在拼死相抗。
这画面甚是无聊,白若梨便将目光移向那尚在襁褓的婴儿。
那是个很漂亮的男孩,很有灵气,与她幼时有几分相似。
鬼使神差地开了口,她轻声问道,“树下那人,你这孩子交给我抚养,让我当儿子可好?”
被问到的人傻了,连那些黑衣人也傻了,他们竟然不知道这树上原是有人的,不免都有些愕然。
白若梨从树上施施然落下,来到那男人面前,又道,“我观察了许久,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你若同意把这孩子给我当儿子,我就带他离开,教他法术,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他分毫,你可同意?”
那男人毫不犹豫,便将孩子交给了白若梨。
她轻笑,“你就不怕我是坏人?不怕我让他成魔?”
“我家一百七十三口难逃此劫,我儿若能逃脱,成仙成魔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很识趣,索性我不是魔,不过一介修习之人。”
“仙子既然看上小儿,是小儿之福。还望仙子日后告诫小儿,不要报仇。”
“我的儿子,自然不会为你家报仇!”白若梨这话说的很是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