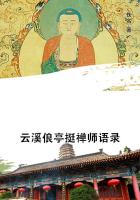如萋进屋换好衣服,黑色铅笔裤搭配白色中长款外衣,收腰且轻盈,突出她高挑的身材,镜中的她脸庞瘦削,她手指轻抚着有些干燥的皮肤,直直盯着镜面的另一个自己,久久,心里冒出个声音,悠远缥缈,如萋,如萋,你已得到他的爱,将过去种种不愉快都忘了吧,释然些,她朝另一个苍白瘦小的自己笑了笑,将头发散落下来,遮住悲伤,遗忘落寞。
正准备出门,恰巧看见了被她遗落在书桌上好几天的手机,打开看,多条短信和来电,有司柔和林浔的,多是夏小风的。
如萋给夏小风回过去,想着她多日没去学校上课,他该担心了。
“喂,如萋吗?”夏小风急切问道。
“嗯,是我”
“你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不来上课?严不严重?啊?你家在哪?我来看你。”夏小风语气透着慌乱和紧张。
“家里有点事,不严重,现在处理好了,明天我就来上学。”如萋既感动又内疚,夏小风的关怀让她倍感温暖,而自己这几日却从没想到突然的消失会让他心急如焚。
“你没事就好,以后有事能先给我说一声吗?我好担心的。”夏小风语气轻松下来。
“恩,不好意思啊。”如萋赔礼道。
“没事,谁让你是我朋友呢。”电话那头的夏小风嘿嘿一笑,笑声纯朗。
“那明天来了,你给我补补课呗。”
“没问题,我这几天笔记做得可好了,就想着你来了给你看。”未见其人,但如萋就能想象到他此刻眉毛必定是一边上挑,嘴角上翘,得意地笑着。
“谢谢啦。我要去吃饭了,明儿再聊。”如萋听见司东敲门的声音,转过头就看见他一身休闲装随意倚在门上,温柔地凝视她,便匆忙结束了通话。
“走吧。”如萋跑着过去牵他的手。
“你刚才和谁讲电话呢?”他可听见她清脆的笑声。
“一个同学。”如萋回答道。
“敷衍我。”某人不满了,阴沉着眉目。
“夏小风,你不是知道吗?除了他谁还给我打电话呢?”如萋明显对他的这个话题有些无奈了,语气有些激动。
“好吧,我问问而已,你干嘛发脾气,这才交往第一天,你就这样,以后可怎么办?”两人边说边往屋外走去。
发脾气?如萋蹙眉。
“不是,我哪有发脾气啊,是你无事生非,好吗?”如萋着急着辩解。
半响,激动道,“交往?我们交往吗?”现在才反应过来。
“你说呢?你都亲我了,难道想让我做地下情人。”电梯内,司东傲娇了。
“谁亲你了?胡说。”如萋说不过他,睁大眼睛瞪着他,明亮亮的眸子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反而他幽深如墨般的黑瞳似磁铁吸引她入醉。
司东轻悠悠地拉近彼此的距离,一手揽过她的腰,“忘记了?那我们重新回顾一下,看看我说错没?”说着,脸就急着上前凑。
“走开啦,流氓。”刚好电梯门开了,如萋推开他疾步往外走。
她娇羞的姿态惹得司东嘴角上扬。
好久,颧骨未上起过了,这样真好。
吃完饭,回了趟司家,司东未将此事告诉旁人,毕竟关乎如萋的清白名誉,他不想如萋遭别人议论和非议,一切如常。
那段沉甸甸的噩梦,埋起来,成了秘密,不被提起,逐渐遗忘,好似从不曾发生过,是自欺欺人还是真成了过眼云烟,无人可知,一切能如愿吗?
如萋用他建筑的天堂来逃离地狱,不知,若天堂不在,人间还有她容身之处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是非之地,她能适应吗?
她和司东,从倾心守护到以情侣姿态相伴,刹那光辉,颠覆命运,她不知,此棋是否正确,顺从心意与命运相搏会不会遭天谴,她的命本如花,只需绽放数日,便足矣,余下的残花落叶,只等它随风飘逝,祭奠她铭心的爱。
所有的不堪和痛苦真的消殆于他清朗笑容下吗?那只会在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时猛然冒出来的噩梦旁人可会察觉吗?如萋能避免吗?纵然白日艳阳高照温风和煦,可依旧抵挡不住黑夜的死寂和寒冷。
那扎根在心里的恐惧不会随着一时的幸福而化作徐徐清流随沟渠流淌出来,怕只会埋藏地更深,有朝一日,在你孤立无援、身心交瘁时,腐蚀消磨着你的心。
如萋在司东的蜜罐里甜甜蜜蜜,她笑得开怀,会捉弄他,和他玩闹。她也会如往常般在学校里认真学习,与夏小风聊天作乐。
可她真的不一样了,不漏痕迹的神色和心慌,无人知晓,她的眼角眉梢在无人时无所防备地露出忧虑惊恐之态,她与熟人如常,但恐惧与陌生人相处,更爱独自一人静静注视着蓝天绿野,鲜少与同学交谈互动,遇见陌生人搭讪会匆匆逃走。
司东学业忙碌,仅有的空闲时间全落在陪伴她,可那从心底里点点滴滴冒出的忧虑他不会懂,毕竟他无法进入她的心。
一夜,暴雨天气,雷鸣闪电,风雨交加,如萋半夜起床去客厅喝水,刚倒好水,一声惊雷带着震耳的轰隆声猛地划破天空,一声接着一声的巨响惊动了大地,明亮的客厅瞬间漆黑一片,闪电间或映照着,像极了噩梦中的小树林,刺眼的光闪着闪着,如萋眼前忽现那人发狂凶残的表情,翠绿树叶忽明忽暗,好似鬼魅,如萋仿佛又坠入了那日的地狱中,喉咙被人掐着,无法呼救,手脚战栗着,不能动弹,泪水积聚在眼里,耳边是那个人的低吼声和侮辱声,他又在撕扯她的衣服,抓破她的肌肤。
如萋头痛欲裂,如千万蚂蚁撕咬着她的神经,痛苦难耐,手中的玻璃杯掉落,杂碎一地的渣滓,脚软蹲下,双手紧紧圈着脚踝,将自己缩紧,缩紧,紧紧靠着墙壁,如溺水之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或喃喃自语,或鬼哭狼嚎,断断续续的呻吟与哭喊。
雷声和玻璃落地声将司东惊醒,见如萋不再床上,急忙去寻找,在明明灭灭的光影里,见如萋满脸泪水地缩在墙角,浑身颤抖低语着,司东瞬时心都裂了。
匆匆上前蹲下将她护在怀中,手轻拍着她的背,“没事,如萋,是我,是司东,我来了。”他忽视心碎的声响,用最温柔细腻的声音安抚着她。
“放开我,放开。”如萋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握着拳头捶打司东的脸,挖着,掐着,一下比一下重,一次比一次狠,歇斯底里……
司东没阻止她的击打,只是用手护着她的身子,避免地上的玻璃渣伤着她。
“你这混蛋,滚开……滚开……”破碎的低吼,如萋的双眼失去焦距,空洞木然。
“别怕,我是司东。如萋,我是司东啊。”他的嘴边已有鲜血溢出,唇齿如鬼魅般艳红。
“滚……滚。”她怒吼着,夹杂着愤恨与惧怕,她被心魔困住,无法挣脱出来。
她红红的眸子刺得司东不敢直视她,明明那么可爱纯洁的一个人,为何会变成这样。
司东轻搂着她,温和地疏解她的防线,“没事了,没事了,我在这呢,司东在这呢。”一句一句,不厌其烦,他的柔情蜜意渐渐让如萋消停下来,她没在攻打他,可泪水不止,悲痛绝望,最后哭晕在司东怀里。
雷声已停,悲戚不减。
司东抱着如萋回房休息。
暗色的窗边,伴着大雨瓢泼的冲刷声,烟味被清风一吹就散,烟头的点点亮点,映出司东紧蹙的眉头,明明汹涌流淌过的爱,怎会有躲不开的伤害。
第二天,一宿夜雨迎来初晴,清冽的空气里夹杂青草芬芳味,流淌淡淡的甜,清晨的缕缕薄如蝉翼的光线中,司东静靠在床头,眸子深邃,如萋安稳地睡在他的怀里,不过一夜,他的胡渣就生长得密密麻麻,脸上嘴角还留着淤青,尽管已处理过,浅浅伤痕依旧无法完全磨灭。
此时熟睡中的如萋卸下了所有防备,像个小猫似的依偎着他,头动了动,睫毛颤了颤,睁开眼,迷离又迷糊,盯着司东瞧了半天。
记忆未回笼,佯装镇定。
“醒了?”一如既往的宠爱,噙着笑,好似一切如常。
“呀!你脸怎么了?”如萋注意到他脸颊上的伤口,张大眼睛,强撑着身子起来,手想触摸他的脸,却又怕弄疼他。
“没事,不小心磕破了。”司东抓着她的手,放在嘴边亲吻,意在转移她的注意力。
“胡说,磕也不能磕成这样,你的伤口明显是被掐的,或挖的。”如萋抽出手,回想昨晚。
“我脑袋现在有点混乱,我好好想想。”
“别想了,头会疼的。”司东心疼她。
“是不是我打的,我做噩梦了。”如萋过滤了下昨夜的记忆,她记得她在喊,在叫,撕心裂肺的那种绝望地痛哭。
回忆太恐怖,她潜意识想遗忘。
“你别骗我了,是不是我打的?”,虽是疑问,但已有半分确定,她此刻的心似被悬在两座高峰间的铁链上,一不小心,粉身碎骨。
“嗯,昨晚打雷,你受惊了。”司东侧着身子,将她圈在怀里。
“别担心,不疼,不信你打打看。”说着,还拿她的手拍着他的脸。
“不要。”如萋忙着将手从他手里缩回。
“你干什么?不疼吗?”如萋眼里已有泪光了,他俊朗的面容上有着紫红的印子,格外触目,每一处,都割着她的心。
“对不起,我太坏了,对你都那么心狠。”如萋呜咽着。
“别哭,行吗?我想看着你好好的。”司东刚擦干她的泪滴,又有泪液溢出。
“我们不要因为这点事伤心,好不好?”他温柔地注视她,大拇指摩挲她的脸颊。
如萋抬眸瞧见他清明的眸子,他话语温和,可眉头轻蹙,知道他心里有事,可正掩藏着。
“好,不过以后你不准再这样让我随便打了,我的力量肯定不及你大。”如萋尽力憋住自己的泪水,不让它开启泪流成河的阀门。
“嗯,我答应你。”司东应着。
他凝视她的双眼,“告诉我,经常做噩梦吗?”
如萋哑言,转过视线,躲避他的追问。
他捏住她的下颌,迫使她与他对视,“不许沉默,不许说谎,不要让我担心。”
如萋沉思片刻,斟酌语句,“有时候会,醒来只有模糊印象,没大碍。”
“我知道了。”司东沉声道。
“真的没事,你不要担心。”
司东拥紧她,似嵌入骨血里,“嗯。”
如萋不再说话,默然相拥,冰凉的泪从心上滑落。
无力感从两人心底悄然肆无忌惮滋生,顿感失望,却又无可奈何,努力着想让对方幸福,却又只会增添伤心事。
浅浅伤痕划在皮肤上,印在心间,淡淡的疼痛让快乐也不那么尽兴。
相拥着寂寞,可是此般无法言说的滋味,为爱人憔悴伤悲,可只能徒增伤悲。
一切只能说太爱了吧!
这天,学校大扫除,早早放学了。如萋想去学校找司东,打电话,不通,便发了条短信,
步入这所历史悠久的高校,如萋不陌生,却惶恐。
她好像和这里格格不入,身旁的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走路也带着一阵风,意气风发,而她的心太小,连自己都装不下,何况梦想呢?
梦想于她而言太遥远,连小孩子都整日将梦想挂在嘴边,可她却从未想过,她的生命从遇见司东开始……
她行走在热闹的人群中,却倍感孤独。她明明打扮靓丽美丽夺目,却感觉众人的注视仿佛看破了她的自卑和胆怯。
她眼睛低垂着,双手紧抓着书包带,想将自己缩小再缩小,最好没人能看见她。
“你在干什么?”低沉的声音从头顶响起。
抬头,没有惊讶与愤怒,低首。
想擦身而过。
“对不起。”他拉住她的手,阻止她再一次离他而去。
“那天我不应该不送你回去。”一向高傲、目中无人的他竟会道歉。
黑瞳里流动着伤悲。
“不要说了。”如萋转头盯着他,眼神漠然,话语激动。
“这件事我不怪任何人,那是我的命,我认,可我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纠缠,你不能逼我。”她隐忍着怒气,尽量心平气和地一字一字吐出,着重强调了‘命’与‘纠缠’。
她不怪罪于他,并不代表她会接受他,那不是一笑置之的往事,她忘却不了,也释然不了。
“为什么?我难道就那么差,连一眼你也不肯给我。”他从未如此消沉和无奈过,眼里闪过一丝受伤的痕迹。
“不,是我的问题。”那一晚,她明知晚回有危险,可想着每日他都会送她归家,她心存侥幸地自私地贪心地想把那道题做完才走,可悲剧发生了,无可挽回,她回想,他有何义务和责任需陪送自己呢?
“我有司东一人已足够,你不必抱着弥补的心态对我好,你没错,错在我。”不应对他人奢求过多,如萋想,把所有的纠葛是非都划在一个小圆内,里面只有她和司东,所有的事情都由他(她)们俩来承担。
“你和他在一起,对吗?”林浔问道,声音有一丝喑哑。
如萋转过身,没有回应。
可也没有否认。
两人停驻在十字交叉口,一侧是茂密的树林,一侧是宽阔的运动场,阳光洒下,清风徐来,各自坚持着。
一人执迷不休,一人执迷不悔。
“我不会退缩的。”他已经没办法了,他无法强迫她,不能伤害她,只能用一颗真挚的心打动她。
那夜的宿醉忘不了她,用责任友谊捆绑自己无济于事,她的面容,含着泪,时时浮现在自己眼前。
以前他可以把她视为一个猎物,用尽手段去捕获。可现在,他想换回她的喜乐,做她的骑士。
“呵……没有用的,你太低估我对司东的感情了。”如萋自嘲一笑,目不斜视地走了。
这一次,她抬起头,留给他一个自信独立的背影,她不想他怜悯她。
风和日丽,岁月静好,可为何总有吹不散的悲伤笼罩着她(他)们。
强求就会有牺牲,林浔,你若早觉悟,便不会有惨剧发生了。
我当初若狠一些……为何总有吹不散的风萦绕在我们的身边,太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