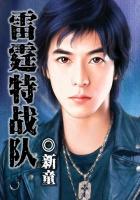“你确定是这个?”荣梓义看着手里红色的硬木印章问梓孝。
这个印章几乎是全新的,但却很容易看得出,与父亲常用的那个硬木印章是同一个师傅雕刻制作的。父亲的印章由于用得年头久了,表面被摩挲得光润温和,甚至已经有了几道浅浅的裂痕。而眼前这个,应该是很少使用,一直存放得极好,凑到鼻端,甚至还能闻到檀木淡淡的清香。印章上雕刻着的“吴玉珍印”四个字是楷体,底下还有难以模仿的花押图案。
“我并不能确定,只是认为有这个可能性。”荣梓孝道:“据母亲回忆,这个印章是父亲请人做了以后送给她的。但父亲一向叮嘱她要好好保管,似乎看得比她常用的那个玉石的还要珍贵。虽然是檀木,但毕竟不值什么,母亲以为是因为请了大师做的,求之不易,所以父亲要求珍藏,她便真的很少拿出来使用。但父亲近几年倒是借用过几次。便只这点,我就觉得奇怪。”
荣梓义点头:“你说得没错。只这一个原因,便值得去试一试。这样,我这边还有件事没有处理,我给银行的方经理打个电话,你先去。有什么结果再通知我。如果电话里不方便,你可以在愚园路找到我。”
荣梓孝微微讶异,什么事会比追查父亲的保险箱更加重要?但他不好多问,见荣梓义有意结束谈话,只好告辞离去。
荣梓义站在路边看着弟弟驾驶着汽车渐渐远去,心中也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心情雀跃。荣梓孝分析得没错,吴玉珍的这枚印章能够开启保险箱的可能性极大。他也想亲眼看看保险箱里究竟有什么东西,是否能够指引出找到杀害父亲的凶手,是否能够找到那批货。
荣梓义对那批货的存在深信不疑。因为他所掌握的情况
比已经告诉梓孝的要多。他手里握着父亲的一封亲笔信,详细交待了他准备这批货的用意。只是,现在还不是告诉弟弟的恰当时机。
最为重要的是,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上海有这批货,而自己身后的尾巴,随时随地将会造成威胁。尤其难为的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现在还不是除去他们的时候。
荣梓义为自己的行动受限颇为苦恼,没想到深田凉子倒是决断很快,一旦产生猜忌便立即采取行动。看来自己有必要亲自去走上一遭,试探一下她的态度,对自己的怀疑到底到了哪种程度。
想到这里,荣梓义不再犹豫。他一个转身,向来路走去。原本离他有一定距离,缓缓跟在他身后的两个戴着礼帽的男人猝不及防,均是一愣。荣梓义走到他们身旁时,他们才从兜里掏出烟来,想做出在路边吸烟的悠闲模样,只是神情未免有些慌张。
荣梓义却停下了脚步,注视着这两个人。这两人在他审视的目光下开始躲闪。其中一人正拿着火柴打火,却怎么也划不着火。
荣梓义从他手里接过火柴,轻轻的一划,那火苗就燃烧起来。他将火柴举在那人面前,向他示意。他人足足呆了两秒钟,才将嘴上的香烟凑到火苗上。
荣梓义微微一笑,将火柴晃灭,用日语客气的道:“两位辛苦。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二位可否见告?”
那人又是一愣,对着荣梓义鞠了一躬,也用日语答道:“荣先生请讲。”
“不知道深田课长今天午后会在哪里,我正好有事情要找她。”
那人苦笑一下,恭敬的答道:“深田课长交待我们两个人的任务只是保护荣先生。至于其它的,我们并不知情。”
“原来是这样。”荣梓义似乎认可了这种回答:“还有件事想麻烦你们。你们应该是开着车的,能否请你们将我送到梅机关去,我想在那里应该可以找到我想要找的人。”
深田凉子一身军装从梅机关走出来,忙碌了一天,可仍然精神抖擞,衣服笔挺。她经常会加班,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
对荣梓义的调查工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她目前可以掌握的,也不过是他在法国的时候曾经参与过左翼社会党人的民主运动,对工人党和共产党一向抱以同情态度。
可是他到香港大学教书以后,就很难查到其与社会党派接触的信息。这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对政治丧失了兴趣,一心只做经济。而另一种可能,则是让深田凉子不放心的,是他已经加入了某个党派,并开始为其秘密服务。
这期间,荣梓义唯一可疑的,便是他的四处旅行。可以解释为一个喜欢多见世面的人开阔眼界的方法,但难道不能说成他在为其组织四处活动吗?
深田凉子发现,只要换一个角度,荣梓义的所有行为便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一个可怕的、让她难以接受的解释。
正是李士群提醒了她有这种可能性。
尽管深田凉子认为,因为自己的职业敏感,一向小心谨慎的她并未泄露过帝国军队的任何消息给荣梓义,但她也还是不由自主的想到,有几次,自己仿佛是按着荣梓义给他安排的路在走。他在某种程度上操纵了她,利用了她,包括这次李士群的死。虽然李士群也的确该死!
荣梓义与她的接触,到底是因为她个人以及他与她的感情,还是为帝国的事业埋了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呢?
深田凉子深恨自己,她甚至都不敢跑去直接去问他,只能偷偷的调查他。而自从调查开始,她便有些不敢见他。
调查并没有得出可以证明荣梓义有罪的结果,包括跟踪他的人回馈的信息,也是他每日行动正常,并无异样。面对这样的结论,深田凉子不知是喜是忧。
荣梓义没事,当然最好;可万一是没有调查出来呢?
正如荣梓忠所言: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了,便有可能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而她的工作,更不允许将自己置身于险境。万一是荣梓义隐藏得极好极深呢?自己是否还能放心与他交往?可是如果是猜测错了呢?只有她自己知道,损失的是什么,她真的舍得离开他从此不再见他吗?
深田凉子眼前似乎又浮现出荣梓义微笑的脸。他经常会扶一扶金丝边眼镜,习惯性的向自己轻轻的点一点头,唇角上扬起一个好看的弧度。他的声音低沉柔和,讲任何事情从来不紧不慢,缓缓道来,娓娓动听。他的学识、他的风度,他的一切一切,从少年时期就是自己的梦,难道她要就此放弃吗?
不。深田凉子在心中对自己摇头,如果让她放弃,那么,她宁愿毁了他,或者是毁了自己!
深田凉子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梅机关的大门口。
门口停着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深色的车窗上挂着窗帘,从外面看不到车里面的状况。这正是隶属于特高课的汽车,被深田凉子派去监视荣梓义的那一组人的专车。
它怎么会停在这里?深田凉子皱了皱眉,向汽车走去。
车上下来的,正是那两个特高课的特务。他们向深田凉子深深的一鞠躬,其中一人凑到她耳边低声解释了几句。
深田凉子不由得变了脸色。她狠狠瞪了那两个特务一眼,挥了挥手。那两人便如遭大赦一般,急忙撤走了。
透过敞开的汽车后门,深田凉子看到荣梓义正好整以暇的坐在汽车后座上。神态从容平静,似乎与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深田凉子仍能感受到安宁背后透出来的阵阵寒意。
深田凉子只好先发制人:“荣桑几时来的?为什么不进去,而在这里等候?”
荣梓义这才起身下车,他看了看深田凉子,并没有回答,而是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示意深田凉子上车。
深田凉子不知道他要怎样,想来左不过是因为知道了自己派人跟踪他的事实而对自己不满,要发作自己而已。但事已至此,也别无他法,她反而不再纠结,痛快的上了车。
荣梓义将车门关上,从另一侧上了车。他把手放在方向盘上,手指轻轻敲击着,似乎在盘算什么。
深田凉子打定主意,他不说话,那么她也绝不先行表态。一切看他的态度来。于是,她便目不斜视的看着前方,默不作声。只是她崩直的身体,表明了她的确也是有些紧张不安。
荣梓义突然凑近了她。他的头离她只有几寸远,近得深田凉子能够听到他轻轻的呼吸声,能闻到他身上一种好似阳光下青草地般的淡淡芬芳。深田凉子的心“怦怦”乱跳起来,她不由自主的将身子往另一边侧了侧,只想离得他远一些。
可是,他的另一边手臂抬了起来,虚虚的环在了深田凉子的脖颈处。她侧过身去,倒象是要倒在他的胳膊上一般。她避无可避。
深田凉子的手心开始冒汗,可此时,荣梓义的另一条胳膊也挨了过来。他离得她那样近,两条手臂几乎便环住了她,整个人包围着他,他的气息就在她的鼻端。她呼吸不稳,头脑里一阵迷糊,身上似乎也要失去力气。
她蓦然恼怒起来!他这是要做什么?他是不是以为可以吃定了她?
深田凉子咬咬牙,坐直身子,伸手去推荣梓义的手腕,可好巧不巧的却碰到了他的手。看起来倒象是自己主动去握他的手一样。
荣梓义看着她,似笑非笑,目光里却似乎含着点惊讶的意味。深田凉子只觉得象是被烫了一般,立刻缩回了手。这时,耳中只听“咔嗒”一声,她座椅上安全带的锁被扣上了。
原来,荣梓义不过是帮她系好安全带而已!
深田凉子的脸“唰”的一下子红了。她再也不是那个穿着制服、冷酷无情的日本特高课课长,而成了一个扭捏女子,十足带着几分害羞的小女儿情态。她嗫嚅着,半天才道:“我自己可以系的。”
荣梓义收回手臂,淡淡一笑。他利落的启动汽车,车子立刻就象是离弦的箭一般,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开了起来。
汽车猛的前冲,因为惯性,深田凉子的身体向后一顿,几乎是撞到了汽车椅背上。深田凉子吃惊的看着荣梓义,只见他变了表情,紧抿着嘴唇,双眼只是看着前方。
她从没见他这样开过车。油门踩到底,汽车行驶得飞快。遇到人多的地方便猛摁喇叭,行人、车辆纷纷避让,留下的是飞扬的尘土和路人的咒骂。
好在汽车行驶的方向是城效,障碍渐渐稀少,但道路也更加坑洼不平起来。深田凉子被颠得几乎要散了架,她现在明白荣梓义给她系上安全带的用意了。
眼看前方道路越来越窄,越来越不平坦,这样行驶起来实在太过危险,路上突发任何状况都有可能要了两个人的性命。深田凉子再也忍耐不住,道:“荣桑,停下!”
荣梓义置若罔闻,丝毫没有减速。
“请你停下!”深田凉子高声叫道,语气严厉,但多少还带着一点请求的意味。
荣梓义瞟了她一眼,终于缓缓松开油门,将车停在路边。
深田凉子抚着胸口:“没想到荣桑也会做这么疯狂的事。”她看向荣梓义,气忿的道:“但是,请荣桑下次再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带上我好吗?”
“怎么?深田课长也会害怕?”荣梓义冷笑,他逼视着深田凉子道:“你怕的是什么?是无法操控我?还是被朋友背叛?”
他见深田凉子愣怔着答不上来,继续道:“车是我开的,你控制不了。生怕一个不巧,也许车轮压上一颗指头大的石子都会让我们车毁人亡。你习惯了开车的司机都听你指挥,通常都是你要他快,他就快,你要他慢,他就慢。”
深田凉子的脸色铁青,荣梓义却仍然咄咄逼人:“深田课长,你就那么想要掌控别人?非要让周围的一切都听从你的指挥?最终,让他们都成为你的操线木偶?其中……也包括我?”
深田凉子深吸一口气,压抑住自己的愤怒:“荣桑,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一向是最为冷静的人,我实在无法理解你今天为什么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
“我疯狂?”荣梓义冷冷的道:“至少我还保有一线理智。我停下了车,不是吗?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有信心,并没有真的想让我们两个就这样死在荒郊野岭。可是凉子,你呢?在这条路上,你管不住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了!”见深田凉子想开口说话,荣梓义及时制止住了她:“你一直派人在跟踪我,我没有说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