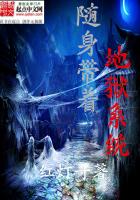我每天的饮食很有规律,除了蹭饭外,一天三顿就是馒头蘸老干妈豆豉。
我对吃的东西没有特别的要求,或者说,因为从小在艰难的环境里长大,我长这么大,除了别人请客,一直都是以粗茶淡饭为主。
凌晨2点,当我陪着姚若琳上完晚班,就一个人来到了那个只能称之为窝的出租屋。
这个房间虽然不大,但是我所需要的必需品一应俱全。
一打开那个有些摇晃的房门,内部的一切尽收眼底,地下有一口电饭锅,那是我在菜市场花了八块钱买的地摊货。
别看它便宜,除了噪音惊天动地意外,效果倒还不错,至少每顿饭都能煮熟,虽然煮出来的味道差强人意,但是填饱肚皮倒是没问题,吃饱不想家嘛,所以这个电饭煲平时还是帮了我的大忙,至少没有饿着肚子入眠。
有些时候,我收到了新闻发布会的红包,给报社上交一半,等完成了稿件以后,也会拿出来一点犒劳一下自己,在外面狠狠地吃上一顿。
那个便宜的电锅在深夜里的噪音明显比平时大很多,每当我煮饭的时候,总会感觉似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一样。
有些时候,我做饭的时候突然碰到了一下锅,隔壁房间还会突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唏嘘声,灯突然会亮一下,不久又关上了。
我的房间长3米宽2米,三面墙是石棉瓦,一面墙是原有的房间外墙,墙上有一个长宽约2米的大窗户,按照我的判断,隔壁那个房间应该是用客厅改造的了。
同租的邻居用一个破床单把窗户遮的严严实实,尤其是灯亮以后,那个影影绰绰的帘幕总能带给我无限遐想。
因为窗帘位于隔壁房间,我这边则空空如也,换句话说,隔壁的人若果想偷窥我,只需要轻轻拉开点床单一角,就能通过玻璃把我的房间观察的一览无余,而我却一点也看不到对方。
我想,管他呢,反正隔壁住的是女人,总不可能偷窥的一个大老爷们吧,即使偷窥,只要不在老子打手虫的时候欣赏就好。
这世道真是说不得,说来也怪,这年头有时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
一天夜里,我加完班回到这里,瞬间感觉饥肠辘辘起来,看来不加餐是不行了。
在房间里,我打开电饭煲正在兴致勃勃地煮面吃,把床头那个破收音机调试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没有杂音的节目,是午夜的悄悄话,为了不影响隔壁睡觉,就把声音压到了蚊子一样低。
坐在床头上,我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一个人正吃到兴头上,隔壁房间突然传出来咯咯的笑声,那声音在深夜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脆唯美。
我愣了一下,情不自禁滴扭头一看,窗帘忽然动了一下,很显然是被人刚刚放下来的,而对面没开灯,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意思?难道对面的美女大晚上的会偷窥我这个大老爷们?她也太重口味了吧。
或者是因为我的响动,惊醒了这个熟睡中的美女?可是她为何没有生气,反而格格地笑了起来,难道是在取笑我么?
管她呢?我尽管吃饱喝足就行了。
其实对我来说,有个睡觉的窝就可以了,其他都不需要,反正现在不找对象,最多泡泡妞而已,谁愿意嘲笑就嘲笑把。
但是有一天晚上回来,我哭了。为我的命运,也为老天对我这个乡下来的穷小子的不公而叹息。
那天晚上,蜀城狂风暴雨,马路上的积水已经没过脚踝,当我蹚水回到这个破破烂烂的出租屋,开门进来一看,床上全是水,我的房顶那层薄薄的亮瓦出了问题。
此前,屋顶已经出现了裂纹,几只猫经常跑上去打架嬉戏,肯定白天它们在上面把亮瓦踩烂了,加上这场狂风暴雨的糟蹋,很快就被掀开了。
透过远处微弱的灯光,我看到那些雨水,刀子般的砸在我的被子上,也割到了我的心里,此刻,这样的房子还是人居住的么?我感觉似乎连郊区的牲口房都不如。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悲哀,千里迢迢来到这样一个大都市,却住着一个连牲口都不如的地方,吃着比农村还差的饭菜,过着一副吊儿郎当、穷困潦倒的生活,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工作?泡妞?还是找罪受?
身上又冷又饿,好在灯还有电,只是这种狼狈的场面希望隔壁的不要看到就好,我开始收拾那些被雨浇灌了的用品,就在房间里那盏破旧的灯泡突然被水浇灭的前一秒,我看到玻璃窗上的窗帘又一次动了一下。
又是偷窥,这下可把我的凄惨看清楚了。
我心里很窝火,这个偷窥隐私的人竟然连人落魄窘样都喜欢看是不是心里有什么问题,没灯了,看你还怎么偷窥。
雨还在啪啪滴着,被子已经像水洗的一样,根本没法坐在上面,只有角落半块残留的石棉瓦可以勉强避雨。
随着黑夜的慢慢深沉,看着这个一片汪洋的家,我陷入到无可奈何之中。
实在太累了,我就撑起一把雨伞,一个人蜷缩在靠屋檐的那个角落,穿着半湿的衣服听着雨声发呆,为了尽快把这个恼人的时间打发过去,我就听起新闻不是来,听着听着我哭了,而且哭的一塌糊涂。
不知道哭了多久,倚在墙角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躺在一间暖暖的别墅里,那里有空调、有灯光、有崭新的棉被,我自由地坐在书房里看书,在客厅看电视,在卧室里盖着暖暖的被子睡觉……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