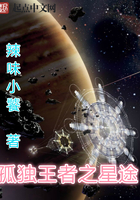四十一
许承宗轻轻笑了笑,目光转到车外,看着这花溪镇的街道和人群,叹道:“过几天就要走了,以后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到这里。”
“这种小地方,人人都急着向外跑,谁会想着回来呢?”望舒轻声答。
“你说的也是。”他语气复杂地轻轻接道,自己默默了一会儿,对前面一直等着的崔三叔道:“开车吧。”
回程的路上他没有再盯着路两旁的景色看,而是默默地盯着天空,乡村上空未受污染的一片湛蓝映在他乌黑的眼睛里,闪动的一点微光,很亮。
到了家门口,望舒和许承宗下了车,许承宗付了车钱,四个人正打算向家里走,开车的崔三叔对望舒道:“望舒,你等会儿,我有句话跟你说说。”
望舒怔了一下,停住脚。崔三叔一直等到许承宗跟两个孩子走进大门,才看着望舒,把望舒看得心里毛毛的,才听见他道:“那人是你家养伤的那个?”
“嗯。”
“他怎么那么跟你说话?”崔三叔语气里都是不满。
“哦?他没说什么啊?”望舒心里有点着急,难道许承宗当着崔三叔面说了什么?自己怎么没有感觉到?
“反正我听着不是那么回事——望舒,你可得小心些,自己一个人在家,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到山下喊人,听见了么?”崔三叔叮嘱她。
望舒脸上有些发烧,即使知道崔三叔话外有音,她也不敢细问,也不好较真,含糊地点点头,一直看着崔三叔把车开走了,她才满腹心事地转身慢慢向屋子里走去。
进了屋子,里外竟然都静悄悄的,两个孩子似乎在楼上看电视,站在走廊,隔着珠串门帘,见许承宗在脱衣服。他光着上身,线条流畅的身材像只猎豹一样,充满了男性的力量之美,她喉咙微微发紧,脸有些发热,目光一时移不开,竟看得呆了。
夏日傍晚的风,暖熏熏地带着一点醉人的气息,吹得她好像在梦里,作着不愿醒来的梦。
肩胛骨处那道触目惊心的疤痕,蓦地出现在她眼前,不自主地就是一惊——他初来的时候,她曾经看见过这条伤疤,又深又长,当年伤得极重么?流了很多血,才能落下那么丑陋的痕迹吧?
“你后背上的那条疤是什么时候落下的?”终于忍不住,问他。
正在换衣服的许承宗愣住,他似乎怔了怔,后来回过身来面对她,那条伤疤她看不见了,他微微犹豫,才答道:“十年前。”
“怎么伤的?”
十年前,他还是个小孩子吧?莫非好勇斗狠,跟人打斗落下的?
“被人划了一刀。”他目光中闪过一抹极细微极复杂的情绪,随即恢复如常,若非望舒细心,几乎不易察觉。
她心中的疑问加深:“谁划了你一刀?”
许承宗盯着她的眼睛,脸上肌肉微僵,一言不发,转过头迅速套上汗衫,随口道:“忘了。”
她本性不是多事的人,但见他举止迥异,平素随心所欲的人此刻竟然有所顾忌,心里不自禁地替他难过——他的往事里,竟然有这么多难以言说的痛苦与秘密么?
“忘了?”
“嗯。”他很肯定地答了一声,翻身躺在竹席上,对她道:“你去做饭吧,我饿了。”说完,把眼睛闭上,浑身上下的姿势摆明了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望舒心中的疑问更加放大,但是他既然不肯泄露,自己也不好一直追问,转身向外走,刚迈出一步,听见身后许承宗的声音突然道:“望舒,等等——被你一打岔,我差点忘了,我有东西给你。”
望舒停住脚,回头见许承宗欠身从自己脱下的裤子口袋里摸出一个崭新的手机,递给她道:“送给你的。”
她有些措手不及,迷惑道:“什么?”
“送给你,拿着吧。”他似乎想下地来递给她,伤腿上上下下地毕竟不方便。望舒看他费力地想起身,忙走过去,接过来,却放在旁边的炕上道:“我不能收你的东西,再说我也用不着。”
他躺着,先是没有接话,后来转过脸来,看着她,说话时,口气十分诚恳:“望舒,我就要走了,以后你嫁了人,可能用到我的地方不多。不过要是你有什么为难的事,钱不够了,生活太累了,甚至晚上又做噩梦了,就用这个手机给我打电话——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都输进去了,你只要按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了。”说到这里,他刚毅英气的脸露出一抹近似自嘲的笑容,“其实我也有私心,有时候我太寂寞了,或许会想听听你的声音。你拿着这个手机,不管到了哪儿,我们还算有机会联系上——这世界这么大,我这一走,一想到你就这么淹没在人海里,心里有些难受。有了手机,总算有一点不同吧。”
她看着他,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听见他说着这样感伤离别的话,自己静立着,心中也有些感伤,伸出手,把那只手机握在手里,转身匆匆出去了。
她把手机放在柜子里,精致得微微发亮的机壳,在阴暗的角落里闪着光——就放在这里吧,她就要嫁人了,他走了之后,再也不会跟他联系,这部手机,就当是这一次遭遇的一个纪念吧。
她走出房去,提水洗米,准备晚饭。盆里的水由清澈变为乳白,一点点地澄出去,眼睛看着水,心思重重中,脑子里猛地划过一个念头——刘果志要来了,而我心里竟然一点都不欢喜。
不光是对即将到来的生活不感到欢喜,对未来,甚至对活着,都感到一丝乏意——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连坚强的理由都没有了,因为她好像不在乎了!
人吃了,猪吃了,鸡鸭鹅吃了,地扫了,拖了,菜地浇了水了,衣服洗了,两个孩子收拾妥了,灯熄了——她躺在炕上,睁着眼睛,胸口似乎有一股不知名的火焰般,烧得她翻来覆去,浑身犹如火炭,呼吸也比平时烫,怎么也睡不着。
她硬撑着,不管如何难受,也不起来,每次听见许承宗屋子里的凉席响声,她滚烫的呼吸都要一窒,后来索性用手捂住耳朵,听着自己怦怦的心跳,紧紧闭上眼睛。
好高的一座阴森的山,她站在山下,努力向山上爬;马,她骑上马,总算爬到半山了,可马突然倒了,马腹里滚出恶心的内脏、血水,排山倒海一样的恶秽向山下淌去,她绝望地意识到自己就要被这些脏东西淹没,想要大声喊,可是没有用,她喊不出来;她被淹没了,窒息的感觉让她想死……
“望舒——,望舒——,醒醒,你做恶梦了!”
她睁开眼睛,茫然的一刹那,心中先闪过一个念头——幸好这是个梦!
定神之后,看清坐在自己旁边的许承宗,窗外的星月光很亮,墙上的指针指向**了,她揉着头,有些抱歉地道:“我吵醒你了?”
他没有回答,只问:“你吓坏了?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她伸手在脸上一抹,惊讶地看着自己满手的泪水,无语良久,双手交握,头慢慢低下,轻轻咬着指关节,咬得手指微痛,半晌哑声道:“做——做了一个噩梦,没什么。”
旁边的他没有回答,他坐得这样近,近得她似乎能感到他身上发出的热力——咬着指关节的牙齿不自觉地用力,星月的光辉似乎只笼罩着自己和他两个人,这周遭是这样的静,透过窗帘的光朦胧出一个梦幻般的假想世界,这个世界里,自己的心又是紧张,又是欢喜……
身子蓦地一紧,随之向后被推到,她出其不意,吓了一跳,惊恐的眼睛前是许承宗专注的脸,和一双亮极了的眼睛。来不及让她思考,他的嘴已经急迫地落在她的唇上,滚烫而热烈,似乎要把她吞下去一般,带着压抑的需求几近蹂躏般地吻着她,她感到自己的呼吸急促,心里想到的竟然只是,他又来亲我了么?
我心里真是欢喜呀!
“望舒——,望舒——”
模糊的她的名字,从两个人的呼吸里溢出来,带着饱蘸**的颤抖,刹那间令她的身体变得无比敏感,感到他的下身顶着自己的小腹,被压抑的禁忌般的渴望如决堤的洪水一般,让她回吻着他。这样排山倒海般的欲望,让人有些害怕,可隐隐地又有些豁出去的快活。
这样被他抱着,仿佛她是无边海上的一块救生的浮木一般,抱得她也伸出手去,回抱着他,跟他紧紧拥在一起,心里嘴边都是满足的叹息,那谜一般的男女**世界,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