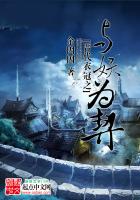张仪家本在魏国旧都安邑,原也是出身贵族。魏国迁都大梁后,张家也举家迁往大梁。但在张仪未满五岁时,父亲便染病亡故,张家因此家道中落。于是张仪之母变卖城中家产,搬到城西十里外孝贤村居住。待到把张仪含辛茹苦带大,张仪便出外游学,家中只剩老母一人苦苦支撑。张仪自楚归家,母亲十分高兴,虽说张仪没有出人头地,但是母子能够团聚,也是喜不胜收。
此日天气晴朗,阳光和煦。
陈离一路打听,终于在未时到达张家。只见院子颇大,但多少显得有些破败,一颗大槐树光秃秃的树枝伸出墙外,似与破败的庭院同病相怜。陈离见大门并未关闭,便自行走进去。只见院中一少女正摇着辘轳自井中打水,偶然瞥见有人走入院中,忙抬头一看,不禁当场怔住,升到一半的木桶又噗通一声掉落井中:这不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男人么?呆了半晌,小唯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冲上去便紧紧抱住陈离放声大哭。陈离见到小唯,也是颇为激动,眼泪也不禁在眼眶中打转,但还是强忍着没掉下来:“傻丫头,哭什么,我来了不是该高兴才对么?”
张仪听到院中声响,便出来观看。只见来人竟是陈离,亦大喜过望,忙跑过来道:“贤弟,你让愚兄等得好苦呀。”
陈离见张仪来到,忙与小唯分开,上前一拜道:“张兄,小弟有礼了!”
兄弟二人双手紧握,不胜欢喜。
张仪先帮陈离把马车赶到院中,搬下行李,然后一同道后堂拜见母亲。
张仪母亲五旬上下,见陈离仪表堂堂,彬彬有礼,也十分喜欢。
张仪着小唯带陈离先休息片刻,言道陈离来到,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便自己一个人出门到外面购置酒食去了。
小唯把陈离带到早已收拾好的房间,见他风尘仆仆,道:“我这就去给我的爷烧些热水,先伺候陈爷沐浴更衣,我的爷先喝完茶解解渴,休息片刻。”
陈离道:“我一路上虽风餐露宿,倒也不觉乏累,不如我同你一同去烧水吧,也好说说话。”
见陈离坚持,小唯也不推辞,便到厨房去生火。陈离则去井边打了几桶水,提到房中,然后陪着小唯。
火光升起,把小唯的脸映得通红。陈离看得有些心醉,不禁上前亲了一下。
小唯的脸更红了,羞得说不出话。
陈离道:“现在就你我二人,不必害羞嘛。这几日过得怎么样?”
小唯道:“小唯过得很好,只是时时刻刻为我的爷担心。张大哥家本来清苦,不过有爷的资助,现在也吃穿不愁。”
陈离道:“是我不好,累得你为我担惊受怕。不过现在好了,我不是完完整整地来了么?”
小唯道:“幸好我的爷来得还算早,小唯这几日可愁呢!”
陈离道:“愁?愁从何来?”
小唯道:“老夫人见张大哥只带我回来,不见带着妻儿,又见我手脚勤快,就要张大哥纳我为妾呢!”
陈离听罢哈哈大笑:“老夫人好眼力呀,哈哈。”
小唯噘嘴道:“爷还笑得出!小唯心里只有我的爷,怎会给旁人做妾?就算张大哥也不行。”
陈离收住笑声,道:“你的心意我自然明白,我也舍不得你呀!但是日后若张兄飞黄腾达,你可不要后悔呀!”
小唯道:“小唯自然不会恍惚,这辈子跟定了我的爷。对了,爷的事情办得如何?韩小姐怎么没和陈爷一起?”
这句话,又触到陈离的伤心之处,使他一阵沉默。
小唯见此,便慌道:“小唯惹陈爷生气了么?”
陈离一声长叹道:“不是。只不过,哎,怎么说呢?事情办砸了,也不是,只是没办成而已,不过好在所有人都安好。至于韩小姐,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小唯见陈离若有所思,便不再追问。待水烧热,陈离帮她提到房中,倒入大木桶里。
一切准备就绪,小唯擦着湿漉漉的刘海道:“我的爷来吧,小唯伺候您沐浴更衣。”
陈离笑道:“你我二人一起沐浴如何?”
小唯羞道:“大白天的,成何体统?张大哥一会就回来啦!”
张仪回到家,置办了一大席酒肉,一家人欢乐的用了午餐。
饭后,小唯陪张母去后堂休息,陈离与张仪二人饮茶闲谈。
陈离问道:“分别几日,小弟见张兄起气色好多了,那现在张兄可有什么打算?”
张仪道:“具体打算倒还没有。不过,近几日苦读恩师所传阴符,着实受益匪浅,越品越有滋味。所以,也不用心急,先韬养一阵也无妨。”
陈离道:“确实如此,这事也急不得。只可相时而动。”
张仪道:“我观贤弟,虽说似无大碍,但是眉宇之间似乎总有一股阴郁之气若隐若现,难道有何难言之隐么?”
陈离暗叹张仪果然目光如炬,淡淡道:“不瞒张兄说,确实有点小失意。”说着便简单说了与韩慕儿的过往。
张仪听罢哈哈大笑:“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不过,贤弟是聪明人,总会从这段失意中走出来,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贤弟不如也与我一同研习恩师所传的阴符,贤弟强过愚兄许多,相信必然会大有收货。”
陈离点头称是。
当晚用过晚饭,小唯果然如约与陈离共沐鸳鸯浴。二人小别,更胜新欢,一夜温存,自不必细说。
转眼之间,小半年就过去了。
时至初夏,天气回暖,万物复苏,柳绿花红,大地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说来也怪,研习阴符经之后,陈离果然对其爱不释手,只觉其囊括天地,包藏宇宙,仿佛人世间所有的道理,无不包含在其中。并以对阴符经的理解,自创一套刀法,名曰鬼谷七式,分别为盛神、养志、实意、分威、散势、转圆、损悦。虽只有七式,却招招变化无穷。陈离与张仪二人闲来无事,经常会过过招。张仪虽不以武艺见长,但也并非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兼且此时人人尚武,所以最初也可以斗个二、三十合。但自从陈离创出鬼谷七式,再交手张仪便每况愈下,直至如今在陈离面前再也走不上三合,令张仪颇为敬佩。陈离醉心于刀术,虽每想起韩慕儿,心中仍隐隐作痛,但也不是当初那般强烈了。
张仪武艺虽与陈离相距甚远,但因他志不在此,也并不为意。经过半年韬光养晦,张仪对阴符经也早已熟捻于胸,自此以为世间道理、列国形势,俱已尽在掌握,只待时机成熟,便可纵横天下。
一日午后,陈离正在练刀,突听院外有人不断唉声叹气,觉得奇怪,便出门查看。
只见院外歪着一辆华丽的马车,车轴已经断了,一个衣着光鲜的中年男子正在一旁唉声叹气。
陈离见状,向中年男子一拱手道:“老兄,车轴断了,怕车子走不了啦!”
男子见状,回道:“可不是,行脚赶路,最怕碰上此等事。”
陈离道:“看来怎么也要去大梁城里请工匠来了修了。”
男子道:“是吗,可到大梁城还有十数里远呢,这可如何是好?”
二人正谈话中,张仪也走出来,询问到底何事。
了解情况后,张仪便说道:“不如这样,请老兄先到寒舍歇息片刻。我家里还有一辆车,不如请车夫大哥赶着到大梁城里去,请工匠过来修复,兴许日落之前便可修好。”
男子一听,不由感激。待车夫赶车出去,便到张仪院中坐下休息。
小唯上茶后退下,陈离与张仪作陪。
张仪问道:“不知老兄尊姓大名,家乡何处,在哪行发财?”
男子道:“不敢当。在下贾兴,邯郸人士,平日里做些珠宝生意,这是刚刚自新郑而来,准备回邯郸去。”
张仪道:“哦?阁下是邯郸人士,又是商人,想必是家资巨富,又走南闯北,必然消息灵通。最近外面可有什么大事么?”
贾兴道:“大事?哈哈。生意人自然要关心些事情,因为这事关市场的行情,搞不好就会血本无归呀哈哈。若是说最近最大的事情,便发生在我赵国邯郸呀。”
张仪奇道:“哦?敢问邯郸发生了何事?”
贾兴道:“我国国君认命洛阳名士苏秦为相,举国托之。”
张仪惊道:“什么?苏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