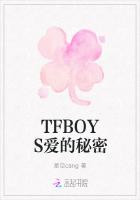当两个人相对而坐的时候,罗筱曼的眼睛有点迷茫,不知道该朝哪望。不过,到了这种吃吃喝喝的地方,化解这种迷茫的最简当方法就摆在面前,只要你愿意,随时启用。罗筱曼看似随意而且平静地从桌角拿起点餐的平板电脑,递了一个给吴骥尧,然后自己低下头,边看边说:
“我们先点吃的吧,还是很饿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冷静,无波无浪,罗筱曼在滑动手指的同时,心里暗暗表扬了自己:“干得不错。”
罗筱曼其实无心仔细看菜单,虽然她告诉自己,她和吴骥尧坐在这里,只是想把过去的一些事情说开,解除现如今的尴尬,无关将来,但是一想到吴骥尧的未婚妻,她就觉得不自在,尤其是感受到吴骥尧时不时投过来的目光。之前从严达那里偷听到信息是吴骥尧不愿意直接面谈,他可能更关注他关心的问题的答案。吴骥尧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以至于未婚妻/妻子今天回来,他都没有推掉今晚的聚餐(对,是聚餐,罗筱曼不愿意把这称为“约会”,虽然此约会非彼约会,但一想到这个词,会让罗筱曼泛起一种罪恶感)。这个时候,其实罗筱曼很希望葳蕤能够在耳边嗡嗡几句,如果他们真的出现,大声点说话也没有关系,因为罗筱曼实在是猜不出来吴骥尧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无法应对。但是,葳蕤有言在先,他们此刻并不会多嘴,那么,好吧,既然已经尽力去猜测,却仍然毫无结果,那就放弃,想一想她自己想对吴骥尧说点什么,以不变应万变。
吴骥尧呢,他有些木木地接过平板电脑。不时地看了看低头专心点餐的罗筱曼,想起两人第一次在面馆吃面的时候,罗筱曼热情地推荐。果然是时移境迁,人还是这么两个人,但却没有那种相视而笑的温暖,有一种强烈的落差感,“看,点餐也要各看各的,毫无交流。就算是嫁做人妇,也可以帮我一起点的啊,同事之间难免会这样。”时间此时仿佛是一个跛腿地老人,在静悄悄地缓慢前行,让时空都充满了孤寂。几分钟的时间,仿佛等待了很久。但罗筱曼仍然没有收到他发过去的脑电波,还在一页一页地看,丝毫没有征询他意见的迹象。看了看罗筱曼左手上的戒指,吴骥尧放弃了等待,他直接点了一份商务套餐。话说回来,他对这个地方的熟悉程度更甚于罗筱曼,真实的情况是他不需要罗筱曼的推荐,因为他对这里的菜单了如指掌。人就是那么奇怪,像个小孩,明明看见糖果就放在眼前,可以随意随时伸手去取,可还是会希望,别人递到他的手中,如果能拨开糖纸,放入他的口中更好。可能他只是小小地期盼一下,罗筱曼能像以前那样,对他投来一丝关注,即使是现在已为人妻,已为人母。
“我已经点好了。”吴骥尧将平板电脑放到桌上,身体向后倾,靠在了沙发里。
“我也是。”罗筱曼按了按桌边的小按钮,身体也向后移了移,靠在了沙发上。不过她马上发现,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四目相视的瞬间,她觉得有些尴尬,但表面上,她仍然若无其事,硬撑了一秒,然后把视线移到鼻梁处。
一股奇怪的气氛开始在两人之间蔓延,两人谁也没吭声。罗筱曼在想,怎样开头;吴骥尧不想先开口。
直至服务员过来送饮品确认点餐,几分钟的时间里,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罗筱曼发自肺腑地对服务员说了“谢谢”,然后拿起水杯,小小地喝了一口,淡淡的柠檬味安抚了她的神经,镇静了她那有些跳跃的思维。
“你不是有问题吗?怎么不问呢。”罗筱曼先打破了沉静。如果一定要开始,那么由她来敲响锣鼓吧;如果有些事情早晚都要面对,那么早点面对吧。
“你就没有想问的吗?”吴骥尧把双手交叉相抱在胸前,看着对面的罗筱曼。
罗筱曼摇了摇头。不是没有要问的,是已经不想再问,如果时间已经带走了某些东西,那么就让它们像吹起来的肥皂泡一样,即使再绚丽,也送它们轻盈地离开。更何况,她已经送走了它们。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吴骥尧把身边的纸袋拿了起来,放在了桌上,从里面拿出了一件颇有“特色”的陶瓷罐子,指着这个罐子问罗筱曼。
这是一个看似普通却又不那么普通的陶瓷罐子。说它普通,因为造型很简单,就是那种常规的放笔筒的罐子;说它不那么普通,因为这个罐子周身满是裂纹,似乎是破碎之后又重新拼凑而使它重生的罐子,以至于表面的绘画和字迹都已不再流畅,如果缺乏想象力,很难猜出那两个被肢解的字是“雨后”。没错,这就是三年多前,罗筱曼亲手做的、辗转送到吴骥尧手中的笔筒罐。
罗筱曼看着这个浑身是伤的陶罐,眼眶瞬时红了。她微微低下头,抿着嘴,掩饰着自己内心的起伏,努力地眨了眨眼睛,让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不至于掉落下来。如果不是在这,如果对面坐的不是吴骥尧,罗筱曼觉得自己铁定会抱着这个罐子嚎啕大哭。所以,此刻,她只能正襟危坐,让两个大拇指深深地埋进左右拳头里,静静地、冷冷地看着这个从自己的双手里诞生的希望。是的,彼时,罗筱曼对它寄予了满满的希望。可是,现在,再见它时,它已变了模样。虽然仍然直立在她的面前,却已是伤残满目。果然是物非人也非,究竟是怎样的缘分,让她和她自己亲手做的陶罐有了这样的巧合?罗筱曼有些惨然地笑了笑,心里默默地说:“很好,它本该就是这样的命运。这样倒也安心了,死心了,省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