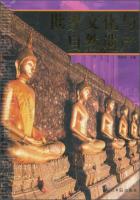七日之后,苏州,帝谭镇。
入夜,静谧的山间小镇被幽幽的炊烟缭绕,磅礴如山的万年古村从深不见底的峡谷中巍峨而出,古树间阡陌的吊桥将凭空而起的树屋与圆形祭坛相连。
万壑有声含晚籟,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副壮阔而不失婀娜的景象。
来到江南地界,享受的正是这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悠闲。
帝谭镇并不一味的安静,时常也称得上热闹。这黄昏时分,小道上也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翠幕斋就置身于其中。
现下,它的主人正坐在庭院中读书,年约二十七八的女子,眉间凝柔,指尖拨雪,一双垂珠眉端的是柔情似水。洒金的薛涛笺,书页泛着起舞的墨香,时不时清风拂过,带来树叶野花的丝缕烂漫。
远远望去,正是一副极好的夏夜抚卷图。
然而,一阵轻柔的敲门声打断了这宁静。
主人仍沉浸在遐思中,并未留意,于是那敲门声再次响起,高声了许多,这才惊醒了她。
她急匆匆地穿过庭院,打开了门。门外,是一个布衣荆钗,仍掩不住其国色天香,姿态风流的姑娘。姑娘笑唤道:“先生,多年不见了。”
这边,主人亦显出与她久别的样子,惊道:“云儿!”
“没想到么?”路凝云盈盈一笑。
“这可真是……”被唤作“先生”的女子大喜过望,“我竟不知道你会来,快进来。”
待二人坐好了,先生问道:“你是如何知道我住这儿的?”
“这个不难,自云儿小时,先生不就时时念着‘将来定要离开这刻板的京城,定居苏州’。到了苏州,再打听先生‘沈凡’的大名,又有谁不知呢?多年不见,先生竟一点未变。”
沈凡自谦地一笑。
“真能不变倒好了。云儿可是变了不少,几年前我离开时你还是个小丫头呢,如今也成个绝代的美人儿了,诗书又有进步吗?”
“先生真真是先生,”凝云嗔道,“来了不说嘘寒问暖的,倒先拷问起课业来。”
“嘘寒问暖?”沈凡显出识她的样子,“那么我就来嘘寒问暖。不在京城做你的小姐,到这江南来是做什么的?可别瞒我。”
凝云咬唇正色道:“本也不想瞒先生。云儿不愿再过自欺欺人的生活,是来先生处避难了。”
沈凡凝视她片刻,严肃道:“我不收留懦弱的逃兵。从何时起,云儿也学会逃避了?”
“并非事事都是可以干脆理清的事,并非人人都是先生这般干脆果敢的人。云儿的勇敢,皆是从先生这里学来的。可惜当初先生只授人以鱼,而未授人以渔,而今鱼用完了,只好再来先生处补充。先生若不收留,岂非落井下石?”
沈凡叹了口气,站起身来道:“说句实话,云儿,你十二岁时我就时常怀疑我们两人究竟谁是先生,谁是学生,今**仍在怀疑。我这就去打扫出一间房。”
“多谢先生了。”凝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
“然而……”沈凡回头道,“你仍有事没有对我坦白。”
“有些事,云儿难于启齿;亦有些事,云儿是为先生着想才隐瞒。”凝云低头道。
苏州的日子宁静且其乐融融。
每日,路凝云如小时一般,与沈凡读书论诗,赏花品茶,登山观水,听鸟览日。宫里住久了的凝云对江南水乡的一切都喜爱非常,终日不踏出帝谭镇一步。沈凡亦陪着她聊天游玩,细心地引导她走出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