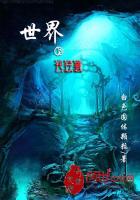那秦王望着秦王妃的背影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分明有些不寒而栗。
二人完全没看见偏僻处有人将见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收在眼中。
秦王来到了长寿殿,早有秦王妃在太后面前红鼻子红眼睛的把状子告了一遍。
那姜太后也是一脸铁青,秦王并不惧,只跪地行礼,“烨儿拜见母后,让母后这些天费心了。”
姜太后一根玉如意就丢了过来,砸在了秦王头上,碎成了两截子,“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母后吗?!你还知道母后为你提心吊胆?!”
秦王跪地磕头,“母后息怒!儿臣无时无刻不感念母后的恩情,您不能只听她的一面之词啊!”
姜太后一听,这萧烨把责任推到了秦王妃身上,愈加生气,素日她就知道萧烨和王妃不睦。
当初是她亲自选了姜家的女儿做他萧烨的王妃,他之前一直有个相好的,也被她这个母后给拆散,好在萧烨明白权力最大,自此也看淡了****,却不想变得荒淫好色,反倒亏待了秦王妃。
“你的王妃说了又如何,她说的有一句假吗?萧誉待你不薄,他身子骨弱,却为你的事费心费力,你倒好,出来之后就犯这样的糊涂,就算没什么大不了的,传到十一耳朵里他作何感想?!”
“母后您也是糊涂了!我怎会对十一弟妹有想法啊?我不过是做戏!”
如此那姜太后才消了气,疑惑的看向秦王,“做什么戏?事关皇族声誉,做得了戏?!”
“母后,眼下儿臣最大的威胁来自哪?”
秦王看向太后,然后一步步分析道,“儿臣不会如此糊涂。眼下皇兄虽然一时放过了儿臣,可他始终不会放心萧烨。尤其这一次,萧誉为我求情,皇帝势必会怀疑儿臣与他关系走近,有联盟之意。诸王结交,这是皇兄最忌讳的一点,在皇帝的眼里,只恨不得我们彼此防备互生仇恨才好。”
“所以你故意给老十一找不痛快对吗?可你别忘了,得罪了萧誉,你难道没有损失吗?”
“回母后,确实有些损失,可儿子不过是行为上有些唐突,并未有轻薄之意,何况他一介残王,与他的王妃感情淡漠,谅十一也不会与我们翻脸。估计他们也很快要返回江陵了,对我们没什么大的帮助。眼下,对母后和儿臣最重要的,不是尽快找到另一枚兵符吗?”
姜太后苍老的面上微微闭了眼,半天之后才睁开了眼,低叹了一声,无奈之下,似乎也觉得萧烨说得有道理。
“你不要对老十一做得过分了。这么些年,萧誉姑且念在我这个母后的面子上,自是不会有什么举动。”
只是当初先帝将第三枚兵符给了谁,又藏在了何处?
第一枚在皇帝这儿,第二枚在她这儿,皇帝一直伺机对萧烨下手,无非是想逼自己交出她手上的那一块,眼下要紧的是,他们母子要比皇帝早一步得到这第三枚兵符。
话说萧誉回到含章阁时,看见新月一直坐在那儿发愣,他心间不禁生了些惆怅。
许久,他终于开了口,“王妃在想什么?”
新月目光失神,依旧没有回过头来,只淡淡一句,“没什么。”
之后再无话。
萧誉心中不由地自责。
他自是知道新月不开心的缘由,那萧烨如何人品,他早有所耳闻,今日他的王妃定是受了轻薄,然而,他却不能立时为她出头找萧烨算账,甚至他都无法安慰她。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假装今日不知此事,才是对新月自尊的照顾。
他试图找点别的话,“新月,你不是想早些离开吗?今日我们就可以出宫回府。”
新月这才回过头看着他,那双眼眸分明抬不起精神,“出得了这宫,可这京城呢?”
只要一日生活在大梁京城,只怕这些个麻烦就会源源不断找上来。
萧誉自是明白她的心思,便道,“傻丫头,你倒忘记了,这江陵王自然要回江陵的。”
倏然,新月失落的眼眸顿时生了喜悦之色,“太好了,那我们早些回去吧!”
萧誉怔了怔,他知道她一心想着离开这后庭,然他想告诉她,遇到问题不要总想着去逃避,一退再退,将没有立足之地。其实迎难而上,也是可以避其锋芒。
他还想告诉她,遇事可以告诉自己,要相信他这个夫君。
然而,看到丫头开心的样子,终究他什么也没说,她开心就好。
萧誉淡淡的点头,“好,我们收拾下,这就出宫。”
二人出宫时一同坐着来时的车驾,新月喜笑颜开,时不时掀开帘子看着长街上的车水马龙。
暮色下,她眸中漆光点点,喜悦浮上了脸庞。
她之前脸上的郁郁寡欢一扫而尽,萧誉的心情终于晴朗起来。
霜降过后,早上还是挺冷的。
新月一大早就裹了好几层衣裳,喷嚏连连。
“公主,这是新做得几件冬衣,您瞧一瞧吧。”玉书过来。
新月漠不关心,“做好了啊。收着吧。”
阿珠走过来,笑道,“是王爷给您做的,您也不瞧吗?”
新月蓦地回首,就去看那案板上的衣裳,“那个,既是王爷送来的,我若不看倒也不好。”
阿珠和玉书暗笑,新月没瞧见她们的表情,只走上去展开那些衣裳。
其中一件乃是一件红色的狐毛披肩,其下边还缀着流苏,流苏上乃是玉片和宝珠,甚是好看。
新月很是喜欢,拿起来披在身上看了又看,又有些遗憾,“可惜,若是白狐的就好了。”
她到底还在孝期,她本不该穿红的,在宫里头没法子,但这是王府总该是穿什么管不着才是。
阿珠道,“听说这白狐的皮毛甚是难得,不如红狐多些。”她是在为王爷说情。
新月点了点头,却忽然又转过头看向阿珠,“谁说少的,本公主先前还见到太子哥哥猎到过呢。”
“公主倒是忘了,当时那只受伤的小白狐您舍不得,就养在宫里头。”
新月想起了旧事情,眼眸里的眼神有些哀伤,轻叹一声,“是啊,后来那只小白狐死了。”
阿珠有些后悔,“瞧奴婢这张嘴,不提过去也罢。”
玉书也道,“阿珠说的对,这凡事都要往前看。王爷准备后日离京回江陵,让咱们收拾下细软等物品,这些冬衣大约是为路上冷准备的。”
“后日?”新月重复了一句,恍然才意识到很快就离开这京城王府了。
耳畔是阿珠与玉书说起江陵王府如何大如何好的话,可她目光只停在东苑的一草一木、一亭一台,停留在房间的纱帐家具。
“不知不觉中,住在这里快两个月了。”
新月的话很轻,仿佛心头里的叹息。
阿珠最是了解公主这性子,表面上大大咧咧甚至心直口快,实在内心却又十分的敏感。
便安慰道,“公主放心便是,这京城王府会一直有下人打点的。再说,您之前不还是挺期待回南的吗?”
是啊,江陵郡与南晋的北境相接,或许会有新的机会。
离开的那日大清早,天气寒冷,青瓦上一片白霜。
新月没穿她十分喜欢的狐绒披肩,而是襦袄外罩一件兔绒马甲,这一出屋却才知道很冷,不得已又回去加了一件毛裘,镜子里的自己俨然胖了许多。
外面的阿珠喊道,“公主,您快些出来吧,王爷已经来接您了。”
新月自知萧誉乘轮车入房并不是很容易,虽然没设置门槛,但是入屋的台阶改成缓坡,仍有些费劲的。
新月顾不上别的,便也毛毛躁躁的跑出来。
果不其然,萧誉的轮车已经到了园子。
他端坐着,墨发一丝不苟,用玉簪束住,略厚实的玉白色锦绣缎袍,其上精美的绣纹在晨辉下浮光掠影,彰显了华贵清雅的气质。
他竟也没穿什么大氅。
此时的萧誉,目光并未看向她的门口,而是看着入冬的院落有些失神。
原来他不笑的时候,英俊的侧颜略显冷峻,有一种高贵的疏离感。
新月不由地露出笑容,见他不看自己,便喊了一声,“王爷!”
萧誉蓦地回转了头,冷峻的目光瞬时回暖,那丫头有些羞怯的站在门口,衣裳裹得有些多,倒像是个圆滚滚的球一样可爱又可笑,只露出那张圆脸朝气而美好。
面上终于绷不住的笑了,他转了轮椅过来。
“这是哪里来得糯米粽子?”
某丫头意识到在说自己的身形,上下打量了自己一番,一本正经的说,“这么冷的天,出门在外,多穿点准没坏处的,太注意胖瘦不好,像王爷这样,最容易感冒了。”
她眼里的萧誉就是为要好看才不穿大氅的。
话刚说完,新月就很不合时宜的打了一个喷嚏。
“外面风冷,王妃要慢慢适应一些才行。”
萧誉又看见阿珠和玉书都各挎着包袱,还有各种糕点吃食都备了很多,看样子像是担心没东西吃饿着一样。
萧誉抬眸看向新月,淡淡的打趣,“王妃莫不是担心,跟本王回江陵要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