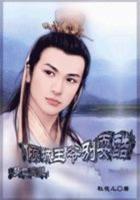菁芜意气风发,扶着窅美人走在通往瑶光殿的宫墙下,窅美人却突然不走,遥遥看着宫门,若有所思。
菁芜问道:“娘娘在看什么呢?那殿里已经没有娘娘在意的人了,娘娘怎么还这样看着它?”
窅美人悠悠一声叹,像是冷笑,又像是轻叹,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问着菁芜,“地位低下,被人轻贱是什么滋味儿?”
菁芜是在世俗的墨汁里泡大的,这种滋味当然受过不少,咬着牙愤愤道:“那是生不如死的滋味。”
“对了,就是生不如死的滋味。我真恨她啊!天姿国色,才华绝代,出身名门,身为国母,诞育皇嗣,又得国主专房嬖宠。瞧瞧她的瑶光殿,以珠宝为烛,曲栏金箔,销金红罗,组佩辉映,真真是豪华侈丽!”
“就算是笏满床又能如何呢?如今人去楼空,她所拥有的一切都化成灰了!娘娘也是称心如意的了。”
“就算她死了,可是国主对她还是念念不忘,她生前的时候,对我颐指气使,那眼里的傲慢华贵之气将我作践到尘埃里,她死了,还带走了国主的心,她真是阴魂不散!”
“娘娘不要忧心,国主对她再多的恩宠与思念也只能化为纸上的墨迹,以娘娘过人的智慧和手腕,又怎愁没有平步青云的时候呢?”
“是了,熬了这些年,也该到了透透气的时候了。听说这几日国主常常往瑶光殿中走动?”
菁芜点了点头。
“一呆便是大半日?”
菁芜默许。
窅美人嗤笑一声,“就算是国主睹物思人,就算是瑶光殿里有多少的珍稀宝贝儿,这些日子的光景,国主也都该是惆怅悼念完了,能留得住他的也只有人了。”
菁芜的三角眼闪烁着熠熠的光彩,“娘娘的意思是……”
“瑶光殿里如今还剩下哪些人?”
“先前服侍国后的那些宫女内监如今都已经遣散走了,只剩下一两个洒扫的宫女,再有的,就是国后的贴身奴婢——流珠。”
“流珠?”窅美人眯起了细长深邃的眼睛,“以前在府里就觉得她行事圆融沉稳,想不到她倒是安了这份心思,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倒是我小瞧她了。”
菁芜随即明白,“国后病重不能侍寝之时,千方百计推举她侍奉国主,只是她身上的那股狐媚子劲到底不对国主的胃口,屡屡入不了国主的眼。”
窅美人遥望着铅云低垂的天空,瞬息而已,浓云千变万化,她面无表情道:“今日不同往昔,她的那股狐媚子劲如今正是用的时候。进去吧。”
两人进了瑶光殿的宫门,殿室外一切摆设如旧,干干净净没有风尘,唯有成片鸟雀飞过,诉说着此处煊赫的红尘过往。
殿中无人,两人长驱直入,走到侧殿窗口的时候,窅美人便听到了国主与流珠的声音。
寝殿中,国主憔悴消瘦了不少,眼下亦是青黑一片,原本一双纤长秀气的手也瘦得青筋显露,他长身玉立,呆立良久,望着梳妆台上玉笥,呐呐不言。
流珠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玉笥中的药丸,那还是国后吃剩下的药,她怕国主睹物思人,强颜笑道:“这些香奁玉笥许久也没洒扫了,都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奴婢这就拿取擦拭一新。”
她的手刚拿走妆奁,便突然被国主的手抓住,流珠只觉得似被雷电霹雳击倒,浑然不知身在何处,犹如木偶般地立在原地,任一颗心快要跳出了胸腔,也任红霞染遍了自己的脸颊。
“官家……”
国主的神情哀婉痛楚,痛楚得近乎麻木,“不要挪动了,国后所有的东西都物归原处。”
流珠捂了捂发热的耳朵,望着国主那忧郁的眼,熟悉的痛又毫无征兆地袭来,那忧郁哀怜的眼神,怎又不会让她的心噗通地跳呢?
她怜惜道:“这瑶光殿有奴婢一个人守着就好了,国主还是少见国后的遗物,免得徒增伤感。”
“伤感?伤感抵不过虚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朕每次来到瑶光殿,就恍若回到了从前共享天伦的日子,就仿佛看见她的秾丽倩影还在朕的眼前,流珠,你说为什么她们母子就撇下了朕?为什么就忍心看着朕是孤家寡人?”
“官家!”流珠肝肠寸断,情急之中,又是哀痛又是爱怜地唤道,“官家怎会是孤家寡人?官家有天下,有子民,还有宫中诸佳丽,还有奴婢……”
她情真意切,顾不得许多,以自己的一双小手握住了他的手,仿佛要将自己所有的爱怜之意悉数给他,只要能温暖他的心,哪怕粉身碎骨她也愿意。
国主不为所动,依然沉静在落寞的悲痛中,他仿佛看见了国后正坐在头,绞着一缕红绒,娇怯万分地呼唤他一声“檀郎”,仿佛看见了国后正揽镜描眉,昔日的婵娟,今日却是芳魂渺茫,天人永隔。
那样的彻骨落寞、悲怆心神,又有谁能懂呢?
殿中寂寂无声,只有金炉香兽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仿若天地都已经静止了,窅美人不失时机地走了进来,妩媚唤道:“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