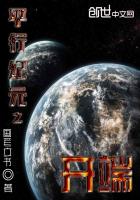他根本不敢再还手,此刻在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弯身求饶,若是空间足够大的话,肯定得跪下了,那副可怜巴巴的表情也挺惹人同情的,“我求求你,真的,我辛苦经营了这么多年,不能进去啊,我还有三个孩子呢,有个刚刚一周岁,他不能离开我,那是我唯一的儿子,我们老罗家三代单传,我......”
“小三生的吧?”
我不屑的哼道,“这都是自己作的,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看你在窑厂时那嚣张的样儿,当个官儿,挺风光是吧?来钱快,对吧?今天遇上我,你算到头了。”
“你,你为何要把我往绝路上逼?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就不能高抬贵手。你说,你到底要多少钱?只要你能开出价格,我都应你。我在大城市有的是房子,一百万,一百万行吗?不,价格你来提,你只要说出数字,我都满足。千万别揭发我,求你了,求你了。”
我相信这是他最真诚的忏悔了,他浑身泛着冷汗,肩膀一直在抖,像是临上刑场的死囚,在做着最后的殊搏,当听到一百万甚至更多的数字时,我这个卡里只有八百多快余额的**丝说不动心那是吹牛比,相信就现在罗队长的状态,我开价一千万,他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但,有些钱是不该拿的,拿了会做噩梦,早晚也得还。
即便我再心动也不能乱了方寸,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我秉持公正,深明大义,一定会有所回报的,即便这个回报的过程不会体现在收入上,但我想,于我个人的发展、性情塑造、机遇、超能力的晋升、社会认可度等等方面都有好处,这些东西是无形的,拿钱买不到的。
我很自豪自己能在这般诱惑面前保持初心,当即给了罗队长一个耳光,随即便押着他去了检察院。
!!!
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我才忙完,老罗当场被扣下,估计要被连夜突审了,走的时候,我看到他万念俱灰的面庞,心里也是一阵错愕,我清楚自己做的是对的,但却深深的伤害到了他以及他背后的家人。
还有那个一周岁的宝宝。
想到这里,我就踌躇、恍惚,仿佛迷离在下满大雾的海洋面,分不清方向,不知要漂向哪里。
彩蝶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在里面做笔录的时候我连挂了她三遍之后就关机了,接听后,她急切的问道,“哥,你,你在哪?你没事吧?”
“没事。谁跟你说什么了吗?这么紧张干啥。”
我问道。
“噢,梁子,说好像在商业街这边看到了你,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让我问问。你接连挂我电话,后来又关机,我就以为真要出事了。给李月茹和图心蕊都打了电话,她们也都不知道你的消息,急死我了。你去哪了啊?”
彩蝶说道。
“梁子不是要喝酒吗?让他备好,我一会就过去。放心,我没事。”
丢下话,我就挂了。
随后月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充斥着关切和焦躁,“贝勒,贝勒,你在哪啊?真急死我了。我满世界都找不到你。傍晚的时候我听同事说下午那家川菜馆门口聚集了很多混混,好像是要去打架,他们还录了小视频,我一看人群里有你。后来彩蝶也给我打电话说找不到,我以为出了大事,你要再不接,我都要报警了!”
“我去。”
网络的时代太可怕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能颠覆真相,幸亏我及时发声,否则真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她非要见我,没办法,我只能说是去她宿舍公寓接她,然后一起去梁子的店里。
心蕊就生分些了,她只是给我发了两条微信语音,询问我在哪之类的话,我并没回复。
貂媛的十几个未接让我一度头疼,她此刻定是心急如焚,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现在时间紧迫,她巴不得一天有42个小时可以用来抓捕贾凡国。
当然,朱少武也一直在等我,短信、电话打了一大通,我今天很疲惫,不想再跟他联络,明天吧,明天重整精神,跟他好好畅谈一番。
我给貂媛回了过去,总得先安抚好她的情绪,“你别急,总得做好必要的准备,另外适当的时候你可以自首,以欺诈之名躲进看守所,保命要紧。”
在非常时刻,高墙铁网的地方反而会成为貂媛的避难所,毕竟涉及的数额太大了,备不住别人会气急败坏、铤而走险,拿貂媛发泄。
“什么?不会吧?我真的,真的完了吗?”
貂媛欲哭无泪,过去那般坚强、专横的女强人在这一刻卸下了所有防备,像个孤立无助的残兵,在战场上负伤等待敌军的围困,手里仅剩的手榴弹将绽放出最后的绚烂,以自毁的方式保留最后一丝尊严。
“你认为呢?仅剩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贾凡国,但即便找到,也是未知数,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你佐这么大的时候应该想到一旦出现意外的后果啊。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你这几年快速崛起,春风得意,也是享受了啊,现在出了事,又不想承认现实,那没人帮的了你,首先你自己得做好接受任何后果的打算。”
我这么说,不是想刺激、打击貂媛,是希望她能把心放沉,不要再存在侥幸心理,只要人还活着,就一切还有希望,天还没塌,即便一无所求,最穷也不过讨饭,不死终将出头。
她一度无声,看她那憔悴样,我也挺感伤的,但我无能为力,她利欲熏心,这是自作自受,一切看命吧。
挂断电话后我又给弯弯打了个,她那边挺吵的,应该是在同学聚会,“你等会哈,我出去。”
很快,她那边就安静了下来,“贝勒,你是不是跟延明撞见了?”
“恩,不过他的事我以后和你说。你少喝点,早点回去,照顾好你姐,她遇到点事,情绪很不好。看好她。”
我嘱咐着便不再遛弯,在路边打了辆出租车直奔月茹那边。
“什么事啊?”
她着急问道,“我姐怎么了?”
“很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先这样。”
行将挂电话的时候,我却隐约听到了她那边传来了一声嬉笑的男腔,“哎呦,弯弯,你在这啊,来,跟哥喝了这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