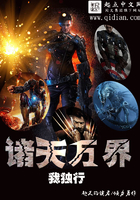次日下午,一点还差十五分钟,刘弈来到秦石武家。
他没来得及按门铃,门就自己开了,娜塔莎在门内探头向外张望几眼,倏地把他拉了进去。
“我把家里摄像头的录像关掉了,你来这儿没人知道。”
刘弈警觉起来:“等等,你什么意思?”联想那张过分的名片,他突然觉得背上一股凉意。名片他是阅后即焚,可既然能伪造出一张,再伪造一张也不是难事。
“我请你来,是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棕发女孩嘴角翘起,一脸狡黠,“今天小一要开会,晚上还要值勤,我们有的是时间。来吧,跟我过来。”
她当先迈步,刘弈却不敢跟她走,他甚至有了转身出门的冲动,即便在战场上最不利的局势下,类似的想法也从未有过。和她单独待在秦石武的家里,还不知道要待多久,这种事瓜田李下的,传出去就糟糕透顶。“所谓重要的事,”他迟疑地问,“可以先告诉我究竟是什么吗?”
“伸张人类最原始的权利。”
“啥?”
“什么时候开始堂堂的刘弈队长变得婆婆妈妈了?快来吧,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人类最原始的权利?略一思忖他觉得真是要命。她是在指繁衍?难道是看上了我,所以来找我出轨?这事荒谬得超出想象,一旦被人知道,凄惨的结局是注定的,会被秦石武活剥,而且也会伤透陆菲的心。
他快步跟上娜塔莎,打算向她把事情声明清楚。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对,她还没成年,这个瞬间开头被他毙掉;作为你的朋友我很荣幸,也愿意为你效劳……也不行,容易引起误会。
“呃,等一下,娜塔莎,”他结结巴巴地开口,“有件事,我得先和你说明。”他们正走在通往秦石武家地下室的楼梯上。这儿的地下室很深,足有四层,面积甚至比地上的部分还要大。
“不管什么事,都过会再说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娜塔莎说。她身形灵活,在楼梯上走得飞快。
一连走下三层,她仍不停步,直奔最深的第四层而去。上秦石武家作客时,曾粗略地参观过,刘弈知道第四层有避难用的套间、储藏室和一个未经装修的房间。套间里有全套的生活设施,食物和水储备充足,设有空气循环与净化系统,可供和外界失去联络的情况下支撑数月之久。
那地方足够隐蔽,又有床铺,难道……不能继续跟她下去,刘弈清清嗓子,正要出声,看到娜塔莎打开的是那间未装修过房间的门。“来吧,”她的笑容有些诡秘,“好东西就在里面哦。”
难道想错了?刘弈疑惑地跟她过去。偌大的房间仍是毛坯,未经粉刷的墙壁黝黑而粗糙,只有一盏连罩子都没有的裸露白炽灯悬挂在顶上提供照明。
房间中央是个被灰布蒙起来的东西,刘弈猜不出那是什么。话说回来,凭娜塔莎的脑子,常人想要猜中是白费心机。
不过这样一来,他也安心了。她喊自己过来,当然不是为了出轨,他有些惭愧。
“这就是我要给你看的东西。”棕发女孩搓了搓手,像是小女孩看到了心爱的甜食。她面对刚端上来的、还没开瓶的美酒时,就是这副神情。
“一尊后现代主义的雕像?”刘弈蹙眉。他不喜欢打哑谜。
“虽然不是雕像,但从艺术角度来看,确实是后现代主义没错,”随口胡诌的却很接近事实,“崔斯特,请把布揭开。”
“崔斯特?”这名字引起了刘弈的兴趣。
“是这个屋子里人工智能的名字,和桑南岛上的迈达斯是一个系列的。顺便一提,我车上的AI叫努波,宿舍里的叫伊尔明斯。扯远了,请看,你一定会满意的。”
刘弈没看到机械臂或者类似的东西,灰布却自行揭开。很神奇的设备,正想称赞娜塔莎一番,看清布下的东西,他倒抽了一口气。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是孟欣怡。女孩坐在一张泛着乌青金属光泽的椅子上,手脚都被暗红色的束带固定,嘴唇被胶带牢牢封住,一双眼睛里透着惊恐和无助的光。见到刘弈,她顿时开始挣扎,虽然不能动,不能说话,目光却再明显不过地表达着“救救我”的含义。
“怎么回事?为什么是她?”刘弈此刻的感受与其说是诧异,不如说是恐惧。女孩显然经历了和陆菲一样可怕的事,浑身上下伤痕累累,汗水和鲜血——也许还有泪水——****了前胸后背。
娜塔莎在椅子前踱着步子,以欣赏艺术品的眼光端详孟欣怡好久,才依依不舍地挪开目光,回答刘弈的问题。“她啊,”她拨弄着束成马尾的辫梢,“因为牵涉到冈格尼尔,所以大家都认为不适合送进你们天朝的拘留所,而是由我们看管,讨论后再决定怎么处置她。感谢上帝,我提出由我来负责此事时,大家都同意。”
“然后你就……”刘弈在战场上见到鲜血与残肢也面不改色,此刻却不自觉地感到脊背发凉,膝盖酸软。怎么回事?他在心底问自己,为了取得敌人的情报而拷打俘虏,在游击队时他甚至亲手干过,心理上从没像现在这般脆弱。
“是啊,是啊,”娜塔莎转着脑袋东张西望,寻找着什么,“稍等一下,这种时候不能来一杯,未免不够尽兴。啊在这里。崔斯特,送两个杯子过来。”
一辆酒店里常见的推车诡异地自行出现,吱溜吱溜地驶向他们,刘弈压根没见到这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娜塔莎从墙角抄起一瓶瓶身布满灰尘和蛛网的葡萄酒,随意地掸了下,在孟欣怡身上找了块还算干净的地方擦了擦手,打开瓶盖,在两只杯子里各倒了半杯。
“来干一杯,”她拿起一杯递给刘弈,“为了我们亲爱的孟欣怡小姐。”
刘弈接过杯子,没有朝嘴边送:“你是为了小菲?”
“当然,”杯中美酒一饮而尽,女孩棕色的发辫上下颤动,“见到她躺在床上,全身到处是伤痕,纱布上都是渗出的血,换掉之后又很快染红,好像永远也止不住的样子,我心都碎了。真的,不是幻觉或者心理作用,心脏实实在在的很痛,非常痛,就好像是——”
话语戛然而止,她猛然抓起瓶子,好像后面的内容没有说出去。来不及倒在杯子里,她举瓶就是一大口。“可最让我难过的还是她的眼睛,”娜塔莎居高临下地睨视椅子上动弹不得的孟欣怡,“和现在这个****不一样,瞧她,有那么点害怕,可还在骨碌碌地转着,肯定又在动什么歪脑筋,也许以为自己还能好端端地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