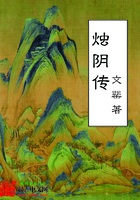究竟怎么回事?我记错了吗?刘弈目瞪口呆。这分明是昨天早晨起床时两人的对话,连一个字都不差。是姆布拉在开玩笑,还是我的头脑出了问题?
接下来的一切简直让他怀疑人生。每个人都在重复着昨天的事,整理装备,为动力甲罩上白布,队伍带上干粮和清水出发,在下午抵达巴勒贝克先生的旅店。各种怪异的念头在脑中纷至杳来,今天只是昨天的重复这种事,有可能是真实的吗?他分不清自己是在做梦抑或是回忆,身体的感觉明明很清晰,可就是觉得和任何东西之间都隔着一层薄雾般的帷幔。
很快,卡勒夫的队伍又一次来到旅店,法芙妮也准时出现。护卫的人数,女孩的话语,姆布拉拿出来的巧克力与饼干,费萨尔省下的部分,所有的细节,甚至卡车爆炸时升腾的烈焰都与昨天一模一样,刘弈再度经历昨天的战斗。
肥胖的军阀又一次破门而出,刘弈目视他背着小女孩跑下楼梯,消失在墙角后,跟着滚滚沙尘一路远去。仍然没有开枪,也许根本就无法开枪,无法忍受无辜的人倒在自己枪下,这一点他始终坚持。
于是队伍又一次无功而返,归途中费萨尔抱怨,法芙妮反驳,姆布拉打圆场,每个人都像是舞台上的演员,重复着表演过的动作与台词。
回到营地,还是昨天的伙伴们来安慰他。没关系的,只是一次而已,将来机会多得是。刘弈浑浑噩噩,机械地应和着众人,并非他有意敷衍,身上发生的事超出了可以理解的范畴,他的脑子近乎一团浆糊。
沙漠的夜晚很冷,最后一个同伴也在拍了拍他背后离去。刘弈裹紧毯子,不要紧的,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一定是劳累和压力导致的过度紧张。他只有这样说服自己,否则再坚韧的神经也无法承受,真要爬起来在营地里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次日清晨,他在晨曦中醒来,身上的毯子滑落。听到响声,姆布拉以充满朝气的声音问候:“早上好,刘,今晚准备干掉几个?”
刘弈听到自己回答:“一个就够了。”
“狡猾的家伙,”姆布拉佯作生气,“又把最好的猎物挑去。好吧,就听你的,不过其他的你别出手,都让给我!”
心底里一声呻吟,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在干什么?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整理装备,出发,战斗,逃跑的军阀,回营,同样的经历就像是电影在眼前回放,只不过他也是演员之一。
第三天就这样过去,接着第四天还是一样,第五天,第六天,每天都像两滴水一样完全相同。甚至连这个事实本身在刘弈的脑袋中也越来越模糊,唯一的不同只有他自觉正在越来越疲惫。
该试着改变,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又一次穿上动力甲出发时,他提醒自己。这副情景似曾相识,他想起北欧神话中伟大的战士们,他们死后灵魂升入瓦尔哈拉神殿,每晚纵情欢宴,而白天便无数次重复令他们获得无上荣誉的战斗。
除了每天都重复以外,其他的和神话一点也不像。放跑目标的战斗毫无荣誉可言,也没有瓦尔基里女神来带自己进入神殿,更没有宴会。
只是,为何会突然想到的是北欧神话呢?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照理说,一个十几岁的天朝少年,没多少机会了解瓦尔哈拉神殿。思索间,旅店又一次出现在地平线上。对了,我后来离开过这片土地,回到了天朝,那之后……
旅店临近,尽管事情荒唐、精神早已疲惫不堪,战斗的本能还在,他又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眼前。今天选择的还是相同的狙击位置,他在山腰伏下身子,确认状况没有异常。要不了多久卡勒夫就会到,接着法芙妮来告诉他计划稍有变动,而姆布拉会拿出饼干和巧克力。
一尘不变的生活像是牢笼,地平线上烟尘滚滚,卡勒夫果然又一次再同样的钟点抵达同样的地方。刘弈突然想到个至今为止从未考虑过的问题。那个令自己无法开枪的小女孩是什么人?
就他所知,卡勒夫是个残忍而贪婪的军阀,甘愿冒着危险背负的女孩绝不会是毫无关系的人。仔细想想,关于卡勒夫,了解的途径颇为单一,印象几乎全来自游击队的口口相传。女孩十岁上下,说不定是那家伙的发泄工具,在这片土地上,类似的事情司空见惯,曾令刘弈不适过好久。
不对,他推翻了这个想法,一来女孩衣衫整齐,二来工具不值得冒险带走,随手丢弃才符合军阀的作风。是私生女儿?他试着回忆女孩的面容。
恍惚突如其来。这边,实验室,陆菲,基因。一瞬间,他想起了很多与今天的任务不相干的事。我……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不,还是先面前的麻烦要紧。尽管已经见过无数次,刘弈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女孩的脸,越是努力去回忆就越模糊;军阀的面孔倒是清清楚楚,最细微的疤痕也不会错过。
他很快释然。没必要多去纠结,反正马上就能见到。巨响震耳欲聋,火光映红了面孔,旅店前的空地上,属于军阀卫队的卡车在烈焰与浓烟中四分五裂,车轮高高抛上半空。刘弈将瞄准镜指向那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楼梯。差不多再过五分……不,是四分二十秒,卡勒夫便会背着女孩从楼梯顶端的门中出来,然后溜得无影无踪。
枪声密如炒豆,爆炸接二连三,整座旅店沐浴在枪林弹雨中,尖叫的客人们四处逃窜,场面一片混乱。
该来了,刘弈移动枪口,瞄准镜锁定木门。经历了不知多少次,他在心中默默倒数,五,四,三,二,没来得及到一,卡勒夫破门而出。
心脏仿佛在这一瞬间停止跳动。怎么会这样?若不是身着动力甲,刘弈第一个动作就是揉自己眼睛。卡勒夫背上的女孩一如往常般瘦小,惊慌,可那容貌……没有看错,确确实实是陆菲。比起现在来要小了好几岁,满脸的天真与稚气。
为什么出现在瞄准镜中的是这张脸?他本该疑惑万分,可另外一个念头却牢牢地占据了此刻全部的思维。既然是她,那就好办了,多少天来,刘弈的手指第一次搭上了扳机。
楼梯很短,军阀在移动,陆菲的身子挡住了大部分的目标,留给刘弈的时间少到可怜,这是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狙击。但是没关系,包括为什么女孩会有着陆菲的长相、自己为什么困在这一天如此之久、为什么同样的人和事会反复出现,所有这些问题统统都无所谓,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我的子弹,绝不会打中她,绝不会。
他扣下扳机。肉眼捕捉不到子弹的动向,两秒后,红红灰灰的事物在军阀后脑炸裂。
终于,刘弈长长吐出一口气。随即,从眼前的旅店开始,战斗中的双方,倒下的军阀,燃烧的车辆,一动不动站定的女孩逐一如飞灰般飘散,身边的整个世界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