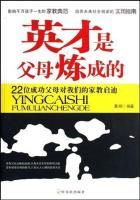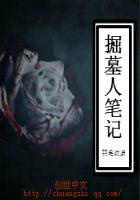被推醒的时候,已经东方破晓。
我揉着眼睛,用手指舒缓略略有些发胀的额头,问身边的空山晚秋道,“晚秋,你怎么进来我房间的?”
“不告诉你…”
空山晚秋看来并没有回答我这个没啥意义问题的欲望,只是催促着问我,“江枫,还给我治病么?现在已经六点多了!”
我反问,“今天西京女监那边还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吗?”
“我倒没有,不过你好像说过要去过问一下英氏集团工程师被打的事儿,江枫,难道你忘了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空山晚秋喊我的时候已经不是江科或者江队,改成直呼名字江枫。而按照心理学上关于称谓的理论,往往出现这个信息便表明,在她潜意识里,和我的关系已经变得相对更亲近了。
我应道,“对啊!要不是你的提醒我差点儿忘记了,嘿嘿,女犯人轻易扒光调研工程师的衣服…这踏马的,我要是不彻底查清楚,有些人恐怕还以为我江枫这个异地互查小组成员是摆设呢!”
看了看表,我沉吟片刻,道,“晚秋,现在时间还来得及,我先帮你看看吧…”
“嗯。”
我示意对方趴在更换过被单的大床上,指挥着,“衣服脱掉,裤子,你自己看着办…反正我不希望你身上有任何阻碍我动作的东西。”
提出这样略显暧昧的要求,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因此话并没有说得那么直白,不过,我却相信空山晚秋一定能够听得懂。
事实上,说这种极容易引起误会,甚至听上去充满挑逗韵味的话,我也是没辙。
毕竟,空山晚秋的情况和T市东河县医院性瘾症医生马昕很相似,因此,在我脑海中升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尝试按照救治马昕的方式对空山晚秋治疗。
而当时给马昕治疗的时候,并没有需要我动手,她自己早已主动变成一只雪白的小羊,甚至在强烈迷情促使下差点反强了我…
放纵思潮,脑海中,为马昕治病的那一幕再次浮现,我便有些心浮气躁,或者说胸焦气短。
那一晚的情形我记得十分清楚,从马昕背部尾椎长强穴开始,我沿着对方脊椎督脉线路,催动内息,最后达到头顶百汇穴,进入任脉,最后又回气于她腿部会阴穴,重归督脉,从而气行大周天。
当时我累得差点走火入魔,而马昕则将性瘾症患者从发病到巅峰再到平息的全过程,在我眼前完全展示一遍…
虽然我一直认为自己和马昕之间的关系没有超出底线,但不得不承认,整个儿治病过程中的各种旖旎,的确令我回味无穷…
正想得出神,空山晚秋却忽然抬起头,她明显有些害羞,目光躲躲闪闪,糯糯地问,“一定要这样吗?穿着衣服不行吗?”
“晚秋,”我忽然笑起来,“嘿嘿,昨天晚上,你不都要和我那啥了吗…好啦,和我做男女爱做的事儿都没问题,为什么对于堂堂正正的治病却怀有这种顾虑呢?我一直觉得你空山晚秋是一个豪放直率并且心地纯洁的女孩,现在看来我的判断不对,你还是深陷三俗中啊!”
听到我的话,空山晚秋不语,片刻沉默后,开始脱衣服。
我则出于避免看女人脱衣过程而导致对方心头升起尴尬的目的,转身走进卫生间,再次抽起香烟。
迅速将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在脑海中捋过一遍,我微微蹙眉,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头。
左思右想,我最终将这种‘不太对头’归结于,空山晚秋和马昕的症状看似相同,却存在不少差异。
虽然我还说不清楚二者之间的不同点到底反应在具体哪些方面,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但我却隐隐感觉出,她们俩的的确确不是同一种情况。
令我深信这种念头的原因,主要源于二者的病状表征---发病的时候,马昕的反常几乎完全表露在‘性’这个领域,她的动作、呻吟、欲望…也比空山晚秋更为明显。
而空山晚秋,她的病状却似乎反应在不同方面,并且突发性更显著、更危险、更有侵略性。
比如,发病的她可能下意识去踩我的脚,去接触陌生男人。又比如,几分钟之前还好好的,却在瞬息之间产生状况,以至于来不及关上办公室的门,被我撞破。
对比起来,尽管我认为马昕的情况比空山晚秋远为严重,但每次发病的过程却因为更强的持续性,从而几乎都会完整经历初始、渐强、剧烈、巅峰这样的过程。
环节多了,就会造成时间拉长,所以,马昕才可以在每次病情发作,达到难以抑制之前,自己通过各种办法缓解或者宣泄掉…
类似的结果,完全不同的发病过程,这让我对马昕和空山晚秋是不是同病相怜,产生极大怀疑。
…
掐灭第二根烟头,我发现空山晚秋一直没有主动出声喊我,沉默片刻,决定不再等待,推开卫生间的挂毛玻璃门,走了出去。
空山晚秋面朝下趴在床上,身上盖着雪白的被罩,乌黑的秀发披散在枕边,一动不动。
如果不是因为呼吸而使得身体略微起伏,我根本不能分辨她究竟是活人还是俯卧着的雕像。
“晚秋?”
我叫了她一声,并不确定她已经准备好了。
“嗯…”
空山晚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出来,却始终没有抬头看我,只是藏在雪白被单下的娇躯,起伏得更加厉害了…
“可以开始了吗?”我问道,不知怎么搞的,手心全是汗水,就像我这个悬壶济世的‘神医’,却在进行某种难以启齿的苟且勾当。
“可,可以,开,开始…”
她上下牙互相磕在一起,舌头打卷,显然比我更紧张。
一问一答之后,我俩忽然便同时失语了。
半晌无言,我终于失去僵持下去的耐心,伸手抓住盖在晚秋身上的被单,使劲儿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