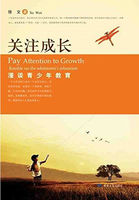1937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当麦金利号客轮顺着长江缓缓驶向黄浦江到达上海时,和煦的阳光正轻拂过长江口岸。太阳给向西延伸去的田野带来了鲜明的绿意,跟江里混黄污浊的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河岸两旁停靠着战舰,甲板和船舱上闪烁着严峻无情的阳光,偶尔闪现着一缕在甲板上反弹的光线,似乎在向我们顽皮地眨着眼。
战舰停航抛了锚,船尾的两侧飘着日本的青天白日旗。驱逐舰在熠熠生辉的巡航舰后的江水上随着波浪剧烈地上下起伏着,那些庞然大物般的巡航舰上体积巨大的船舱也跟着在无瑕的天空下笨重地摇来晃去。舰船上的甲板已经为军事行动清了场,火力也瞄准着西岸以示威胁。
麦金利号驶出吴淞口进入黄浦江时,头顶天空掠过了两队轻型轰炸机,机翼下还带着红白色的太阳旗标志。顷刻,飞机变换形成了纵队,头机迅速俯冲向了大上海市中心的政府大楼圆顶,五架僚机紧随其后。
三周前从西雅图起航时我并未料到会亲历一场战争。在东方居住了几十年的人意识到,中日两国最终还是逃不过一场恶战。不论是从国家荣誉或是国家安全任意一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忍受外来入侵者对自己的主权进行反反复复地挑衅。我此行的目的,本是进行正式的针对中文的研究与学习。与此同时,麦金利号客轮在横滨入了港,淞沪会战打响了。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不知道的是,我即将前往的并不是北平专门研究中文语言的学校,而是将作为一名官方的观察员陪同美国海军,亲眼见证中国为了维护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抗争。
游轮在距离吴淞河口一英里的地方停泊抛锚,虽然船上乘客众多,但却只有一小撮人跟我一同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勤务船。如今的上海并不是个适合游客停留的地方,甚至对于商人来说,他们在此殒命的几率也大大高于和平年代。勤务船从游轮旁驶出后向着八英里外的海关码头全力驶去,我坐在船尾,看着这一幕幕与我在十年前初次抵达中国时有着天壤之别的景象。
我那时与海军陆战队士兵一道前来中国保卫在此地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防遭受从南方北上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袭击。现如今军队已经在过渡时期铲除了各省的旧军阀,一个由国民党建立的政府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国家的首都也从北平转移到了扬子江边的南京。
共产党党内的分裂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共产主义的核心力量被清除掉,那些组织创建了红军和苏维埃政权以及号召土地改革的元老们倍感压力,一场长达九年的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在12月之前才刚刚进入了停战阶段。随后形成了日益坚固的抗日统一战线。
在十年间,尽管内部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却不可否认现在的中国变得强盛起来,通讯及交通情况得到了改善,法律日渐完善,教育也有了长足的提高。如今的中国由于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感的产生,其领导人坚持他们应该受到西方国家的平等对待。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在中国享受特权的时代迅速落下了帷幕。西方商人已经准备好了调整如何处理与东方国家关系的方法。但是,在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地方,居高自傲的日本却因中国的强盛而越来越焦躁不安。在日本所密谋规划的东亚新秩序中,一个强盛的中国并不具有一席之地。
1931年的9月,日本试探了西方列强对于通过暴力手段进行强行扩张的反应。日本的军队入侵了满洲里并且建立起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在列强看似勉强阻挠,实则暗地怂恿的情况下,1933年,日本强行占领了绥远的热河。
以上这些对于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行为激起了她的人民的强烈愤怒,并且加速了潜在的民族主义精神。国家救亡小团体在国家范围内疾风骤雨般地兴起,个人的以及政治上的对立情绪被搁置一旁,整个民族也平静下来准备迎接一场似乎不可避免的国家力量上的较量。7月7日的那一天,一支驻军在中国北部的日本特别派遣小队在卢沟桥挑衅一支中国的守卫部队,中国政府拒绝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的行为惹怒了日本上层领导。力量较量的时候来临了。
正当我还在脑海中重新回想这一系列的事件时,勤务船已经高速地沿着长江行至上海地区,这一航段沿着黄浦江北岸绵延约五里。船在外白渡桥掉头向南,在河岸西面的码头稍作小憩。码头的景象有些反常,平日里常常能见到的面粉厂成群结队的苦力、批发商,和沿街叫卖的小贩不见了,同样不见的还有摩托车、有轨电车、四轮马车、自行车和黄包车,连宾馆的塔楼和办公大楼也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大楼低层的窗户被壁垒所掩盖,前门也被用绳子捆扎成矮墙的沙袋壁垒遮挡着。在路的尽头,汇中酒店的顶层还有一个因空袭而被炸出的黑洞。
吉姆·迈尔斯,一位美联社的通讯员,在神户时加入了我的行程,现在我们都在询问对方应该做什么。
“我们还是先去找莫里斯·哈瑞斯吧。”吉姆说,“然后从他那打听打听现在局势怎么样。”
这个主意不坏,于是我们去了电报大楼。哈瑞斯是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在十年间他一直在上海负责着美联社部门,对目前的一切情况无所不知。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哈瑞斯笑着说,“现在正好是这场战争的中期。”
随后他给我们描述了事态发展的最新情况。“十天前,在殖民地区以西的虹桥机场,一名日本军官,一位日本海军登陆部队的士兵和一位中国的哨兵发生了一场冲突。从那之后,日本在特遣登陆部队实施了海军的强迫政策,中国也从南京调兵入沪。战争在四天前突然打响了。上周六,中国的飞机误把炸弹投向了这片公共租界上,炸坏了华侨饭店和汇中酒店,切断了法租界内的爱德华第七大街的水源。这场空袭造成了将近两千人的伤亡,其中包括几名外国人。外国的驻华领事馆已经建议疏散妇女儿童和那些并不是非要留在此地不可的商人们。现在,这条战线已经从苏州河边上的租界地边缘向北经过虹桥向外延伸了两英里,继而向东及东南至杨树浦地区。”
看起来似乎这是场预料之中的战争,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蓄势待发的形象早已经表露无遗。
在哈瑞斯的建议下,我们在美国俱乐部安排的房间住下。当把一切都安顿好后,我出门去拜访了海军将领哈利,我们的亚洲舰队的司令。
黄浦江上飘荡着美国、英国和法国舰队的旗帜,在河流下游及小河湾附近,停靠着日本装甲巡航舰,出云号主甲板上还插着一面海军中将长谷川的旗帜。在这些外国战舰的上游至法租界南部,中国已经布置好了一系列的汽艇以及用来组织上游船只移动的航海帆船。
我坐了一条小船抵达了停靠在国外舰队前方的奥古斯塔号军舰并且被引到总司令所在的船舱。在房间里我看到了一位外表上看着饱经沧桑的老人,不过他的表情太过平静和安详,以致于我无法猜出他竟已近古稀。在将要到来的事务繁多的一周中,我发现了他隐藏在如此外表下清晰的思维,敏锐冷静的目光下是一颗坚定的内心以及对日本非法入侵的企图寸步不让的决心。
“在我看来是这样,”上将评说道,“现阶段看来,你在这发挥的作用要比你在北平大得多。你对中文有了解吗?”
我告诉他,1933—1935年在北平执行公务时我曾学习了两年中文。
最终经由驻华大使同意后敲定的结果是,我将被派往上海任驻华海军武官。
那一晚,发生了一件在此后几个月内又多次发生的试探将军耐心和信念的事件。一艘日本驱逐舰逆流而上,在奥古斯塔号舰头三百米的地方停船抛锚,对黄埔区东部和南部的浦东中国驻军进行了整夜的狂轰滥炸,而临近奥古斯塔号的驱逐舰妨碍了中国军队的反击。第二天早晨,哈利上将向日本海军司令发送了一封言辞犀利的便条,却未收到任何回应。其他难忍的事情还在后面。
河滨地区的商业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年轻些的商人在上海志愿队工作,以协助英国和美国守卫他们的殖民边界。日本军队占领了虹桥和苏州湾北部的杨树浦地区,一些西方中立列强的官员却决心把交战国双方的装甲部队阻挡在北部的外国领区外,不过即使这样仍无法保证他们不被偶尔偏离的炮弹所误伤。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枪声和炸弹爆炸声响彻了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
在美国总领事馆,我发现了戴着眼镜的驻华大使克劳莱斯·高斯,他正在安静地处理着反对派留在桌子上的大量额外行政工作,一些做文秘工作的女性成员已经被转移,高斯大使和他的领事同事不得不接手大部分的文案工作。
克劳莱斯大使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候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归功于多年的领事工作彰显出来的高尚品德,在远东地区多年的外交经验,以及能够处理好随时发生的大量棘手问题,这些条件最适合这个职位。在战争期间的每个清晨,他都会与哈利上将和杰出的第四任陆战队司令官克劳奈·劳伦斯·F·B·皮尔斯在办公室见面。这个著名的三方执政小分队聚集在一起商讨解决目前的问题,并且为能够预见的突发事件制定应对计划。没有困难会妨碍他们三个人的合作,也正是由于他们准确的判断和高度的警惕,才保证了战时没有发生损害美国中立立场的行动或外交错误。
我在上海的同事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少校,忠诚的朋友爱德华·海根。海根已经作为助理海军武官开始履行职责,而我最终下定决心,将投身于交战国双方尤其是中国军队的事务中。
之前我曾参加过战争,但是这次是我第一次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正式观察研究的战争。摆在我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做?”一场战争需要被观察被见证,并且为了见证这场战争,我必须要投身战火正酣的前线。我申请能够被委任成为一名正式的观察员,蒋介石委员长并不接受这个申请。这些委任也没有被发布。
日子飞一样地过去了,我们的活动范围有限,若想观察整座城市的形势,只得到一栋中国驻军右侧的国际公共租界大楼楼顶去。最终,我分析出了中国对于军队中出现这样一个外国观察员的反对理由。首先,他们感觉一个西方的观察员有可能会嘲笑他们军队的管理方法以及设备;第二,中国军队的指挥官不愿意为西方的观察员承担出现安全事故后的责任。他们只是单纯不想徒增烦恼。
中国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此前,西方人并不愿主动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甚至连一丝意愿也没流露出来,就更不要说前来关心战争进程这种行为了。我决定去改变他们脑海里的这种偏见,并且设法从有实权的当权者手里拿到在警卫那行得通的通行证。有了通行证的护身,我能够毫无阻碍地进入战区,不必再因我的安全问题去烦扰沿路的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