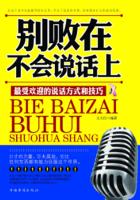我们的商人富有进取心,我们的企业家非常勤勉,我们的工人发奋地工作。我们的国家积累了过去无法比拟的财富。我们的银行拥有充足的黄金。在蒸汽机不知疲倦的轰鸣中,我们的工业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尽管我们有着如此之多的财富,然而,我们还有许多同胞遭受着贫穷。紧靠着富裕之国的大门,就能听到悲惨之国的呻吟——奢侈安逸是建立在痛苦与不幸的基础之上的。
国会的报告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披露了相当一部分劳动者所忍受的不幸。据描述,这些工人在工厂、车间、矿山、砖厂以及乡村中劳动。我们一直在通过立法与他们所遭受的悲惨环境作斗争,但事实似乎无情地嘲笑了我们。
那些深陷贫困的人虽然得救济,但他们依然并不领情。在施舍者与接受者之间连同情的纽带都没有。
因此,那些拥有一切和一无所有的人。富人和穷人,仍然站在社会的两个极端,一条巨大的鸿沟横亘在他们之间。
在那些粗鲁原始的人中间,贫困的状况是相同的。他们仅有的愿望很容易满足,他们对痛苦已经麻木。哪里有奴隶制度存在,哪里的贫困就不为所知。因为奴隶们仅够温饱正是雇主们的利益之所在,雇主们渐渐只关心雇员们最起码的生存要求了。只有当社会变得文明和自由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生活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他才不会遭受贫困,或是经历社会的不幸。
文明在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最高点,巨大财富也已被创造出来,贫困阶级的痛苦应该被舒适和奢侈来迅速地补偿,否则,冲突就不可避免。
许多现存的不幸都是自私造成的——或者是出于对增殖财富的贪婪,或者是挥霍浪费。增殖财富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动机和热情。无论是富国,还是不幸的国家,都把它作为主要目标。
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且让社会经济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发展。“力争第一”是正在流行的格言。高额利润被当作至善——不管它是如何获得的,或是付出了何种代价。金钱就是上帝。“只有魔鬼才选择贫困”。这种精神成了最高主宰。
许多所谓的“上层”,他们用来辩护的理由,不会比“下层”阶级更多。他们把金钱花费在打肿脸充胖子上,他们过着一种荒淫无耻、挥霍放荡的罪恶生活。
没有人能谴责我们的工人缺乏勤勉。他们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都更勤奋、技能更成熟。如果他们在节俭方面也如勤劳一样出色的话,他们也能够生活在舒适与富足的环境中。但是,遗憾的是,这个阶级有着挥霍的弱点。
即使工人中薪水最高的那部分人,他们的收入比专业人士的平均水平要高,但由于他们不计后果的消费方式,导致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属于比较贫穷的阶级。在经济景气时,他们不习惯为将来的坏日子作准备,所以,一旦社会压力来临,他们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一个能干的工人,除非他在节俭方面养成了好的习惯,否则,他的生活要求不会高于肉体的需要。他收入的增长仅仅能够满足他的畸形消费愿望的膨胀。查德威克先生说,在棉荒期间,“许多家庭排着队到为最贫困的人设立的救济站去领取救济。实际上,这些人以前的收入超过了许多助理牧师的收入”。
经济周期是生意场上永恒的规律,就像埃及法老梦中的瘦牛和肥牛必定交替出现一样。在一阵突然繁荣之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市场饱和、人心惶恐、社会贫困。
那些不愿动脑却挥金如土的人不注意吸取教训,对将来缺乏足够的准备。挥霍似乎是一个人最不可救药的缺点之一。贝克先生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所有在工厂区附近居住的人,他们不仅仅没有任何积蓄值得一提,而且,失业两个星期的工人们,因为缺乏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而正在挨饿。”
虽然没有发生罢工事件,但工人们已经迅速陷入了贫困的绝境。他们的家具和钟表被送到了当铺,当不幸的恳求声充斥慈善机构的时候,许多家庭已经在指望救济金了。
这种习以为常的挥霍——虽然其中也有许多是令人钦佩的例外——是导致工人们堕落的真实原因,也是导致社会不幸的重要根源。这种不幸完全是人性中的无知和自我放纵的结果。虽然造物主已给穷人创造贫困,但穷人并非必然如此。事实上也不定就不幸。不幸由道德的原因引起的——大部分是因为他们个人的邪恶与挥霍。
罗瑞斯先生在谈到那些有着高工资的矿工和炼铁工人的脾性时说:“用挥霍来形容他们的习性显得多么苍白,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鲁莽。这里的年轻人和老人、已婚和未婚者,都一致公开承认自己是挥霍放纵的人。每个人都听任这种鲁莽的性格来降低他们人性中的高贵品质。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敢类似蛮勇。除了弥补因为闲散或狂欢而损失的时间外,他们很少紧张地工作。他们热衷于为他们生病的朋友或是结婚的朋友举行聚会,这一切似乎仅仅是为了花掉他们以前的积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那种虔诚得让人奇怪的人,在困境中,他们经常举行祈祷会。他们真正的信条常常使他们堕入狂热的宿命论。人们痛苦地同时也确定无疑地看到,一年底到另一年底,过剩与匮乏总是交替出现,所有的人似乎都感犹豫不定。发薪后通宵达旦地挥霍狂饮,星期天沉醉不醒,星期一也许到星期二都上班,接下来的两三周内,整个家里都满地狼藉,不到下一个发薪日前,不会去收拾和整理;他们的孩子离开了学校,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去了矿井,他们的家具进了当铺。他们居住在拥挤泥泞的乡间小道上,他们的房子常常从屋顶到屋脚都裂了缝。没有下水管道,没有通风,没有足够水来供应——这样一种可怜的状况,是与他们领取不菲的工资同时存在的。这些工资本可以保证他们过上舒适甚至富足的生活。上述情况似乎表明,没有任何法律能够救治他们的毛病。”
我们已经在进行各种“改革”。我们已有了家务投标权,家务事可以通过选票来表决。我们已经着手减轻劳工阶级有关谷物、牛、咖啡、糖和供应品的税收。我们已经把相当一部分应由救济对象上交的税转加在了中层和上层阶级的身上。这些措施已经出台。但对改善劳工阶级的状况收效甚微,本身还没有落实这些主要的改革措施,他们也尚未在家里实行改革。然而,改革的结果对于每个个体来讲必定会是有益的。对个人有害的东西肯定对社会也会有害。当人变坏后,社会也会随之变坏。
仅仅抱怨法律的不公和税收的沉重是无济于事的。即使阿里斯多克洛蒂政府的残暴也比不上邪恶欲望的残暴危害之烈。男人们容易被引导到痛苦的路上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心甘情愿和自愿负责的——其结果就是虚度光阴、挥霍浪费、自我放纵、行为不端。因为我们所受的痛苦而去责备别人,比责备自己更容易被我们的自尊心所接爱。
非常清楚的是,那些生活一天到晚没有计划的人,缺乏条理的人,没有事先考虑的人——他们花掉了自己的收入,没有为将来留下任何积蓄——正在为今后的痛苦种下苦果。一切只为了今天必然会损害将来。一个信奉“只管今天吃好喝好,哪管明天是否去死”的人,会有什么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