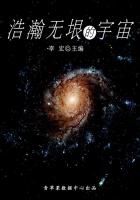1966年,考古学家们在泰国东北部呵苏高原上的班清镇发现了一些史前墓地,里面除了骸骨,还埋藏着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陶器、石器及精美的金属制品。一夜之间,鲜为人知的班清镇名扬天下。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斯蒂芬·杨来班清进行社会调查。一天,他经过一个筑路工地时,看到工人挖出一些陶器碎片,这些碎片上有一些奇怪的图案,便好奇地捡了几个图案美丽的残破陶罐带了回去。
1968年,美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伊丽莎白·莱昂斯把一些陶器碎片送到费城大学的考古研究中心。费城大学博物馆的考古研究中心将陶器碎片进行碳14测定,检测结果令所有在场的学者们大吃一惊,原来这些陶器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制造的!此后,他们又多次用不同的碎片通过不同的手段鉴定,但鉴定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学者们马上把伊丽莎白·莱昂斯找来,问她这些东西是在哪发现的?为什么过去考古学从没提过这个地方。
她也满怀疑惑地说,这些碎片来自泰国一个叫班清的小镇。过去从没人知道这个地方?
费城的学者们马上和泰国的有关文物部门联系,说他们准备来此地考察。
但班清在哪儿呢?为了接待费城的学者,泰国官员们马上拿来地图,因为他们也不清楚这个小镇的位置。
1974年,在联合国的资助下,泰国艺术厅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对班清开始联合考古发掘。开工的第一天,人们的期望值并不很高,很难想像这个人口不足5000人、世代以种稻为生的小镇会有很悠久的历史。然而,当挖掘到5米时,考古学家们惊呆了!原来,他们发现这是六层界线分明的墓葬。最深的一层可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最浅的也可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过去一直认为,泰国的可考历史至多有1500年,而他们眼前的一切都大大超过了传统认识中的泰国历史。
挖掘工作愈发不可收拾,每天都有大量的文物被挖掘出来,到后来实在多的让工作人员无法一时清点出来,只能以吨来计算。到1975年,班清已挖出各种文物共计18吨。其中除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金银装饰品之外,还有一些用象牙和骨头雕刻的人像,用玻璃和次等宝石制作的光彩夺目的珠串。
经过对挖掘的文物测定,这些珍宝至少已在班清埋藏了5000年之久。
同时,发掘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班清人已经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因为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年代大约在5000年前,是世界上历史最远久的发明。
过去的历史学家一直认为,5000年前的东南亚人还生活在原始的石器时代,而青铜器最早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冶金术是从西亚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而班清的考古发掘,对以往的这种结论将是一个最为有力的挑战。班清的青铜器将会促使考古学家对过去的观点提出新的见解。
事实上,那时的班清居民已经相当进步了。他们居住在固定的居民区,种植水稻及其他农作物,并且会制作漂亮的陶器。
那么,是不是青铜器的发源地可能就是在泰国的班清呢?
考古学家切斯特·戈尔曼是这次发掘工程的主任。他说,我们深信,炼铜术的起源最早可能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其发源地就在泰国呵功高原边缘的山脉之中。这里从古至今都以锡、铜储量丰富而闻名。班清的出土文物是丰富多彩的,有众多形状不一的陶器,在浅黄的底色上,绘着深红色的图案。这些图案看来是古代艺术家们随心所欲、一挥而就的。有些则是经过深思熟虑而精心绘制的几何图形,如同古希腊的骨灰罐上的图案。从外形上看,有些是颈部很细的高花瓶,这需要很高的制作技巧;有些是矮胖的大缸,上面却有着极为精致的图案,显得甚至不大协调。看得出他们在制作中的自由发挥和潇洒自如。
有关专家通过对班清挖掘的文物经过严格地清理、整理、分析之后,认为,班清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制品,并且在制作技术上有不断的创新。在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锛和青铜手镯的含锡量只有1.3%,制作也较粗糙,严格地说只能算作红铜制品。而班清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就制作了各种精致的青铜手镯、项链、戒指和长柄勺。
从班清人的制作工艺来看,他们的技术相当精湛,能在一把长柄勺的勺把上刻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图案。
同时,班清人在这一时期制作的青铜器就其铜锡配比来讲也比较科学。说明此时的班清人已熟练地掌握了青铜的冶炼和制作技术了。除青铜器外,班清的地下还出土了为数不多的铁器,有铁脚镯、铁手镯和双金属的矛头、斧头等。晚期的青铜制品中,有用含锡量高达20%的青铜锻打成的颈圈。因为含铜量这样高很容易碎,所以制作时须锻打成多股再扭曲而成。至于班清人是如何掌握这项重要技术的,考古学家们至令无法解开这个谜底。
班清文化不仅是东南亚,而且也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文化。最初的中东青铜是红铜与砷的混合物,后来,在接近公元前3000年时,锡取代了砷,青铜就变成了铜与锡的合金。中东或中国的冶金术可能源于泰国呵功高原这一带。
据此,有人认为,班清的青铜文化可能是世界青铜文化的源泉。
还有人认为,班清文化很可能是世界青铜文化的源头。
人们甚至猜想,班清的地下也许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
当然,大多的学者还是认为,那种把所有重大发明都归于一个源泉的观点是片面的。就冶金术来说,它完全有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独立演化出来的,也可能是同时产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班清出土的宝藏会越积越多,有关它的争论也将更深更广泛,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一个曾被认为是不可能存在的文明,确确实实是存在过的。
有人猜测,班清的宝藏的发觉还远未被穷尽,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个古墓葬,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埃及的帝王谷。
“问鼎”之“鼎”今在何方
鼎是古代人用于炖煮和盛食物的烹饪之器,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锅。形制以圆形三足者之多,但也有方形四足的。鼎有高足支撑,下面放木柴燃烧,鼎内便可烹煮食物。当然,鼎也可盛置食物。“问鼎中原”、“势成问鼎”诸如此类的成语中都有“问鼎”二字。我们今天对这两个字都不会觉得难懂。“问鼎”是指可能达到或者想要达到权力或者是荣誉以及其他的一切项目的最高峰。可是,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字的引申意义,它的原义是什么呢?正如几乎所有的成语都对应着历史典故或寓言一样,“问鼎”二字成为成语也是有历史掌故的。
公元前606年,中国历史上正处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战国中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经过了一番励精图治之后,使楚国变得国富兵强。于是他开始图取霸业,兴兵攻击陆浑之戎,直逼雒邑的郊外。当时名为众诸侯国之天子的周定王被迫派人来为他举行慰劳欢迎的礼仪。楚庄王向使臣“问鼎的大小轻重”,表明他欲灭周而代之的野心。从此,“问鼎”才成了具有特指含义的专用名词。
为什么楚庄王的一句问鼎就能反射出他的野心呢?原来这个“鼎”可不是指寻常之物,而是专指象征王权和天命所归的夏代“九鼎”。
夏是我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九鼎”就是夏禹制造的。就是传说中治水英雄的大禹。他建立夏朝以后,把华夏大地划为九个州,每个州设立一个最高行政官员叫做“州牧”。州牧又由夏王统辖。
据有关史料记载:夏禹令九个州的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了九只镂刻精美、古朴典雅、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铸鼎之前,已经先派人把各州的著名山川、大河和风景峻奇的地方,以及出产或具有的各种奇特的东西都画成图、编成册。然后由那些被精选出来的、技艺高超的工匠们把这些图画仿刻在“九鼎”上。每一只鼎对应着一个州,制成后的“九鼎”就象征着九个州,又象征着天下。这样既体现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集中,也显示着夏王已经成为天下之主,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九州”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自此,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之宝。
“九鼎”从问世以后就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们一直被作为镇国之宝和王权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
楚庄王所问的九鼎,正是周朝国家和社稷的宝物,是周王朝权力的象征。夏、商、同几个王朝的更替,是以夺得前代的鼎作为象征的。楚庄王问鼎,大有欲取周王朝天下而代之的意思,结果遭到周朝使者的严词斥责。对今人来说,“九鼎”的珍贵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显贵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包含的丰富的考古信息,它们身上浸透着我国当时的手工艺水平、冶金文明和人文地理。
可是,如此珍贵的“九鼎”早就在华夏大地上失去了踪迹,它们的下落,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
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传世之作《史记》中就已经无法确定“九鼎”的下落了。同一部《史记》的不同篇中,对“九鼎”下落所作的记载也不同。在有关周、秦的两个“本纪”中这样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周赧王死后,秦国从排雒抢走了“九鼎”,它们被掠到了秦国。而在《封禅书》中又说:“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沧没,伏而不见。”这段话的大意是:在周朝的天子之德日衰之时,鼎就不见了。这和秦抢鼎的记载是矛盾的。
而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又考证出各种各样的说法来解释“九鼎”的失踪。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周显王四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27年,周王室为了避免传国之宝落于他人手中,于是把“九鼎”沉没在彭城(今江苏徐州)旁边的泅水之中。他们还考证出:秦始皇南巡时,还曾派出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可惜最后一无所获,徒劳无功。
还有一种说法是:周王室在衰落时财政困难,入不敷出,于是销毁了“九鼎”铸铜钱。而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避免各诸侯国借此兴兵问鼎。
历代史籍中关于“九鼎”的说法还有很多。但是大多自相矛盾,或者自说难圆,谁也没有十分能令人信服的依据。直到今天,“九鼎”的下落仍然是待解之谜。或许有一天,“九鼎”还会重见天日,给世人带来一个惊喜。
猴首、牛首、虎首回故国
1860年,英法侵略者对驰名中外的艺术典范圆明园进行野蛮劫掠和焚烧,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精品从此流落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劫难之一。圆明园的文物被劫掠后的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一直非常关注着国宝的下落,企盼它们终有一天能够重回祖国的怀抱。虽然多年的辛苦追寻成果甚微,圆明园的文物大多“秘不示人”,但总有一点“蛛丝马迹”出现,时常点起国人希望的火种。
2000年4月,香港传来消息,香港嘉士德和苏富比两拍卖行分别将于4月30日和5月2日拍卖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走的四件圆明园珍贵文物。消息一出,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都在密切关注国宝又将流向何方。
国家文物局获悉后,立刻正式致函有关方面,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止拍卖圆明园文物,严正指出:这四件国宝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根据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1996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郑重声明中国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追索的权利。这乃国家和民族权益之所在。
然而,两家拍卖行置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依然照常按期进行拍卖活动。国人被激怒了,人们纷纷要求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抗议拍卖战争赃物。香港市民反映最为强烈,舆论普遍认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他们对拍卖行执意拍卖国宝表示愤慨,举行抗议活动,并要求特区政府做出果断决定,通过司法程序收回有关文物。法律界人士指出:按照有关国际法原则,只要在拍卖前能出示合理凭证,证明文物属中国财产,是可以阻止拍卖的。
4月30日,在多方努力均无效的情况下,拍卖会如期举行,海内外都拭目以待拍卖会的结果。下午,猴头铜像和牛头铜像出现在众人面前。猴首开价200万港元,拍卖场内竞争气氛热烈,现场一位留着平头的男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似乎对台面上的物品极为热心,志在必得,不断与其他买家竞价,每次都加价20万或30万港元,豪气吸引全场。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来自中国北京代表保利集团的易苏昊。
由于叫价声此起彼落,以双语报价的拍卖官几乎忙不过来。价码超过400万港元后,其他买家纷纷败退下来,只剩易苏昊和一名身穿灰色套装的女子相持不下。该女子由一位神秘买家通过电话遥控出价,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到第25次出价时,易苏昊叫价740万港元(包括佣金约818万港元),对手才知难而退,不再叫价。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里,这件猴首价钱竟涨了三倍多。
稍后,牛首铜像也以200万元起价,但这回战况改变,其他买家大多在旁观战,由易苏昊与透过电话出价的“神秘客”单打独斗,双方出价都又急又快,一分钟内叫价数次,最后再度由保利集团以700万元得手。会后,易苏昊表示,参与竞投主要是因为这两件东西关乎中国人民的情结,使中国人想起了伤心往事,竞投国宝也是不希望国宝外流。
5月2日,继嘉士德拍卖行无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告和抗议拍卖两件国宝后,苏富比拍卖行又拍卖了另两件圆明园文物:铜虎首和乾隆描粉彩镂雕六方套瓶。结果同样又都被北京的买家投得。由于前次竞投,各界目睹了中国人势在必得的情绪,因此这随后的拍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保利集团此时已充分预料到下面的拍卖价一定会抬得很高,但仍作出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国宝的决定,中间退出已不在考虑之内,“这已不是钱的问题,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
下午2点20分开始拍卖六方套瓶,开价420万。争持的对手只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其中一名是操北京话的中年男子,另一名是通过电话操英语的外国人,每口叫价基本上是50万跳一级,仅用了6分钟即以1900万元成交(包括佣金共2100万元)。最后的买家是代表北京市文物公司的刘岩。他说,能够投得这件国宝,并将其带回国,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另一件国宝铜虎首拍卖底价为300万港元,七、八分钟内有三人争持叫价37次,最后以1400万元成交,加上佣金总计1544万。买家仍是保利集团的易苏昊。
易苏昊在拍卖会后表示,所有这些文物一定要拿回去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毋忘国耻。他说,事先并无打算竞投国宝,皆因受到场外香港市民对拍卖事件愤慨的抗议所感动,继而激发起民族感情,遂决定竞投。他直言:“我们不买,谁买!我们不拿回去,谁拿回去!”
长沙走马楼简牍
1996年,湖南省平和堂商贸大厦在长沙市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一带的区域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闻讯获准于当年6月份开始介入该地区约1万多平方米范围建筑工地内地下文物的保护监控和抢救发掘工作。从6月至10月中旬,考古工作者先后抢救发掘出约20多口古代井窖和共存文物。
10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施工场的南部又发现了四口古井。当日上午8点30分左右,一位队员正在仔细观察前夜施工场地一台挖掘机附近散落的几堆黑色淤泥,当他用手上的小木棍轻轻地拨开淤泥时,没想到却拨出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拿起木板,揩去淤泥,木板上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墨迹,经过小心的用水清洗,发现墨迹原来就是书写在上面的墨书文字遗迹,墨书文字的意外发现令当事人顿时惊喜不已。在第一块墨书文字木板遗物发现之后,不久考古队员又发现了第二块、第三块……和更多的墨书文字竹、木板(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后经确认均为竹简、木牍)。之后,考古队员又顺着散落的淤泥和捡拾竹、木板的痕迹在施工场地的东南侧,追寻到了出土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的一口古井遗迹。但其井坑的上层已被夜间施工的挖掘机的反铲掀开了半边,现存古井的井坑内积满了水,水下是黑黑的淤泥。而值得庆幸的是从被破坏的井中残存裸露的黑泥地层断面上,还明显暴露出隐约可辨的竹、木板层叠的重要现象。
古井遭破坏,考古队员利用现有条件实施了现场紧急保护措施,同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经过对竹木简牍出土现场的进一步勘查,及时研究制定了对这口古井出土文物的应急抢救保护方案:①组织人力对工地残留的有关黑色淤泥土进行收集装袋,保护出土现场,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并对古井实施科学发掘;②组织人力沿着清淤运渣卡车行驶的路线,寻找收集散落在路上以及卸渣场中所有可能含有竹木简版的淤泥。经过严格、艰苦的发掘工作,终于使一大批因商业建设行为险遭灭顶之灾的珍贵历史简牍文物得到了及时的抢救保护,使其损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挽回。
这一古井中共出土了约10万枚孙吴时期简牍。并以此硕果荣膺199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称号。
三国时代战乱纷纭,文献史料也因此多有散佚,传世者罕见。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其年代性质属三国时期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且数量大都保存较好,记述翔实,内容丰富多彩,文字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等重要内容,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等重要领域,加上简牍出土具有地点集中,政区、时代相同等等特点,所以其史料价值极高,对深入研究和准确复原三世纪的长沙郡或吴国的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9年10月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整理与编排,《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另》上、下卷正式出版问世。借此契机,学术界对这批简犊的考证及其与吴国赋税、职官、仓廪制度、户籍管理等等社会制度的研讨也在不断升温和深化。
除其补史、证史的重要价值外,长沙走马楼简牍另一重要价值是为我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动的珍贵资料。由于传世和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数量都非常少,而走马楼简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书体有楷书、隶书、章书、行书、草书等。尽管其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与钟繇等名家的书法有天壤之别,但它们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民间流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与传世的三国碑刻和后世临摹的书法相比,其更具大众性和时代性。尤其是楷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恰为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的中间成长时期,可以作为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相当有利且直接的旁证。
长沙城自古流传着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对联;“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前走马;南正街,北正街,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都正街,街上登龙”。其中的“楼前走马”是指明代吉王(朱见浚)府的附属建筑走马楼,位于今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街一带。古井窖群的陆续发现和孙吴简牍的大量出土,给那里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最主要的是,约13万三国孙吴简牍的惊人发现,创下了20世纪中国考古简牍发现的最伟大的世纪记录。
《永乐大典》的惨重流散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空前绝后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
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告诉翰林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效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欲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而统之以韵,以便考索……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编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到了第二年11月,书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还觉得不满足,又命姚广孝、解缙等开馆于文渊阁,召集中外官员及四方宿学老儒充当纂修,命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生员缮写,并叫光禄寺供给酒馔。当时参加的人数,据说在3000人左右。
永乐六年冬,书成,取名《永乐大典》。在这部书之前,我国历史上已编纂了不少类书。然而,卷帙最多的不过1000多卷。三国六朝时,魏缨袭等编纂《皇览》680卷,梁有刘孝标的《类苑》120卷,北齐有祖艇等的《修文殿御览》360卷;唐代有魏徵等的《文思博要》1200卷,许敬宗《瑶山五彩》500卷,欧阳询《艺文类聚》100卷,虞世南的《北堂书钞》160卷,张昌宗等《三教珠英》1300卷;宋代有李防《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册府元龟》1000卷,晏殊的《类要》77卷。
就现存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诸书看来,他们都是分类抄辑的群书。《永乐大典》依韵目的次序编纂起来,一字不改进行抄录,也是空前未有的体裁。《永乐大典》的这种体例,原来是依据元朝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宋钱讽的《回溪史韵》的体裁而编的。他们把每个字依照“韵目”的次序编纂,但篇幅却都很小。《回溪史韵》已散失,仅见残本;《韵府群玉》则只有20卷。《永乐大典》却将其扩大了1000多倍。
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裁,无数宋元人的诗文和古代的方志、医书、杂书以及宋、元、明人的小说、戏曲等等,被大量保存、收录在内。当时所依据的主要是文渊阁的藏书。但就今日所传的《文渊阁书目》看,有许多书是超出《书目》之外的,特别是关于小说、戏曲等书。编者们并没有“正统派”的文学观念,眼光相当阔大,见解十分“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许多最可宝贵的民间文学作品。吉本《西游记》的一段《魏徵梦斩径河龙》被收录在“梦”字内;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全部被收录在“辽”字内。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国人将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更深的刻全面的认识。
不幸的是,这部大类书的命运是悲惨的,它的命运就如同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受尽了种种磨难和摧残。虽有正、副两部,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永乐大典》自编成之日起,一直深藏内府,一般人无缘得见。明成祖朱棣虽然动员和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纂了《永乐大典》,但在明代各帝王中,查阅过《大典》的却寥寥可数。据记载,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两人最酷爱读书,常阅《大典》。明孝宗曾经把《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过《大医院》,明世宗案头常置数册,按韵索览。
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某日宫中着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大典》重录后,有关其下落的记载很少,以致以讹传讹,弄得扑朔迷离,隐晦难觅了。
明神宗万历中,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曾建议刊刻《永乐大典》,但他没有说用哪个本子来刊刻。太史令李维帧说过“其书冗滥可厌,殊不足观”的话。他对《永乐大典》的看法当然是错的,但从他的话来看,好像见过似的,从他们二人的言行可以看出,明万历时期《永乐大典》尚是完整无缺的。
至明末,有些人就认为《永乐大典》已经不存在了。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有言:“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谈迁以为正本、副本早在万历末年已经不存在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持有与谈迁一样的看法,认为“全部皆佚”。
明末宦官刘若愚熟悉宫廷内情,写了《酌中志》,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书中记载;“旧《永乐大典》两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在明清之际,宫廷内外的人由于不知道《永乐大典》正本抄本所在,因而便猜疑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了《永乐大典》,是嘉靖抄本,并已有残缺。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雍正间又把《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改贮在翰林院。李级、全祖望在翰林院也见到过。全祖望却认为正本没有遗失,藏在乾清宫里,他曾经想建议用宫里的正本来补配副本。直到清末缨基孙也抱有与全祖望相同的观点,而且他认为正本是在嘉庆间乾清宫失火时消亡了。但实际上,全祖望、缨荃孙对正本的下落都只是猜测之辞。
乾隆九年至五十四年间,在编制《天禄琳琅书目》时,把宫中的善本都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进行编目。如果宫中藏有《永乐大典》正本,怎么会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中呢?
后来修《四库全书》时,屡叹《永乐大典》副本不全,曾在宫里宫外都找过。《永乐大典》是万卷以上的巨帙,如果正本藏在宫里,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并没有找到。清高宗曾有诗:“《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清高宗对《永乐大典》不全亦无可奈何。可见《永乐大典》正本“鼎革时亦有佚失”,副本在明清之交也有散失。但正本何时亡佚,史籍并未有明确记述,学界估计毁于明清鼎革之际。《永乐大典》正本的亡佚,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损失。
《永乐大典》副本的悲惨命运,正是近代中国面貌的缩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在这部书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痕。
《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到清康熙这110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宬,雍正年间又改藏在翰林院的敬一亭。开三礼书局的时候,李级、全祖望都利用过副本,并发现有残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要从《永乐大典》中收辑佚书,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1000多册,共计2432卷。《四库全书》总编撰官纪昀对《永乐大典》已非全帙而深为叹息。这两千多卷何时亡佚,没有一丝线索。
据传,康熙间修书时,总编撰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翻阅此书,估计残缺部分尚留存在他们家中。清高宗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这些人家中查问,并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同时估计到《大典》是“前朝旧书”,很可能流通在书贾坊林间,于是又派专人“留心体访”。尽管如此,仍没有找到一本,或寻访出下落。副本2000余卷的亡佚,也可能在明清之际,这是《永乐大典》副本的第一次丢失。
清乾隆时,乾隆帝非常重对《永乐大典》的保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发生过一次《大典》失而复得的事件。当时《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偷去。清高宗对这件事非常恼火,他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任纂修等携带外出。”命令立即“查询明确,据实覆奏”。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缉盗贼。
由于官府搜缉很紧,《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把这6册悄悄放回御河桥边。虽然《大典》失而复得,但黄寿龄受到罚俸3年的处分。从此,四库馆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携书外出,《大典》遗失的机会自然减少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永乐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为的破坏。《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一些馆臣视《大典》为“精华采尽,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而后,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时都曾利用过《永乐大典》,但保管制度已经相当松散。尤其是道光后,《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
更为可恨的是,一些官员乘机偷窃。按说,《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巨帙,不易拿走。可是翰林院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极为巧妙。据缨基孙记载: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晚上离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却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而去,丝毫不起疑心。日积月累,像文廷武之流一人就盗走一百多本。
《永乐大典》亡佚日多,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用每本十两银子的“高价”暗中收购。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5000册,至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800册了,亡佚之快,简直惊人。
《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是帝国主义两次对中国的侵略。咸丰年间,英法帝国主义谋求扩大侵华特权未果,便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称为“万园之园”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化为灰烬。翰林院中的许多珍贵典籍,侵略军也肆意焚烧拿取,任意糟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这次劫乱中被焚毁,《永乐大典》也焚毁不少。当时相传英人劫走的《大典》最多,故后来黄公度出使英法时,王颂蔚临别赠诗说:“《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岩伏。颇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
帝国分子掠夺我国珍贵文物的罪行是不胜枚举的,掠夺《永乐大典》仅是其中的一桩而已。事隔四十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永乐大典》又遭受了另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组成八国侵华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遂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被焚,其余也散落在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军事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
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英国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写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
另一个叫朴笛内姆威尔的,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得更为详尽。他写道,翰林院里的藏书“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这些典籍“有与黄金等价者”,在猛烈的枪声中,有人用火具抛入翰林院,“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文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称拣选抢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抢之而奔”。
朴笛南姆威尔、翟理斯等人,当然也是属于在火光中恣意“拣选”、抢之而奔者。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哄抢完毕后,还装模作样地到总理衙门报信,真正是贼喊捉贼。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事后,在废墟堆中,还有不少人捡到《永乐大典》,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侵略军的马槽下就捡到《大典》数十册。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流散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成为他们象征东方文化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1920年,时恭绰先生就曾在伦敦买回“戏”字韵中的一册。
帝国主义分子不但越火打劫,还千方百计地从中国私人手中攫夺,东洋文库便是一例。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利逊文库,为英人莫利逊创办,他在庚子事变中掠得《永乐大典》六册。莫利逊死后,东洋文库从他的妻子手里接收了六册《大典》,同时委托北京等地书肆,如有出卖《永乐大典》者,希望首先告诉他们,因此又购得多册。1943年春,东洋文库得悉吴兴嘉业堂所藏的49册要出售,便勾结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强行购买,因此,这一大批《大典》为满铁图书馆占有了。
还有一些官吏和书商为贪图暴利,也随便将《大典》售于外人。民国三年(1914年),有个叫董康的官吏曾携带17册《大典》东渡日本贩卖。又如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美国还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一册《永乐大典》。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永乐大典》在暗偷明抢、巧取豪夺之下、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少量《大典》,有一些也远离了祖国,流散到异国他邦(美国有45册,英国38册,日本55册)。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为之痛心。
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之间相互送还对方的文物。1951年6月,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把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11册送还给我国文化部。这是《永乐大典》自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灾难后,第一次从国外被送还。1954年6月,前苏联列宁图书馆又把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送还我国外交部,这两批永乐大典,都先后移交至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954年,前苏联科学院又把《永乐大典》“梦”字韵一册送还给我国访苏代表团。
1955年12月,在原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期间,将1900年从北京翰林院里散失出国流落至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3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并由文化部移交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这些资料珍品的失而复得真可谓我国文化界之万幸,这些图书内容,收录了价值极高已久已失传的书籍,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均有填充空白之价值。
时至今日,冷战结束,国家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若要向那些盗掠我国文物的国家索要失窃之物是相当困难的。虽然我国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及私人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但长路漫漫,坎坷重重。我们只能祝愿这些散失在外的珍贵人类遗产会得到妥善保护和有效利用,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得以充分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