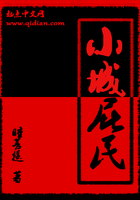在我人生的履历中,有一座山是与之息息相关的,那就是故乡的山。幼时随父母居住在乡下,村子后面就是一座小山。因为山在村子的北面,所以我们都叫它北山。北山并不太高,也不伟岸,在八百里沂蒙山区算是低矮普通的了。但是站在山上,你才发现山并不孤单。山的两边和山的后面,有一座座更高的山相连,形成连绵的群山,山脚下的小路,有如长长的臂弯,将山与山紧紧相挽,蜿蜒而伸展。
山上有一层层的梯田,不知什么时候建成的,从我记事起就围绕在山上,夏天庄稼生长起来,梯田被茂盛的禾苗层层碧染,到了秋天,又被将要收割的庄稼铺成金黄,就像一块经过精心设计的画面,或黄或绿,秩序井然。山里人烟稀少,零星居住着一些人家,房屋建造在山洼之间。这样偏僻的地方,却能给小小的村庄带来希望,人们吃的是山中粮,饮的是山泉水,种的是寻常菜。崎岖的山路织起山中的日月,缥缈的炊烟袅娜出家园的温暖。
山里人的身影,总在这些梯田里忙忙碌碌,面朝黄土,背向蓝天,每天重复而又简单。偶尔,他们会把身体侧弯,用身边的农具肩起一捆捆庄稼,或挑起一副硕大的水桶,以此盛水浇田。但是他们的劳动,永远是那么烦琐而又沉重。庄稼人的腰和肩最为灵活,也最为劳累。他们,站起来是一座高山,弯下去就是一片土地。一双肩,担起的是家庭和责任。
在岁月的长河里,什么都会老去,唯有山不会老。然而山不老,却龙钟了身躯,无处不显出山的老态。故乡的山,便像极了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黝黑的山崖,风化的石壁,让人猜想,千百年来,它究竟付出了多少?她像一位伟大的母亲,用逐渐失血的身躯,滋养山中的植物,抚育身边的子民,护佑着岁月的平静,村庄的安宁。山,生长着,改变着,摧折着。山上的梯田,见证了山的不平凡的历程。
听老辈人说,山上原本是有许多树,后来为修梯田,几乎砍伐了山上所有的树木,仅留下山头很少的一围,乱蓬蓬地立在山顶。在这个偏僻的村子里,拥有一块小小的土地,是多么的珍贵!幸而在梯田的坝缝里,倔强地生长出许多杂树和灌木,有茂盛的酸枣棵和洋槐树。酸枣红了的时候,孩子们提着小铁桶涌上山去,小心翼翼地往下摘,一边摘一边往小铁桶里塞。枣肉可食,枣仁是可以卖钱的,还是上好的药材。一小铁桶枣仁能换两个演草本。山在成熟的季节,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村后有一条进山的小路,路上常见到熟悉的中草药,百部、枸杞、何首乌,等等。在与杂草一起生长的树棵里,也常发现山葡萄、覆盆子。有的芳容可辨,有的叫不出名字。浅春时,开出白色、浅紫、粉红的小花,细细密密地铺满窄窄的小路。果实成熟的季节,疏朗的藤叶间,托出大红珍珠般的晶莹的山果,透出水灵灵的诱人之色。采一把轻轻地捧在手里,稍一用力挤压一下,指缝间就会流出浓浓的果汁,细细地品咂,那甜蜜的滋味,一直流淌进心底。
山给我的记忆,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生活还较为贫困,好在我们读书,一般不缴学杂费,学校里的老师买不上备课本时,就带领学生到山上去采槐叶,也没有防护手套,一把把地往怀里捋,捋得手痛,还常遭藏在叶下的毛虫的袭击。等槐叶装满麻袋,老师带领学生把槐叶运下山去,送到一个专门磨粉的磨坊里。一大袋槐叶,只磨出很小的一袋粉。装满槐粉,扎紧袋口,上秤过秤,过秤的人在一张小纸条上记下斤两,老师们就可以拿着记下数字的那页纸条,到指定的供销部门领取粉笔和纸张了。
我平时一个人不大上山,父母也不同意我们上山。无论多忙,父母也忘不了给我们严加管束。倒是母亲,曾在山后一所小学教书,偶尔有机会跟了去,一边听母亲教书,一边两眼朝山上打量,那些裸露的岩石,零落的植被,整齐的梯田,还有上面的庄稼。小路弯弯地坡挂在山上,在青的植被和乱石间穿梭,从这头开始,又从那头消失。远方,云飘雾移,极富诗情画意。
终于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偷着上山,一路小跑爬上山去,摘食山头上的红枣。正当我们摘得痛快,突然有人喊了一声:看山的来了!熟悉情况的同学连忙往山下跑去。正是夏天,红枣还没有熟透,枝头上挂的还是拇指大小的青果,若被看山人发现,必然不会轻易放过。只听有人一路喊叫着,向我们跑来。由于不熟悉路况,我和一位同学被乱石铺满的小路搁浅下来,越是害怕,脚下越是不听使唤。
幸好,那人并不是看山人,而是一个有点智障的青年,他并没有跟我们往山下跑,而是在我们身后追随了一会儿,又沿着梯田往山后跑去。险情排除,我们这几个人却跑散了。我们找不清方向,也找不到回家的路,纵横的山道在面前分成数条小路,就如同把我们打入了迷魂阵,等到夜幕降临,也没人前来迎接,只好迟迟疑疑地向村庄的方向摸去。远远的,我们看见了村里的灯火,一盏盏地亮了。就是那次,我被那些灯火深深打动,原来温暖,也能来自那些毫不起眼的星星点点。
时间一晃,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已离开故乡,记忆中的那座山,也已被我遗忘。至今天,登山已成了一项不可缺少的运动,人们背着干粮,身着先进的装备,走遍了山水。一为健身;二为减肥;三为减少营养饱和的困扰。偶尔,我也去附近的山上转转,访古寻幽,登高望远,但见一座座山峰,层峦叠嶂,苍鹰在山顶翱翔,鹰之背上,蓝蓝的天空透出一片深邃,漫卷着丝丝缕缕的云彩,像棉絮一样飘逸、洁白,俯瞰脚下的村庄、田地,也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
有一年,我路过北山,车在山下打了个照面,就在将要驶去的瞬间,一抬头,我又看到了它,我惊讶地向车窗外遥望,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山的绿,我的眼眸,立刻被那浓重的色彩照亮了。山在我的眼前湿润起来,朦胧起来,随之清晰起来。如同一幅无尽的画,漫卷而来,随着汽车的行驶,旋转不止。一缕清凉的感觉扑眼而来,湿漉漉的,仿佛还有打湿的痕迹。我突然意识到,眼前的这座山,与我记忆里的北山相比,有着怎样的差别——当年的北山有着怎样的荒凉,现在北山就有着怎样的繁茂!
那绿,是初生的植被吗?是雨后纷乱的草丛给人的假象吗?自然不是,我揉了揉眼睛,挥起手,向它轻轻打着招呼。虽是风起青纱的时节,但我看得出来,那上面蓬勃地生长着的,不仅仅是庄稼,还有一棵棵树木,用执着而顽强的根须,深深扎在岩石间、土壤里,那抹浓浓的绿啊,正是年轻了的山,用青春的颜色织成的幕帘。在注重生态保护的今天,故乡的这座山,再也不会远离美好的、没有尽头的梦,不会从我的记忆里失去。有了梦,故乡的人们就不会走远,人不走远,心就会永远停留在故乡。停留在这里,停留在摇曳多姿的青山绿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