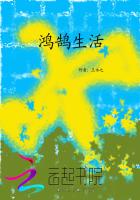那一天丰城下了大雪,老天爷就像是扯了棉絮往下抛一般,把城里覆得白茫茫一片十分寡淡。阮盈袖坐在江家四小姐的床帐前把脉,眉头几乎拧成了一股。
太重的伤了,下手的人几乎是毫不留情。阮盈袖看看江四小姐和她年纪相仿的脸微微怅然,听说她叫江御儿,早有传闻说美貌非常,称得上是丰城第一美人,果然今天得见,即使她在昏迷里,眉眼里都带着刚艳,就像一朵大红的蔷薇,凌风而开。
阮盈袖把好脉,向旁边桌上自斟自饮的江御阳说:“四小姐的病,我治不好。五脏六腑同四肢都受了重创,还能活到现在,算是奇迹。”
阮盈袖怕江御阳,她知道江御阳就是害常莫远家破人亡的元凶。但人生总是有这样多的无奈,她是医者,就不能见死不救,并且她觉得,自家妹妹都要死了,做大哥的还能不管不问,大概四小姐和她的哥哥们本就不是一类人,所以江四小姐,也许会是个好人。
江御阳听到这消息竟也没什么反应,想了一会儿,说:“那你帮我看着她,到她不成了来报一声得了,老爷子等着回话——放心,看护的钱也是少不了你的。”说完他就走了。
阮盈袖觉得心寒,就不想再想起江家的那些人,开了张药方给江御儿吊着命,就这么慢慢耗着。
时间过得太慢,阮盈袖看着香炉里的缓缓青烟百无聊赖,不知为何忽然就有种莫名的感觉,江四小姐仿佛在等什么。
她不仅有点骇然。阮盈袖年纪还浅,想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在一个人内脏俱损的时候一直支撑着她的意念——都六个时辰了,从卯时被江家人吵醒拉到这里来,到现在酉时天已全黑,江御儿真的已经撑了整整六个时辰。
房内一灯如豆,江御儿还是沉沉不醒,阮盈袖在小桌上趴着迷迷糊糊也只要睡过去,忽然听得有一把清泠的女声:“程厉。”
阮盈袖一下子精神起来,抬头打量了一眼屋里,终于发现江御儿好似有觉醒的征兆。
她连忙走过去,握起江四小姐的手腕,脉相忽然很有力,然而她知道这叫回光返照。江四小姐微微睁开眼,像是要说话,阮盈袖温言说:“你等下,我去叫你的哥哥,还有你爷爷。”才要起身,被江御儿狠狠握住。
江御儿气息虽微弱,但濒死之时反而尚能支撑,她轻轻说:“我不认得你是谁,但只要不是这家里的人,就总是好人。”说着她示意阮盈袖将自己左手上的镯子摘下来,“江御儿一生从未求过别人什么事,但我晓得自己要死了,只求求你,如果在丰城,能遇到一个叫程厉的男子,把这镯子给他。”
阮盈袖一时为难,且不说天下之大,便只是这丰城,就不知道要寻多久才能寻到这么个人。况且,是“程力”,还是“程立”呢,长的什么样呢,阮盈袖一概不知。但是人之将死,不答应她未免太狠心。
江御儿看她迟疑,便抬起右手细细看了一阵,那上面有一只和左手上一模一样的素银镯子,然后她气定神闲地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一看到他,就知道他是程厉,因为能让我瞧得上眼的,气度必然不凡呐。若你实在找不到他,就每年我祭日去我坟前看看,他会来看我的。”
阮盈袖忽然笑起来,觉得江四小姐真是笃定而骄傲,随即觉得不妥,忙收敛笑容,接过她一直递过来的镯子,郑重收到袖里:“你放心,如是见到了,我一定给他的。”
江御儿也笑笑,握了握阮盈袖的手,轻轻说:“别让我哥哥和我爷爷知道。”阮盈袖愣愣点点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呆住,或许是为了江御儿的笑,或许只是莫名的遗憾。
“你说程厉会死吗?”江御儿忽然没头没脑抛出来这么一句。
阮盈袖讶然一会儿,已经感觉到她神思不大分明了,恻隐地安慰道:“四小姐看上的人必然是有本事的,怎么会轻易死去。”
江御儿目光朦朦胧胧:“那是自然,他不会死。”
阮盈袖握住她的手说:“你好好休养,一定还会再见到他的。”
江御儿默然了好一会儿,往窗外看了一看,声音渐渐低沉下去,她说:“程厉,我想见你。”
北风把鹅毛大的雪花卷到半空中又抛下,阮盈袖仿佛这十几年间第一回看到丰城下了这样大的雪。她觉得有点彻骨的寒冷,半晌才知道是因为手里握着的那双纤长的素手已经彻底冰凉。其实江御儿同她不过第一次见面,而她做惯郎中早已看淡生离死别,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死亡让她如此难受。
也许是因为她第一次懂得惋惜,那个叫做程厉的,终究还是没有来。
阮盈袖从江府回来的当天晚上,迎来了个特殊的病人。他面如斧削,满脸风霜之色,奄奄一息已是昏迷的模样,好似全身上下都是伤口。旁边有个持剑的男子长身玉立,面色温和,把他稳稳地扶着,这长身玉立的男子道,阮姑娘,我等你良久了。
给病人把脉的时候,阮盈袖讶然了一会儿。病人体内有一股浑厚的内力支撑,显见的是有人不顾自己在为他续命,她抬头看了看另外一个男子,对他道:“尚能救活,但他喉咙这里被利物划破,虽然不深,但以后是否还能再说话,就难说的很了。”
男子想了一会儿,放下两锭银子,道:“烦请姑娘替我照顾他一阵。等他醒来,告诉他来雾云山庄找瞿映月。”
阮盈袖推回其中一锭银子:“那么也用不着这许多,先生不必忧心,待他好起来,我就说给他听。”
男子微微一笑,又将银子放回在阮盈袖面前:“我多给你钱是有理由的,这人惹了丰城的权贵,不能外出,你收留他也要费一番心思,姑娘不必推辞了。”
其实医治这样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阮盈袖不乐意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然而男子趁着她愣神的片刻,竟然已经飘然而去。
阮盈袖真是老实的不情愿,但还是花了功夫来治他。那段时间丰城仿佛真有什么变故似的,官府查处行人的力度明显着紧了很多,但也不说是为了谁。
那日病的半死不活的人在阮盈袖半是嫌弃半是精心的照料下慢慢好起来了,只是喉咙上的伤十分不好,仍旧说不出来话,阮盈袖也问了他叫什么名字,那人凝神片刻,在纸上写下风骨凛冽的两个字:陈豫。
阮盈袖医馆不大,好处是名声在外。找她的要么是贫苦至极连买药的铜板都拿不出的,要么就是得了极重的病的,等闲人有个小灾小难一般不来光顾。这么一来,阮盈袖反倒比一众同行轻松,所以连伙计也没雇,如今陈豫住在她的铺子里真是恰合时宜。
陈豫不能说话,平时也没太多写下来的话语,多数时候只拿着一把扇子在院子里发呆。阮盈袖在他病重的时候打开了那扇子看,暗黄色的扇面上什么也没有,一点也不好看。阮盈袖觉得医人也当医心,便时不时地找来有趣的物什给他看,陈豫略略一笑也就过了,没半点留恋。
事情转变在陈豫来药铺一个半月后。那时他的外伤已经好全了,只拿温和的补药慢慢调理内息。午后阮盈袖拿着一根新麻绳去换水井上被磨砺许久的绳,看陈豫还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发呆,一时觉得有趣,把手里的麻绳当做长鞭甩了出去,直取陈豫背心,当然这力道她拿捏的恰到好处,总不至将他又弄出来什么伤。陈豫闻声回身,中指微弹,阮盈袖只觉一道内力传来,虎口一震,麻绳便飞上了天,“啪嗒”又掉下来,激起了薄薄的土灰。
阮盈袖呆了半刻,才跳脚道:“你干什么你!”她觉得委屈极了,不过开个玩笑,倒值得他动起了真功夫。陈豫眼神忽闪,莫名添了几分温情,他笑了笑,蹲下去,拿着小木棍在地上划着字:“对不住,我帮你换井绳。”
阮盈袖扬着头告诉他自己还气着,并老实不客气的吩咐:“那全交给你了,记得换完了把院子地也给扫了,还把角落那一摞药材磨了,”然后眼睛一瞪,努力做出凶巴巴的样子, “晚饭前不做完了,就别吃饭。”
陈豫浅笑,地面上留下一个干净利落的字:“好。”
从那时起,陈豫就不只是天天在院子里发呆了,他开始帮着做些事情,有时还带着遮面的斗笠陪阮盈袖上山采药。阮盈袖觉得很满意。而又过了段时日,他也终于大好了。
阮盈袖忽然就不太想将瞿映月的事情说与他听,此去雾城路远,如果陈豫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这铺子又只得她一个人了。阮盈袖于是便想着,再拖一拖吧,反正不是还说不出来话么。
而另一件让阮盈袖烦心的事是,当初江御儿交给她的任务,到现在一点儿头绪也没有。她倒是很清楚地知道江御儿被葬在了城东的一个断崖上,因为消息是从江家放出来的,全丰城的人都知道,仿佛把她葬在那里,堪堪是一个饵,等着那个叫程厉的鱼。
阮盈袖回回出去都小心打听着,却一点消息也没有,连着半年,也觉得倦了,以为程厉这男子远没有江御儿想的那样深情,早就离了丰城。她想起江御儿死前的神采,很是怅然。
那时陈豫已经能主动和她说上几句话了,他便写了字条问何事。阮盈袖双手捧着脸颊出神,闷了一会儿说:“你不认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