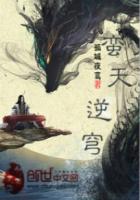骷髅公墓的守墓人马波尔信誓旦旦的说,周五那个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下起的雨里,掺杂着血化作的雨滴。
他办事不牢靠,爱喝酒,到深更半夜的时候,正是他酩酊大醉的好时光。因此他从碎嘴里说的话,谁都不信。
世道乱,什么古怪的谣言都听得到,妖魔鬼怪在人间出没,四处作恶,好像每个人家都曾经被此困扰:有人家里闹鬼,有人家里上吊,有人家里失火,有人家里从此悄无声息。
可第二天早上醒来,街坊领居开门一看,大伙儿不都还活的好好的吗?也没见着谁少了指头,缺了眼球,掉落了牙齿。
但如果读者有雅兴的话,大可以漫步出游,出了波特尔小镇,沿着通往骷髅公墓的道路慢慢行走,大约一公里远的地方,读者自然会发现一只残缺不全的新鲜尸体。
尸体被动物啃食过,手上缺了四根手指,两颗眼球被生生挖出,嘴角被扯去一大块肌肉,露出两排残缺不全的牙齿,肚腹上开了个大洞,可以看见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内脏。
鲜血已经流尽,但尸体并没有腐化,这人死了还不到一个晚上。
镇上的人们会认出来这是镇上臭名昭著的无赖、地痞流氓中最令人生厌的恶棍,那个被人们唤作迪克的大块头。
他一定是在酒吧与人喝酒,一直喝到酒馆打烊。他被酒精冲昏了头脑,与狐朋狗友们打了个比试胆量的赌约,于是在漆黑的夜晚,冒着倾盆的大雨,摸索着往骷髅公墓的走去。
走到半路的时候,这个蠢货竟然在大路旁边睡了起来。
于是,他被在野外出没的野兽盯上,在睡梦中成了那野兽的美餐。
人们唏嘘了好一会儿,心里却都有些幸灾乐祸,倒不全因为这人在镇上不受欢迎,更主要的原因却不能宣之于口
倒霉的是旁人,而不是自己。
这就是人类在灵魂深处隐藏着的阴暗,平时隐而不露,可一遇到事故激发,这些龌龊丑恶的念头就会在心里蠢蠢欲动,如果我们有梦神俄尼里伊般的神力,可以窥见人的梦境,我们也许可以对此初见端倪。
谁都没有留意,这尸体周围散落的鲜血,似乎有些太少了。
傍晚时分,波特尔小镇上的瘦美人酒馆里,传来了鲁特琴凄美的旋律,伴随着吟游诗人信口胡编的歌曲,他唱到:
”她飘飘荡荡,摇摇晃晃,来到舞会之中。
手里捧着罂粟花的花束,高高抬着她的头颅,仿佛她是个活人一样。
我从没见过如此纤细的美人儿。
她穿着华服,脖子上围着血色丝绸,披着酒红色的披风,穿着黑色的天鹅绒礼服。
她的眼神深邃幽远,注视着眼前正在翩翩起舞的人群。
她嘴角带着笑容,嘴唇是如此的鲜红。
只是她这妆容却似乎有些瑕疵,因为有一条红色的水滴,正从她嘴角滑落,
就好像迷途的羔羊一样,离开了羊群温暖有力的庇佑,正朝着凶险残酷的世界走去。
蜡烛在风中飘摇明灭,似乎就要熄灭,她的眼中隐隐现出红光,就好像盯着猎物的食肉野兽一般雀跃而沉着,
风伯作恶,带来一阵狂风,终于将舞会中的蜡烛全都吹灭。
人们惊慌起来,尖叫起来,却趁机大胆作恶,袒露身躯,肉体交融,享受片刻的鱼水之欢。
他们在潘神的催眠下,即将陷入狂欢的癫疯之中。
谁都没留神:那位不速之客,不请自来的骷髅女士,也在享受着另一番景象的狂欢。
她正在吸着血呢!
黑暗许久没有过去,而舞会上的活人在一个个消失。
他们在享受极乐的同时,也在迈向生命的归宿。
这难道不是上苍的恩赐,诸神的慈悲么?
别了,我尊贵的、完美的、令人垂涎的骷髅女士。
别了,我那卑微而下贱的兄弟与同类们。“
请允许我们向读者细细描绘一番这位吟游诗人的样貌吧,因为如果诸位读者尚未留意,这位吟游诗人,恐怕就是今后将要陪伴我们,直至故事结尾的主人公。
他还是个孩子,大概只有十四、五岁的年纪,戴着一顶蓝色的三角帽,帽子遮住了他乱糟糟的金色头发。他眼神坦荡而清澈,容貌俊朗,肤色白皙,时不时露出调皮的笑容。尽管他还是个幼小的孩子,可却由于长期浪迹街头,因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符的沧桑和成熟。
他穿着一身棉绒的绿色长袍,长袍外又罩着一层灰绿色的半袖衫,腰上系着一根黑色的皮带,皮带上挂着几个兜套,上面拴着瓶瓶罐罐,全都是装着药水的小瓶子。
他围着当时诗人常见的短裙,细麻布制成的长裤,牛皮制成的皮靴,皮靴底部满是泥浆,看样子他也曾在昨晚大雨的时候出外晃荡,说不定还出城外兜了一圈。
他这身打扮有些讲究,却也有些不伦不类。但我们如果考虑到他赖以为生的职业,恐怕就会理解他穿着这身服饰的苦心了他需要得体的外表,以此吸引顾客赏脸,给他打赏金币时会加倍勤快。如果遇上某位风流的富家小姐,说不定还能够得到青睐,被她们邀请入闺房之中,窥见一些令人脸红心跳的秘密,发生一段让人羡煞的艳遇。
但必须指出的是,他既然以卖唱为生,又必须在这儿朝不保夕的世道上生存,自然不能在服饰上大手大脚,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正如街上百姓常说的那样:”樵夫的儿子,就要穿成樵夫的模样。“
我们目前还无从得知这位少年诗人的身世,但他既然身为吟游诗人,那这身中规中矩的衣着,对他而言,自然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他唱完了歌,静静等了一段时间,期待着酒馆的顾客老爷们拍手叫好,赏些钱币,以便让他有继续歌唱的动力。我们知道:鸟兽为食而相残,人却趋利而避祸。这位少年在此谋生,若是得不到旁人赏识,虽不至于灰溜溜的跑出酒馆,可心里还是有些落寞的。
平心而论,他的嗓子不错,琴也拨弄的传神,可由于歌词不太吉利,晦涩难懂,在这市井小民出没的酒馆里,可想而知,自然找不到知音。他等了好久,东瞧瞧西望望,压根儿就没人理睬他。
他自嘲的笑了笑,却也毫不气馁,于是轻轻拨弄琴弦,曲调一变,唱起一首欢闹的淫词小调来。此时酒馆里可一下子热闹起来,各个酒鬼听了歌词蠢蠢欲动,眼睛放光,脑袋发昏,下身充血,趁着女侍者走过身旁的时候,借机动手动脚,女侍者尖叫起来,羞红了脸往一旁跑开。
酒馆的两位保镖可不干了,两人并肩走上前去,架住那些举止荒唐的主顾,运足力气就要把他们撵到大街上。酒鬼们见保镖们霸道,嘴里不干不净,手里也推推搡搡,这几下过招,立即就引发了一场群殴。
只听乒乒乓乓的声音四处作响,酒桌被掀翻在地,酒杯饭碗到处摔落,周围一片狼藉。其余酒馆的客人们非但不落荒而逃,反而在一旁雀跃鼓掌,大声叫好。老板在木头酒柜后面骂骂咧咧,火冒三丈,可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两位保镖毕竟是吃这行饭的,过不多时,他们终于制住局面,把那些寻隙滋事的混球揍得鼻青脸肿。两人把一位臃肿肥胖的酒鬼勉力举起,使劲儿往酒馆外抛去。
可碰巧就在这时候,酒馆的门被推开,一位穿着黑色皮衣的黑发女人走了进来。她一抬头,就看见一个浑身冒着酒气的大肉球往她身上摔来,眼看那肉球的臀部就要砸在她的脸上,她眉头一皱,轻轻一让,在那肉球被上一推,那肉球就以加倍猛烈的力道直飞出去,一下子飞跃了街道,直接落在了街对面的垃圾堆中。
酒馆中的人高声欢呼起来,纷纷叫道:”米波,祝你长命百岁。“米波自然就是那惨遭不幸的肥胖酒鬼的尊姓大名了。
少年诗人听着人们欢呼,手指在鲁特琴上伺机弹奏,很快就编出像模像样的旋律来,于是酒客们也拿起酒杯在桌上伴奏,这酒馆里顿时就形成了一首大合唱,人们愈发兴奋,越唱越是欢畅,有些人酒迷心窍,从身上掏出几枚银币,摔在少年诗人的脚边上,诗人露出迷人的笑容,像那人点头致谢。
那位女子挑了一处僻静冷落的角落坐下,只要了一杯啤酒,就一声不吭的坐在那儿想起心事来。她本来不想引人注意,可想不到刚一进门,立即就成了众人瞩目的目标,于是有几位闲的发慌的酒鬼就对她打量起来。
正如之前所说,她穿着黑色的皮甲,脖子上围着红色的围巾,黑色长发从脸颊旁披落下来,酒馆的煤油灯光照射在她的发丝上,竟然反射回来,在她发丝上留下一条条光彩,就好像她的长发有如绸缎一样顺滑。
她的眼睛很大,眸子乌黑发亮,就像是黑曜石一样闪烁,嘴唇鲜红,似乎抹了唇膏,最让人难忘的是她苍白的肤色,就好像雪一样晶莹纯洁,上面没有一丁点儿血色,在她浑身黑色的衬托下,显得愈发刺眼,愈发突兀。
她年纪在十七岁左右,这是一个含苞待放,令人垂涎的年龄,又是一个罕见的美女,举止沉着,性子孤僻,在这危险的黑夜之中,在这危险的街道之上,来到了这一群危险的男人之中。
就好像是在草原上迷途的羔羊,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终于来到了另一个群落之中,以为她终于来到了安全的地方。
可她不知道,这群落的成员,全都是饥饿的恶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