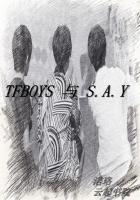“你们都恨我,有恨我霸占了太后宠信的,有恨我杀人作恶的,这有什么?太后允的啊,我就是要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搞得他们焦头烂额,我就是报复他们、报复天下又怎样?”国师笑着摊摊手,有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你们想杀我么,抱歉,太后舍不得我死,这老妇人还指望我给她炼长生不老药,她怎么舍得放弃年轻?”
“别再妖言惑众了,”章庭湮鄙夷地瞧着,“太后容貌与你的药无关,你只是找到了好的时机进了馋言。那段时期太后新丧夫,太多痛苦压力在身,终日无法安寝,所以她气色欠佳。而你的到来,只是恰好赶在她要重新振作的时候,她受了你种种心理暗示,渐渐走出悲境。女人嘛,心情好,容貌自然焕发新生,何况宫中常年备用珍珠粉,各种益容食材,有专门太医调理,她本身就是个美人底子,与你这个国师何相干?你只不过嘴上功夫,她对你产生了心理依赖,仅此而已。”
国师听得心情愉悦,越发觉得等会弄死她有点可惜。
“别打着为太后炼药的名义了,你炼药,是为你自己吧?”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国师矫情地凉凉叹着。
“如果你不捉我,或许我还想不通,如今看来,你炼药与偷取银莲,做的是同一桩事——”她慢慢站起,尽管个子矮了国师不止一头,气场上却不遑多让,“你身中剧毒,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所以偷侯府银莲,所以你相信邪术,以为用三百三十三名少女心头血可以炼出宝药,救你的命!”
国师嘴角僵硬地勾起。
“这事太大,你怕瞒不住,索性欺骗太后,利用太后怕老怕死的心思,以她的名义做着人人皆知的恶事!朝臣因为忌惮太后,不敢将这层窗户纸捅破,所以案发至今,季长安仍然举步维艰,你依然逍遥法外。”
她恨意入骨,拳头握如钢钳。
国师皮笑肉不笑,悠悠然听着她控诉,话毕,他还相当大方地附起掌来:“是啊,说得对,可我现在已经不需要银莲,也不需要心头血。”他眯起眼来,只留细长一条,危险地近看章庭湮:“我有你就够了。”
章庭湮桀骜迎视,目光半分不曾退避,“丁嬷嬷借我手给皇上下毒,事后我却活得好端端,我身上的异处又怎能瞒过你呢?这正是你冒险救我出内狱的,最终原因吧?”
“把你弄出内狱,一防止你信口开河,陷我和丁嬷嬷于险境,二防你说服太后,让你去救皇上,自然最主要的目的,是你身上的那东西了。”国师满脸享受,长吸一口章庭湮身边的空气,如痴如醉:“这东西世所罕见,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章庭湮面色一凝,嘴角微笑定格。
缓缓说道:“我从小父母双亡,在养父家中长大,养父世代从商,家中略有薄财,或亲或养子女十人,唯我一个女儿,为救我的命,别说这东西,倾家荡产他也舍得。”
“冰魄。”国师慢慢说道:“又岂是金钱能买得?多少帝王豪族,想求都求不到呢。”
“机缘凑巧,你想的太多了。”
国师所说的冰魄,就是她两年前遭受暗害,身中奇毒,养父为救她性命,与九大高手合力引入她体内的那气形物体。章庭湮只知那东西不俗,但一直不敢肯定那是冰魄,冰魄太稀世,只有和天裕国东邻接壤的卫国境内才能寻得。
“冰魄使你的身子趋于阴性,所以你需要阳刚之气才能调和,使身体阴阳平衡,”国师邪恶地眯眼笑着,“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养父究竟有什么能耐,能得到天山天池中,那千年才得一见的冰魄?”
“我没必要向你解释,”章庭湮重新坐回椅上,唇角微启,“你国师神通广大,手可伸进内狱,难道还查不出我养父背景么?”
她四下里望望,这炼丹房内镶金嵌玉,极尽奢侈,唯有东南处有一道门,门极阔,占大半面墙壁,一眼望出去,门外是一面雕刻祥云的影壁,没见府卫。
以她现在的身体状况,的确不需要看守防范,章庭湮苦笑,凄凉一叹:“季长安,我全指着你救命,但愿你看到我丢给你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国师眼光一紧,丑陋的脸压了上来。
“我原本从不离身的红绳。”
“什么?”国师铁青脸,眼中杀气汹汹,“告诉你,你弟弟在我手上。”
“真的?”她故作惊讶,“我可自身难保,你还想用他来威胁我?”
国师笑了:“你还需要威胁么?”
章庭湮怕得小脸一怔,往椅背上紧紧靠去:“别这么瞧不起人啊,季长安一定能查到我在国师府的事,然后,太后必然会追究于你……”
“就算查到又怎样,你洗不清的,你忘了你是被买尸的么?以太后对我的宠信,就算季长安救了你,你们也翻不了盘,再说……”他靠得愈近,话中有咬牙切齿的力度:“我现在,就让、你、去、死。”
“死”字才落音,国师忽然揪起章庭湮前襟,身子朝后一撤,向后疾退的力量,带动着她四肢展如张翼的蝶,她无可奈何,任由他的气劲将她全身笼罩,她身在他内力布控的气团中,像被钉上空中十字架,身不由己地被固定,被摆布。
劲风扯去她的发带,及背长发随风狂舞,如堕入九天的仙魔,隐约中,她嘴角上扬,狂放,恣肆。
国师双手成爪,内力化成一道盘旋在她胸口的旋风,欲通过他强劲的内力,硬生生取出她体内冰魄,占为己有。
章庭湮只觉得心口奇痛,仿佛她的所有五脏六腑都要破体而出,所有奇经八脉都要一点点离她而去,这样近乎变态的痛,她之前只有过两次。
一次是两年前她性命堪忧,养父为她引入冰魄那时。
一次,是季长安为策万全,封锁她经脉那时……
“不要杀我!不要……”
在季长安走进莺儿牢房时,受惊过度的莺儿无助地哭喊着,缩在了墙角中,她手上全是血污,僵硬地绻屈着,季长安一见,就知道她曾受过怎样非人的待遇。
“你向审讯的人说了什么?”季长安慢慢走去,口气和缓,“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季大人!”莺儿的双眼迅即恢复了些些神采,仓惶爬来:“季大人救救奴婢,奴婢没有害皇上,奴婢也没冤枉任何人,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章姑娘被人杀了,奴婢不想死……”
“别怕。”季长安蹲在她身前,轻声说道:“她可能还没死,你冷静一下回想看看,在她被人带出牢房之前,她是否留下了什么?”
“她……她……”莺儿脑中有无数个画面相交浮过,想起在那两名狱卒进入牢房后,章庭湮把她推开时,好像在用口型说话。
那她一定知道情况不妙,也许她会就此死在狱中,所以在最后一刻,她还在试图留下什么。
莺儿细细回想,忽然目光一动:“她跟奴婢说,丁嬷嬷,月季花。她在被狱卒抓走之前,是这么说的,我们曾经聊过丁嬷嬷,和她身上的月季花香。”
在生死的最后关头,章庭湮担心她含冤而死,所交代的必然是她所有信息的凝练,丁嬷嬷和月季花,代表了什么意思?
季长安深思片刻,直觉这里头有大文章,忙问道:“你说你和她聊过丁嬷嬷与月季花,具体什么内容还记得么?”
“记得,那晚奴婢接姑娘从天寿宫回来,路上说到丁嬷嬷身上的月季花香,还调侃她是不是太后赐了她对食,所以丁嬷嬷突然爱打扮了。”
“突然?”
“是,奴婢以前与丁嬷嬷也见过好些次,只有上一回进元星宫,教姑娘礼仪,才闻见她身上有月季花的味道。”
“奇怪了,”季长安自疑,“天寿宫人马进驻元星宫后,我也与丁嬷嬷照面过几回,并未闻见这香气。章庭湮留给你这六个字,要表达什么?”
对于章庭湮,季长安是绝对相信的,她进宫之前孑然一身,除了那根一直戴在手上的红绳,一应物什都由宫中准备,携药进宫的可能性为零,若说宫中有内应什么的,那更是子虚乌有。
而在指证她的证物,却从她的衣服袖袋中被搜到,那件证物,正是岑湛受腰伤那晚她穿上身的水蓝长裙,因为她被太后召见,又遇岑湛受伤,她一晚未曾休息,不曾换衣。既是说,在她脱下那件衣裳,到发现她衣服中藏有紫夜蝶毒药,中间所相隔的,正是岑湛毒发、天寿宫控制元星宫。
不难推断出,是天寿宫栽了她这个脏,栽脏者,即是弑君者,天寿宫有人要害上,再联系到章庭湮留给莺儿的话,联系到哪些人有机会接近皇上,凶手是谁,就显而易见了。
可是,即使十有八九能确定凶手是丁嬷嬷,但这一切的推断,基本他对章庭湮的信任,可惜在太后那里,章庭湮连同他季家,都在涉嫌之列,无法说服太后质疑她心腹丁嬷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