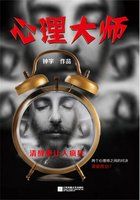没有了头人,没有了青壮男子的部族只有被别的部族吞并这一条路可走。
青狼部的男人都死了,这消息一传出去,部族就招来了好几波趁火打劫的部族。老人没有用,被扔掉,比车轮高的男孩子养不熟,弄死。年轻的女人,年幼的孩子和剩下来的全部家当被几个部族分一分都给扛走了。青狼部从此在北戎消失无踪。
那只盛着头人头颅的匣子被人随手扔在草地里,匣子被羊踢散,头颅被牛马踹得不成个样子,最后还是有个小部族的头人将他捡起来,把上头的草根灰泥随意掸了掸,拿个布袋子裹了,让人送去了王帐。
天气越来越冷,靠北的草原已经下了几场大雪,草被雪盖住了,可供食用的牧草越来越少,北戎大汗的生命也一点点走到尽头。
也速失里这两年过得十分艰难。自从青州一役失败,他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们彼此争斗,互下套子,若不是他为人机警,又有西狄的支持,只怕很早就被淘汰出局。
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几个叔叔和几个年纪尚幼的异母弟弟的支持,与诸兄弟中实力最强的三王子,七王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随着老汗王病势沉重,几度陷入昏迷,王位的争夺终于到达了白热化的地步。
也速失里从来不怀疑,他是天生的王者。汗王这么多儿子里,只有他有远大的目标,并有能将目标实现的实力。南边有丰硕的果实和肥~美的肉,只要他能腾出手,将北戎各部统一起来,他们就是一群战无不胜的狼。就算面对强大的狮子或老虎,狼群也能轻松地战胜对方。
而他,是命中注定这支强大狼群的狼王。
青狼部的消息传到王帐之时,也速失里刚刚干掉与他争抢最凶的三王兄。
空气中还带着淡淡的血腥气,昏迷不醒的老汗王早已不能处理部族中的事务,打开那只破旧的布袋,捧出那颗被踢得千疮百孔的头颅的,自然就是也速失里。
艰难辨认出这是与他关系很亲密的堂兄的脑袋,也速失里大叫一声,抽~出弯刀将身边栓马的木桩砍成两半。
这是南人赤~裸裸的挑衅!狡猾的狐狸,终于亮出了它们的爪子。
他却忘了,带人深入别人的家里,砍了别人的家人,抢了别人的粮食的,正是他这位死到临头求内附的堂兄。
只是现在局势未定,他要是带兵去打云州,前脚刚走,后脚就能被人掀了老窝。
也速失里,他忍了下来。时机不对,人手不足,眼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
严阵以待北戎反扑的云州依旧风高云淡,安宁和平。宇文泰失望,窦庸却暗暗松了一口气。
昭王的愿意很美好,但两国交兵岂是一个美好愿望就能达成目标的?这是一项系统的大工程,从人到物,区区一两载,哪能准备充分呢?
对他们来说,眼下最缺的不是别的,而是敌人的消息。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北戎是一片广阔的草原,北戎人游牧,逐水草而居,他们分了许多部族,彼此有争斗,却又彼此相互支撑。他们以部族为一个整体,外人想打进去千难万难,一个消息光传出来就要花费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更别说要怎么分辨真伪。
以前不打仗,北戎人怎么过日子他们都不管。可现在两边都在卯着劲儿,未来的几年内一定会有仗要打,要怎么打,从哪里打,打到哪里去,这都需要对敌人的了解。
照顾昀和宇文泰的想法,他们要直~捣黄龙,直接杀到王帐,才能将北戎彻底打痛、打残、打到不敢再起祸心。可是王帐究竟在哪里?云州城里没一个人能知道。
叶榛说:“如今秋粮已入库,眼瞅着寒冬已至,往年正是北戎人出来打草谷的时候,可现在,除了青狼部越境被明殊全歼,其他地方竟听不到北戎来犯的消息。只怕北戎汗位之争已到关键时候。”汗王离死不远了,这个时候,有力竞争的人都围在王帐附近,谁也不会当那只出头鸟,然后老巢就被别的鸟占了的傻~子。
“还是要找到北戎王帐,探知北戎现在的局势,我们才能有所行动。”叶榛在舆图上点了点。
宽宽的羊皮卷上,只简单有几处水流,连北戎部族的聚居点图上都没办法标出来。
“榷所已关,北戎不产盐糖茶铁,现在行商又被严控,今年冬天他们会很难熬。”顾昀说,“旁人进草原肯定不行,这些人天性排外又残忍,不到他们部族周边就先被弄死了。只有……假扮私商。”
“扮私商,贩盐铁给敌人吗?”李栩十分不赞同,“资敌以盐铁,不妥。”
“打听完消息,再把盐铁拿回来不就行了?”宇文泰敲敲桌子,“拿回来之后正好往下一处去,还省了往返补货的时间。我看挺好。”
这货更凶残。
“汗王王帐可不好打听。”叶榛又道,“咱们只知道北戎王帐设于金水河边,但金水河长百余里,王帐又不是固定不动的,今年在这儿,明年可能在那儿,若没有准确的消息,不可贸然进军草原。”
“这是自然。”在座所有将官都表示了赞同。
“需择反应机敏的斥侯装扮成商队,深入草原打探消息。”
“鞑子悍勇,全民皆兵,需要格外小心,不能叫人起疑看出破绽。”
商量来商量去,骑云校尉李栩十分荣幸再次中选。众人行动迅速,准备车队货物,铁器是不敢带的,车上只备粗制盐和茶饼,又备了不少布匹、靶镜、针头线脑这些不值什么钱,在北戎却十分受欢迎的小玩意。
这厢正准备着,云州府里来了几位不速之客。
顾昀听着信,惊得面罩都忘了带,直接骑马从卫所冲到怀远城里来。
“阿弥陀佛,经年不见,顾施主一向安好。”听着人声,正在与窦庸说话的那人转过身,面带微笑对顾昀双手合什行了一礼。
“不归兄!”顾昀一脸的惊喜,上前与他紧紧抱了抱!
来人正是南华宗的不归大师。算起来已有两年多未见,顾昀乍一见到故人,自是既惊且喜。
“你怎会到云州来?”
不归微微笑着,眼角浮现几条细细的纹路:“江南住了两年,便想往江北走一走,走得远了,听说你在云州,便往这儿来,看看你再瞧瞧我那几个师侄。”
数年不见,不归大师形容依旧,身上穿着七成新灰扑扑的僧衣,还是没落发,戴了一顶僧帽,塞不进去的头发露出小半,黑白相杂着。一眼望去,像是个二十出头的俊秀僧人,再细一眼,又像年近四十的沧桑和尚。一身气度从容,虽不是极佳的容貌,绝对让人见过不忘。
顾昀与不归是忘年交,早年他在南华宗求学时,便得不归许多指点,又隐隐知他与定北军有深厚渊源,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虽然昭王自小被送与道士养着,但他妈叶皇后其实是信佛的,南华宗为佛教执牛耳者,宗门中有这么一位惊才绝艳却又始终没剃度的弟子,宇文泰行走江湖时便时有耳闻。又兼不归来云州是为见顾昀,宇文泰自然更要好好招待。
当下排了桌素席,请不归大师吃饭。
宇文泰是不知道的,不归不止是南华宗排得号的有名人物,与江左七星阁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顾昀要打探草原上的情报,正是没人指点的时候,见着不归,自然要请这位大师指点一二。
借着出来更衣,宇文泰抓着顾昀抱怨:“你怎么什么都说?咱们派人去北戎也是机密事。万一被漏嘴说出去了怎么成。”
顾昀摇摇头:“你不了解他。他是万万不会说出去的。北上草原,咱们一点经验也没有,去了以后如何与北戎人交谈,如何解除疑心,如何与之交好,探听消息,又如何从他们言行的蛛丝马迹中寻到咱们所要的东西,这都是学问。”
宇文泰翻了个白眼儿:“他一个和尚……虽说也是个名声在外的和尚,通晓的也只是佛法经义,这些事他怎么能知道?”
顾昀眉梢一挑,对他露出个高深莫测的表情来。
卧~槽!顾昀这张脸杀伤力真心大,虽然宇文泰对兄弟从没有过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但被他这样近距离地放大招,还是很丢脸的缩了。
等回到席上,不归已经放下箸,表示自己吃完了。
然后不归大师以一张慈悲脸,对顾昀说:“我一路北行,心中颇有感触。这些年,我的修为似乎无法再进一步,或许北方有我的佛缘在。十数年前,我也曾在北方待过一段时间,北戎话虽不精,也能说一二句。若方便,可否许我带弟子数人与将军的商队一同进入草原呢?”
宇文泰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一个和尚,到北戎那蛮夷之地做甚?”
不归垂目合什道:“佛愿度一切可度之人。”
我勒个去,那群野人,只信他们自己的神啊!
“北戎人残暴好斗,性如野兽,大师未必能度了他们。只怕还有危险。”
不归抬起双眸,脑后若别个光圈就能立刻变身菩萨:“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和尚犯起拧来,简直无可救药。
顾昀却是站起身,对着不归长揖:“令不归兄以身犯险,弟心实不安。”
不归微微一笑:“国之难,吾辈之责。”
等等,刚刚不还是菩萨吗?怎么这话听起来跟什么佛法,什么度人,听起来没有半点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