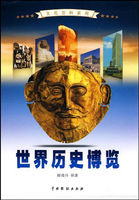中国历史上有学问的皇帝不少,但像康熙这么有学问的皇帝不多。他不仅精通满汉文化,而且难得地对西方科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学习。
在康熙皇帝发愤学习的早期阶段,经筵日讲是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与日讲的主要内容是被尊为经典的几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代替的一些历史著作。其中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基本上都是成书于封建社会前期。由于这些书籍的作者或传授者都是儒家阵营中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阐发的治世思想,对于封建君主施政,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正是因此,封建统治者经过长期的选择,将其确定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宋朝以后,又将之作为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至于有关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著作,则更为封建君主临政治国所必需。因而,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之加以重视并将之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封建君主即曾通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并将之用于实际政治而取得了成功并成为千古称颂的明君,可见,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对于帝王自我教育和世道治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在康熙以前,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清朝统治者即注意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曾先后设立文馆、内三院,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翻译、学习和应用;入关以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相继对之表示重视。从顺治十四年始,顺治皇帝还仿效历代帝王先例,专开经筵,于仲春、仲秋请学问渊博的高级官员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尽管这些活动当时仅仅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对于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加速统一进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康熙时期经筵日讲的全面开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顺治皇帝去世后,中央政权中保守势力的抬头延缓了自皇太极以来清朝统治者学习儒家经典的进程。康熙皇帝即位时,清朝政权已基本上确立了其对全国的统治,兼之以当时康熙皇帝本人年龄尚幼,正宜结合其早期教育及时举行经筵日讲,使其比较系统地学习各种治国经验,以便日后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有见及此,康熙皇帝即位半年之后,工科给事中王曰高首先疏请举行经筵大典,“以光盛德,以端化源”。尔后,康熙二年四月和康熙四年三月,又相继有福建道御史王鼐、太常寺少卿钱等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要求。但是,由于顺治皇帝去世后上三旗四辅政大臣掌权,基于固有的民族偏见,特别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权益,以四辅政大臣为代表的满族勋旧将重用汉官、仿效明制视为对“祖制”的背叛。在此思想指导下,对于这些要求,他们全然不予理睬。这样,几年之中,不但由顺治时期开始的经筵活动被无形地搁置起来,而且,连一个宫中正式教读师傅也没有给康熙皇帝配备。
康熙六年七月,康熙皇帝开始亲政。这时,举行经筵日讲以学习传统治国思想与方法的问题就愈显现实和迫切,不少臣下又为此纷纷上言,要求亟开经筵日讲。如康熙皇帝亲政数日之后,吏科给事中蔺挺达即上疏要求他“敕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慎选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讲读之任,使之朝夕侍从,尽心启发”,于听政之暇,取“四书”、“五经”及《通鉴》等“讲贯脩绎,寒暑无间”。
次年三月,福建道御史李棠奏请“亟开经筵,以光典礼”。五月,贵州道御史田六善亦疏请康熙皇帝于听政之暇,“日取汉唐宋元四代史册亲阅数条,凡一切用人行政,黜陟赏罚,理乱兴衰之故,反复讨论,庶圣德日新,大智日广”。康熙八年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也疏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可以说,举行经筵日讲已经成了臣下的普遍要求。然而,这时康熙皇帝虽在名义上已经亲政,而实际大权却仍操于以鳌拜为代表的原辅政大臣之手。为了达到长期专权的目的,他们把以开发康熙皇帝智力、培养其治国能力为目的的经筵日讲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对之仍然采取了不予理睬的顽固态度。对于在议开经筵日讲活动中态度积极、影响较大者,还枪打出头鸟,予以惩处。如康熙六年六月,康熙皇帝亲政前夕,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康熙皇帝,要求他宜趁青年时期,选择道德学问都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作为自己的老师,“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康熙七年九月,他又再次上疏,指出“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而在今日尤为切要者也”,并要求康熙皇帝将之提到君德成就、天下治乱的高度加以重视。因为他对经筵日讲态度积极而且将其意义也阐释得十分深刻,鳌拜等人极为愠怒。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摘取其奏疏中涉及辅政大臣的只言片语,指为语含讥讽,企图藉此加罪。这样,尽管其时康熙皇帝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但是由于鳌拜等人的无理阻挠,经筵日讲却仍像康熙皇帝亲政以前那样迄未举行。因为治国方向不明确,至康熙八年时,虽除台湾之外,整个中国大陆皆已统一在清朝政权控制之下,但因在中央是鳌拜专权,地方上又是三藩割据,兼之以各级官吏竞相贪污,人民生活极为痛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整个国家仍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康熙八年五月,康熙皇帝经过周密布置,一举剪除了专权擅政达8年之久的鳌拜集团,全部控制了中央政权。为了真正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以取得治国经验刻不容缓。这样,在他亲掌政权之后不久,在集中力量清除鳌拜败政的同时,他即注意到了经筵日讲的问题。康熙九年十月,他下令礼部为经筵日讲做准备工作。几天之后,礼部遵旨议复,经筵日讲均照顺治十四年例,于第二年开始举行。在此同时,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选拔讲官、撰拟讲章等项工作也在紧张的准备之中。康熙十年二月,经康熙皇帝批准,首先任命了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知识的满汉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在他们之下,又从翰林院选出10人充当日讲官员。当年二月,首开经筵;四月,初行日讲。这样,在清除鳌拜集团之后不到两年,康熙皇帝即开始了自己的经筵日讲活动。康熙皇帝5岁读书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即位之初,又面临内而辅政大臣专权,外而兵戈不休、社会混乱的历史局面。这样,儒家经典和一些历史著作中所陈述的尧舜盛世成了这个青年君主所憧憬的目标。为了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中汲取营养,学习传统的治国理论和治国方法,对于经筵日讲,从一开始,康熙皇帝即极为重视。首先是热情主动,持之以恒。长期以来,对于经筵日讲,历代君主多持敷衍态度。对于其中之经筵,因系礼仪活动不得不参加。对于日讲,则因由君主视政事之忙闲自行决定而百般推托。偶尔有个别君主一生之中进行几次日讲,便被史臣诩为盛事。而康熙皇帝却一反历代君主之所为。就经筵而言,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其去世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除因巡幸、出征偶未举行之外,从未停止。就日讲而言,虽然这一活动开始不久便已在数量上超过了历代君主,但是康熙皇帝却仍然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一再要求打破惯例,增加日讲次数。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伏期刚过,因为秋季经筵尚未届期,日讲活动无法开展。为此,康熙皇帝指令讲官:“方今秋爽,正宜讲书,尔等即于本月二十五日进讲。”康熙十二年二月,他又要求讲官改变间日进讲旧例,每日进讲。他说:“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当年五月和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他又先后指示打破寒暑停讲惯例,“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辍讲”。“天气犹未甚寒,仍令进讲。”康熙十四年底,又再次指示讲官不必于次年春季经筵后始行日讲,“着于正月二十日后,即行进讲”。后来随着日讲活动的开展,康熙皇帝的热情愈益高涨,先是巡幸南苑期间,以讲官侍从,日讲于南苑东宫前殿。后来,又发展到万寿节祭祀之前的斋戒日期和因病不能御门听政的空闲时间也不辍讲。在此同时,为了争取日讲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对日讲时间的安排,康熙皇帝也颇费心思。三藩叛乱期间,因为军务紧急,康熙皇帝一般是起床之后不及用膳即御门听政,而后再行日讲,以致日讲之时时近中午,饥肠辘辘,影响学习。
后来三藩平定,台湾统一,紧急政务减少,为了提高日讲效果,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始,康熙皇帝特将日讲安排在御门听政之前。一般情况下,每日上午均为日讲和御门听政时间,偶尔当日没有启奏本章而不行御门听政,也不辍讲。个别时候,因为政务较少,日讲、御门听政之后,时间尚早,还一日两讲。他自己说:“读书以有恒为主,积累滋灌,则义蕴日新。每见人期效于旦夕,常致精神误用,实归无益也。”正是这种热情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使得康熙皇帝虽然在学习上起步较晚,但在学习效果上,却大大超过了历代君主:在15年的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四书”、《尚书》、《易经》、《诗经》、《通鉴纲目》、《通鉴》等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创造了日讲近900次的纪录,经筵日讲成为康熙前期康熙皇帝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方式。在此同时,为了搞好日讲,对于讲官,康熙皇帝也十分尊重。日讲之初,由于康熙皇帝知识未开,讲官进讲一度是康熙皇帝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关键环节。为此,日讲之前,讲官须预选内容,撰写讲章,缮成正副两本,将正本呈给康熙皇帝。讲官为了照顾康熙皇帝的接受能力,又须对内容详加解释并阐发其中义理,还须设法启发其联系实际政治,从始至终,负担相当沉重。对此,康熙皇帝予以全力合作。日讲时,常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对于讲官本人,也体恤备至,日讲之后,每赐御制书画卷轴以示慰劳,寒暑之节也常常赠给貂裘、表里纱缎、果品之属以联络感情;遇有优缺,从速升转;如有疾病,还遣医诊治并赐药物;去世之后,又遣使吊唁致厚赙,赠予美谥,录用子孙。康熙皇帝的这些行动,使得日讲官员普遍地感激涕零,实心报效,从而使经筵与日讲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其次是认真踏实,重视质量。日讲之初,康熙皇帝的态度极为认真。每次日讲之后,他都坚持课下复习。他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证于人,务期道理明彻乃止。”又说:“自幼读书,凡一字未明,必加寻绎,期无自误。”这些,足可看出他早年日讲课后用力之勤。后来,随着康熙皇帝文化知识的提高,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康熙十四年四月,他向讲官提出:“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只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全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从此之后,约有两年时间,每次讲官讲毕,例由康熙皇帝加以复讲。复讲虽能督促康熙皇帝日讲时专心听讲并考察其记忆和理解程度,但就学习方式而言,尚属被动。因而,从康熙十六年四月开始,每次日讲,均由康熙皇帝先讲,或讲全文或讲其中一节,然后再由讲官进讲。这样,为了准备亲讲,每日日讲之前,康熙皇帝必须预习日讲内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康熙皇帝逐渐培养起自学能力。在此同时,对于讲官日讲中的过分颂扬之词如什么“媲美三王,跻隆二帝”、“道备君师,功兼覆载”等,或者谕令删除,或者谕令改撰“劝戒箴规”之词,并且还一再通令讲官以后所撰讲章中不得再行出现过分溢美之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
再次是目的明确,联系实际。康熙皇帝举行经筵日讲,目的在于汲取治国经验,因而,在日讲活动中,极为注意思想内容。日讲之初,他虽然一度允许讲官注重词句训诂,但同时又要求他们只以明白书理为限,不得漫无边际,多为援引,以使自己如入迷宫,不知所归。他说:“书中义理原自完备,惟在注解明白,加以反复玩味,自然旨趣无穷。若多为援引,反致书理不能豁然矣。”“读古人书,当审其大义之所在,所谓一以贯之也。”康熙十六年以后,他进一步向讲官提出要求,在日讲中以阐释其中义理为主。他对讲官说:“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朕虽不明,虚心倾听,寻绎玩味,甚有启沃之益,虽为学不在多言,务期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然学问无穷,义理必须阐发;卿等嗣后进讲,凡有所见,直陈勿隐,以符朕孜孜向学之意。”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将其思想内容和实际政治相联系。他说:“朕每披阅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以探索源流,考证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整个日讲活动中,他常常将日讲活动和实际政治结合起来学习。在施政时,也有意识地联系以往日讲内容。其中,仅以日讲活动结合实际政治而言,例子便不胜枚举,如康熙十六年五月一次日讲后,他即联系讲章内容发表议论:“孟子所谓一曝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透彻,人君诚不可不知。”康熙十七年九月,在讲官讲授《尚书》时,他又说:“朕观高宗命傅说,谆谆以纳诲辅德为言,可见自古君臣为一心一德至诚孚感。为上者实心听纳以收明达聪之益,为臣者实心献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主德进于光大,化理跻于隆平。后世君臣之间,徒尚虚文,中鲜实意,治不逮古,职此故耳。”康熙十九年四月,又在讲授《尚书·吕刑》时即席发表看法:“律与例不容偏废,律有正条,自应从律;若无正律,非比例何以定罪。总之,用律用例,俱在得人。”总之,在整个日讲活动中,凡与当时政治有关者,康熙皇帝几乎都曾论及。另外,为了使日讲内容和实际政治联系更密切,康熙皇帝还主动要求增加新的讲授内容。如康熙十五年十月,他向讲官提出:“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做何拣择,撰拟讲章进讲,尔等议奏。”考虑到《通鉴》一书部头巨大,讲官提出,朱熹所做《通鉴纲目》一书,内容本乎《通鉴》,且又“提纲分目,尤得要领”,“拟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进讲。讲章体裁,首列纲,次列目,每条之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可采者,亦酌量附入”。从此,学习和实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知识也成了康熙皇帝日讲的重要内容。不久,因为《通鉴纲目》一书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康熙皇帝的要求。根据他的指示,从康熙十九年四月起,讲官又将《周易》和《通鉴》参讲。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从未中止。与此相一致,结合各种历史经验教训如外戚专权、母后临朝、权臣专制、宦寺乱政、藩镇割据、异族入侵、人民起义等日讲内容,康熙皇帝发表了更多的议论。
所有这些,都对康熙皇帝的思想及其施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作为康熙皇帝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经筵日讲对其本人思想及康熙朝政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对其本人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二是为其巩固统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三是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到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努力博习经史以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同时,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康熙皇帝还积极学习和国计民生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些活动,不但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使得康熙皇帝的政治成就大大超出了他的同行先辈,而且使其在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早在亲政之初,康熙皇帝即已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康熙初年,清朝政坛上曾经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历法之争。明朝以来,由于长期袭用十三世纪下半叶郭守敬制定的《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交食不验时有发生,节气推算也常常发生差错。为此,崇祯年间,崇祯皇帝采纳大学士徐光启建议,聘请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主持改进历法并修成《崇祯历书》137卷,但是此历未及推行,明朝即已灭亡。清朝入关以后,顺治二年,摄政王多尔衮遂将此历改名《时宪历》,颁行于世。同时,还将历局与钦天监合并,任用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并谕“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顺治皇帝在位期间,对于汤若望更是宠信有加,尊为玛法(满语爷爷)而不名。利用顺治皇帝的信任,汤若望等积极传教,不长时间,教徒激增,影响迅速扩大,从而引起了正统封建儒生的不满。顺治皇帝去世后,四辅政大臣掌权,对于顺治时期的各项政策多所更动,藉此机会,康熙三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上疏,对汤若望所编新历加以非难和指责。为此,四辅政大臣将汤若望逮捕下狱,改以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吴明隽为监副,废除时宪历,改行新历法。然而,由于杨光先无知不学,历法推算连年出错,甚至还出现了一年两春分、两秋分的笑话,并因此而受到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的批评和攻击。此时康熙皇帝已经亲政,为了弄清是非,康熙七年十二月,康熙皇帝与议政王大臣等差大学士图海等会同监正马祜督同测验立春、雨水、太阳、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隽所称,逐款不合。”康熙皇帝遂下令将杨光先、吴明隽革职,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复用时宪历。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康熙皇帝感到,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也必须通晓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统治全国。后来,他对大臣回忆当时情形时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朕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致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测睹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亲政之后不久,康熙皇帝开始学习自然科学。
数学是天文历算的基础和工具,为了使自己在天文历算上成为内行,康熙皇帝首先刻苦学习数学。中国古代的数学计算一直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但自宋元以后,由于统治者不加重视,科学不但发展十分缓慢,而且不少原已发明的计算方法也湮没失传。与之相反,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各国数学知识迅速发展,后来居上。有鉴于此,康熙皇帝遂以供奉内廷的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安多为师,学习数学。当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经筵日讲,学习传统治国理论的任务已经十分沉重,但是,为了掌握数学知识,三藩之叛前两年多的时间里,康熙皇帝仍然以极大的热情把完成计划内的学业以外的时间完全用于研究数学,以浓厚的兴趣连续两年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这项研究工作。在这两年中,康熙皇帝了解了主要天文仪器、数学仪器的用法,学习到了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中的一些基础知识。后来虽因三藩之叛爆发,迫使康熙皇帝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学习,但是,出于对自然科学知识十分浓厚的兴趣,康熙皇帝“一有空闲时间就练习已经学过的知识”。三藩叛乱平定之后,清朝统治日益巩固,中国社会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因为紧急政务相对减少,康熙皇帝比以前更加热心地学习西洋科学。为了这一目的,除南怀仁、安多之外,他又将西方传教士徐日升、张诚、白晋、苏霖等请入宫中,讲解天文历算以及与之有关的《欧几里德原理》与阿基米德几何学。为了消除语言障碍,康熙皇帝还为他们专门配备满、汉教师,辅导他们学习满汉文字。为了使讲课收到满意的效果,还下令内廷官员将他们进讲内容整理成稿,由传教士在进讲时口授文稿内容。在进讲过程中,康熙皇帝态度认真,不但聚精会神地听讲,不懂就问,而且还于课后认真复习。法国传教士白晋于《康熙皇帝》一书中,曾经记载康熙皇帝认真学习的详细情景:
“康熙皇帝传旨,每天早上由上驷院备马接我们进宫,傍晚送我们返回寓所。还指派两位擅长满语和汉语的内廷官员协助我们准备进讲的文稿,并令书法家把草稿誊写清楚。皇上旨谕我们每天进宫口授文稿内容。皇上认真听讲,反复练习,亲手绘图,对不懂的地方立刻提出问题,就这样整整几小时和我们在一起学习,然后把文稿留在身边,在内室里反复阅读。同时,皇上还经常练习运算和仪器的用法,复习欧几里德的主要定律,并努力记住其推理过程。这样学习了五六个月,康熙皇帝精通了几何学原理,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以至于一看到某个定律的几何图形,就能立即想到这个定律及其证明。有一天皇上说,他打算把这些定律从头至尾阅读12遍以上。我们用满语把这些原理写出来,并在草稿中补充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著作中的必要而有价值的定律和图形。除上述课外,康熙皇帝还掌握了比例规的全部操作法、主要数学仪器的用法和几何学及算术的应用法。
“康熙皇帝令人难以置信地深切注意而且细心地从事这些研究工作。尽管这些原理中包含着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我们在进讲时,也不够注意礼节,但皇上从不感到厌烦。最初,我们解释的某些证明,皇上还不能理解,这可能是由于证明题本身确实难懂,更确切说,也许是由于我们不能灵活地运用适当的词汇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论什么原因,一碰到这类证明题,皇上总是不辞辛苦地时而向这个传教士,时而向那个传教士再三垂问题解。遗憾的是我们往往不能像我们想的那样使皇上把这些问题理解十分透彻。在这种情况下,皇上就要求我们改日再做解释。当时他约束自己专心致志地听我们讲课的情形,是非常令人钦佩的。有一天,皇上在谈到他自己时,曾经涉及这个问题。谈到刻苦学习的问题时,他说对于刻苦学习科学知识,他从不感到苦恼,并颇有感触地追述,他从少年时代起,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学习规定的一切知识。
“康熙皇帝充分领会了几何学原理之后,还希望用满语起草一本包括全部理论的几何学问题集,并以讲解原理时所用的方法,进讲应用几何学。同时,皇上旨谕安多神甫用汉语起草一本算术和几何计算问题集,它该是西洋和中国书籍中内容最丰富的。
“皇上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已感到最大的乐趣。因此,他每天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两三小时。此外,在内室里,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皇上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数学。由于这位皇帝特别厌烦委靡不振的、无所事事的生活,所以即使工作到深夜,次日清晨也一定起得很早。因此,尽管我们经常注意要早进宫谒见圣上,但仍有好几次在我们动身之前,皇上就已传旨令我们进宫。有时只是为了让我们审阅他在前一天晚上所做的算题。因为每当学习到几何学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时,皇上总是怀着浓厚的兴趣,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并练习数学仪器的操作。由此可见,康熙皇帝为了独立解决与我们以往讲过的相类似的问题,曾经做出何等努力,实在令人钦佩之至。”
随着康熙皇帝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日渐深入,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如兵器制造、地图测绘、医学、农学等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为此,他多次表示欢迎懂科学的西方传教士前来中国。在他的授意下,康熙二十一年,南怀仁在致西欧耶稣会教士的一封信中呼吁道:“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重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教士,中国无不欢迎。”在康熙皇帝的招徕下,洪若翰、白晋、张诚、苏霖同时来华,供奉内廷。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又以法国传教士白晋为使,回欧招聘教士。于是,康熙三十八年,又有马若瑟、雷孝思、巴多明等人来华。即使在清朝政府因教规问题和罗马教皇严重对峙期间,康熙皇帝也没有放松争取西方科学人士来华的努力,并先后授意西方传教士沙国安、德里格、马国贤等致书罗马教皇,要他“选极有学问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几人来中国以效力”。在此同时,康熙皇帝则如饥似渴地投身于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试验之中。据白晋、张诚等法国传教士所见,康熙皇帝出巡,经常“利用刚会使用的天文仪器,在朝臣们面前愉快地进行各种测量学和天文学方面的观测。他有时用照准仪测定太阳子午线的高度,用大型子午仪测定时分,并推算所测地的地极高度。他也常测定塔和山的高度或是感兴趣的两个地点的距离”。对于和民生攸关的农学,他也极感兴趣并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亲自培育过御稻米和白粟米两种优良品种。其中御稻米不仅气香味腴,而且生长期短,北方也能种植,南方则可以连收两季。他还做过南北作物移植的试验,北京丰泽园、热河避暑山庄种有南方的修竹、关外的人参,山庄的千林岛遍植东北的樱额(沙果),每到夏天,硕果累累。对于医学,他也极有兴趣,为了学习有关知识并进行研究,他在宫中专门建立化验室,从事医学的研究。对于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他还极力加以推广。如他发现点种牛痘,对于防治天花极为有效,即在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蒙古积极推广。“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但是由于他“坚意为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还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谕令西方传教士巴多明将《人体解剖学》一书以满汉两种文字译出。至于兴修水利、兵器制造、地图测绘等项知识因为和巩固统治关系极为密切,更为他所十分关心,如对治理黄河,他不但于“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而且还乘六次南巡之机,实地视察河工,同时又广咨舆情,经过10多年的努力,终于摸索出了一套治理黄河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从而改变了黄河连年溃决的现状,出现了40年的安然局面。对于地理测量,他的态度也十分积极,每次巡幸或者出征,他都注意携带仪器进行测量,在此基础上,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六年,他又组织一批中西学者在全国进行实测,编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此同时,他也极为重视军事科技的发展,三藩叛乱期间,他曾命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研制改制火炮,并亲至卢沟桥阅视新炮的实弹演习。三藩叛乱平定后,他仍对之表示重视并下令继续铸造,分别配备于全国各战略要地。
由于长期坚持钻研自然科学,在其中一些领域中,他还颇有发现。如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他根据实测结果认定据西洋新历推算本月初一日食时刻略有失误,并怀疑可能是“算者有误,将零数去之太多”。康熙五十年,他又根据实测发现当年夏至是在“午初三刻九分”,而不像西洋历推算的“午初三刻”。总之,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始终不衰,学习自然科学成了康熙皇帝终身爱好的事业。
作为康熙皇帝终生爱好的一项事业,和经筵日讲一样,学习自然科学也对康熙朝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通过学习,康熙皇帝使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成为内行,取得了主动权,从而在各种政策决策以至具体事务处理中都比较容易分清是非,接近实际,避免或少走了不少弯路,即以黄河治理而言,清朝初年“决溢之灾无岁不告”,河患成了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虽然国家每次拨出大量帑金修治,但都收效甚微。所以如此,最高统治者对治河规律盲然无知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为此,三藩叛乱平定之后,康熙皇帝集中精力研究河务,他一方面博考前代文献,另一方面又多次前往视察,其中关键环节并亲自动手测量,与此同时,还屡集廷议,综观全局,从而在治河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其次,康熙皇帝重视自然科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士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帝王大多只重视政治、军事和思想,只研究治人,不研究治物;只研究驾驭人类,不研究征服自然。受此影响,封建士人皆以为儒家经典无所不包,兼以“就易畏难,以功名仕宦为重”,从而形成了一种顽固的“重道轻艺”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康熙皇帝却以帝王之尊对自然科学表示重视,努力学习,积极推广,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士人投入数学、天文学、医学、水利、工艺等自然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他们有的努力发掘中国古代科学遗产,有的刻意创新,不但大大缩小了中西科技之间的差距,同时,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也起了积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