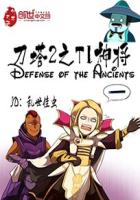悠悠醒转,潇夏曦已经置身在P国的家。
粉色的床幔,粉色的窗帘,日照的光柱穿透玻璃投射在粉色的地毯上,也是粉色的。这是潇万川曾经为她打造的粉色世界,当时她还小,母亲尚在世,他们一家三口坐在地毯上堆砌积木,潇万川把积木一块一块地往上砌叠,待最后一块积木被放置在它应有的位置上时,潇夏曦小心翼翼地在积木群的顶端插上一面旗帜,一座城堡的宏伟模型终于完成。
潇万川大喜,抱起女儿的小身子稍微用力向上抛了抛,潇夏曦嘻嘻地笑不拢嘴,不停地在叫嚷:“爹地,再高点,再高点……”粉红的小脸流光溢彩,在旁的母亲也随着丈夫上抛女儿的节奏轻轻打着拍子,乐也融融。
她侧首,不甚意外地看到了挂在墙上的电子壁画。当年潇万川着人仿照城堡模型制造了一幅长十米高三米的巨型电子壁画。行云流水,绿草如茵,雄伟壮观的城堡居中屹立,每一砖每一窗都精造得非常细致,风一吹,城堡上的旗帜飒飒飘扬。壁画这一挂,便是十二年。
他说:以后建一座全世界最大最漂亮的黄金城堡送给他最最亲爱的小宝贝。
他说:他们一家三口永远都在一起,不相分离。
他说:母亲的泪是他心头上的血肉,他不会让它轻易地掉下来。
言犹在耳,一切却恍如云烟。他要将他最爱的女儿嫁给联合酋长国的酋长以换取石油开发上的得益。他把一个女人带返了他们的三口之家,女人挺着个大肚子,从此,他们的家多了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最后撒手人寰,而她也被逼离家出走。
他的权威推卸了所有承诺。潇夏曦嗤笑,记忆深处的映象仿佛成了这粉红世界里最大的讽刺,丝毫经受不住时间的沉淀,泡沫般瞬间爆破,再无影迹。
她赤足下床,踩在柔软的地毯上,慢慢踱步走向窗门边上的背影,仅五步之遥就嘎然止步。
窗外倾泻的柔光披洒在他的身上,疑幻似真。有多久了,她不再如此耐性地注视过他。自从母亲过世后,他们每次见面除了淡漠的问候外,就只剩下相对无言的擦身而过。即使她身处国外,在电话里通联也是匆匆数语便挂上了。她久久地驻立在话机旁,多想他能不厌其烦地再打多一次,只需要一次,她就能感动得泪流满面,摒弃由母亲去世引致对他的怨恨立即回到他的身边。可是,他连多打一次的时间也如此吝啬。
“爹地——”从上一次通联到现在,仅相隔了不到半年时间,可是这一句称呼在潇夏曦唇齿间溢出后,才惊然发觉已经变得那么生硬。
男人转身,柔光打在他的脸上,更加突显五官轮廓的干净俐落,眼眸漆黑深不见底,鼻子英挺,唇片厚薄适中,既有西方人的俊朗,又有东方人的柔美,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中西合璧型。潇万川已经年逾五十,浑身却依然洋溢着年轻时的冲劲,身躯挺拔笔直,凛然生威。
他径直走到潇夏曦面前。
她不自觉地后退半步,潇万川身上的怒气铺天盖地地汹涌而至,很陌生,很昂然,又深邃莫明,让人不可忽视。
“啪——”猝不及防地,她的脸上已经多了五条深刻的指痕,那声响,像碎了一地的玻璃,片瓦不全。她木然地呆立当地,发抖得像一片快要枯萎的秋叶,只要风一吹,树一摇,就瑟瑟地往下掉,没有片刻留恋。自小她备受呵护,纵然长大后两父女的感情淡泊如水,可潇万川从来没打过她。钻心的痛比脸上炙热的伤疼来得更狂烈,她抚着心口,茫然地看着潇万川,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强忍着不欲流下。
这一切,恍如入梦。而疼痛却来得如此真实,再一次提醒她,这不是梦。
“你违背我的命令擅自出走,逼使我终止了与酋长之间的契约,你令我颜面何存?”潇万川步步进逼,“我最没想到的是,我的女儿竟然会联合外人与我争夺P国的沿海石油开发权。”
潇氏企业在P国本拥有专业的石油开发资源,是P国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只因近年来P国政局动荡,有传说政府有意将本土企业进行分拆,他不得已另外注册了一个新公司,注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并以亏本的价格参与了沿海石油开发权的竞标。虽然亏本,但他更看重的此开发权背后所带来的一系列丰厚利润。透过疏通各种关系,他对这次竞标——实际上是“黑标”胜券在握。
可最终却因为海纳斯总督府上的一场变故,泡影成空。知道潇万川为新公司幕后操控手的身份的人寥寥无几,包括海纳斯在内,也只以为参与竞标的是一间资金实力雄厚但知名度不高的新公司。那次宴会他因病没能参加,委派凌少祺全权代表潇氏企业出席。事后海纳斯实行了消息全面封锁,他从其他途径获知了事件的始末,也终于知道海纳斯为何会突然改变初衷单方面毁约。
潇万川损失惨重,他万万没想到,司徒皓谦身边的女人竟然会是自己的女儿——潇夏曦。
这些潇夏曦并不是没想到,只是在当时的态势下,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她向来不过问潇氏企业的业务,也曾怀疑过与司徒皓谦的投资公司抗衡的神秘对手是潇氏企业,可是根据司徒皓谦掌握的资料,并没有证据证明她的猜想。在P国从事石油开发投资的企业何止千万家,而且记忆中听凌少祺提过,潇氏企业近十年的投资重点将会在中东地区,所以才会有潇万川拟与酋长联姻的一幕。
“面子?”潇夏曦的神色清冷如冰,“爹地,在你的心目中,我的幸福还比不上你的面子?比不上你的那些油田吗?”
这句话她压抑在心里很久很久了,自那个女人踏进家门起,她对潇万川的表现就很失望。那个女人剥夺了父亲对母亲及对自己的爱,但最终的责任还在于潇万川,他违背了当初的承诺,一个作为丈夫和父亲该有的承诺。
“嫁给酋长有什么不好?身份地位应有尽有,金钱财富享之不尽,这是我给你早铺好的康庄大道。”潇万川丝毫不认为自己的专横是对潇夏曦不公平,说得非常理直气壮。
“说是为了我好,这全是你为自己推托的措辞。”潇夏曦脸色苍白,愈显得面颊上的五个指印触目惊心,“你窥觎酋长的油田,将我当作礼物一般送给别人。爹地,你变了。我是你的女儿,你有尊重过我的决定吗?”在她看来,潇万川的贪婪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更令她的心冷到了极点。
潇万川的脸色也由青转黑,一把抓住潇夏曦的手,捋起长袖,露出一截满布瘀痕的臂膀:“你的决定?!哼,你的决定是让你成为司徒皓谦掠夺的女人,然后再被抛弃吗?相信不日的将来,我潇万川的女儿被司徒皓谦抛弃就会成为P国上层社会流传的笑话。”
青一块紫一块的瘀痕非常讽刺地映入眼际,潇夏曦不由得一阵晕眩,使劲将手从他腕里挣脱出来。在时间冲刷后这些瘀痕将会消失,但不可磨灭的是她心头上屈辱的印记。在此之前她与司徒皓谦的相处气氛尚算融洽,才让她天真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也错误判断了他这个人。
她抿唇不语,好一会儿,才蹦出一句话:“司徒皓谦并不知道我是你的女儿。”
潇万川冷笑几声,盯着她锐气渐减的脸说:“你是我女儿的身份他早就知道。而且,还派人到你就读的学校进行了核实。司徒皓谦根本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简单。”
潇夏曦动容。司徒皓谦自以为是,嚣张拔扈,这些她都清楚。她也不认为自己能完全地看透这个人。可是他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身份的?P国宴会前,还是之后?他是故意将她暴露于人前打击潇万川,抑或是以她为饵,并顺水推舟地来个考验?若她临时变节,估计命儿也就当场给结算了。可他为什么又在质疑她是青龙帮派驻的奸细?
司徒皓谦,他简直就是个恶魔。
她颓然地跌坐在地毯上。被父亲出卖,被司徒皓谦摆布,她从来以为自己的人生可以由自己作主,倒头来只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
“你不是早就对外公布,解除了我与你之间的父女关系了吗?”她手指微微合拢,声音却冷得彻骨,如同赌气,“这次你大可以顺理成章地对外宣布,那女人生的儿子是你唯一的继承人了。”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潇万川居高临下冷眸微张,她娇小的身躯被笼罩在他的身影之下,“这里不是你的家。”
闻言,潇夏曦全身一震,面色惨白到极点。
之前她可以当他说的全是气话,毕竟她违背了他的命令。但在亲耳听闻后,她感觉所有的信念都在霎时间轰然倒坍。她的父亲,坦然地毫无留恋地向她发出了驱逐令。
是啊,她为什么还要回来?
她忘记了潇万川从来说一不二,忘记了他为逼使她服从中止了她在外国的所有财政支持,忘记了她已经不再完璧不可能再成为他联姻的棋子,而在受到伤害之后仍然天真地以为,她还能蜷缩在潇万川的怀里,乞求那久违的温暖。
泪水,终于忍无可忍,簌簌而下。
木然地跑离潇万川的视线,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伤痕累累,潇夏曦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竭止自己不断奔涌的泪水,还可以为谁停留。这天地辽阔,仿佛已没有了她的容身之所。
在昏迷之前,恍眼里她看到了他。热炽的目光犹如苍茫大海里的一座灯塔,容她这片在风雨中飘摇的小孤舟只能不顾一切地投向他。她紧紧地攥着他的臂膀,央求:“带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