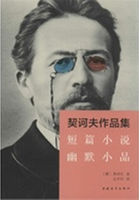第二十九章
中午我们的车子陷在一条泥泞的道路上,那地方据我们估算,离乌迪内大约有十公里。上午雨就停了,我们三次听见飞机飞来,眼看着从头顶上飞过去,往左边飞到远处,听见轰炸公路的声响。我们在纵横交错的小路上探索行进,走了不少冤枉路,不过走不下去就掉个头,总能找到另外一条路,这样离乌迪内也就越来越近了。这当儿,艾莫的车在退出一条绝路时,陷进了路边的软泥里,车轮越是打转,车子往泥土里陷得越深,最后车子的差动齿轮给卡住了。眼下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把车轮前边的泥土挖开,弄些树枝塞进去,好让车轮上的铁链不打滑,再把车子推到路上。我们都下了车,围在车子周围。两位中士望望车子,检查了一下车轮。随即一声不吭,拔腿就走。
“来,”我说。“去砍些树枝。”
“我们得走了,”一个中士说。
“马上动手,”我说,“砍树枝去。”
“我们得走了,”一个中士说。另一个一言不发。他们急着要走,看都不想看我。
“我命令你们回来砍树枝,”我说。其中一个转过身来。“我们得走了。再过一会儿你们就会被切断退路。你无权命令我们。你不是我们的长官。”
“我命令你们去砍树枝,”我说。他们转身沿路走去。
“站住,”我说。他们只管沿泥泞的路上走去,两边都是树篱。“我命令你们站住,”我嚷道。他们走得更快了。我打开了枪套,拔出枪来,对准那个说话多的开了一枪。可是没有打中,两人拔腿就跑。我连开三枪,撂倒了一个。另一个钻过树篱,没了踪影。他穿过田野时,我隔着树篱朝他开枪。只听手枪吧的一声,没有子弹了,我连忙再装上一夹子弹。我发现第二个中士已经跑远了,手枪打不着了。他低着头在田野上奔跑,已经跑得太远了。我往空弹夹里装子弹。博内洛走上前来。
“让我来结果他,”他说。我把手枪递给他,他朝那个扑倒在路上的工兵中士走去。博内洛弯下身,把手枪对准那人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枪没打响。
“你得扳起扳机,”我说。他扳起了扳机,连开了两枪。他抓住中士的两条腿,把他拖到路边丢在树篱旁。然后走回来把枪还给我。
“狗娘养的,”他说。他朝中士望了望。“你看见我打死他的吧,中尉?”
“我们得赶快弄点树枝来,”我说。“那另一个我打中了没有?”
“我想没打中吧,”艾莫说。“他跑得太远了,手枪打不到。”
“混账东西,”皮亚尼说。我们都在砍树枝。车里的东西全卸下来了。博内洛在车轮前挖土。我们准备好后,艾莫发动了车子,挂上了挡。车轮在打转,把树枝和泥土直往后甩。博内洛和我用力推车,推到觉得关节都快折断了,车子还是不动。
“把车子来回冲一冲,巴尔托,”我说。
他先倒车,再往前开。车轮陷得更深了。车子的差动齿轮又卡住了,车轮在挖开的窟窿里直打转。我直起身来。
“我们用绳子拉拉看,”我说。
“我看没用,中尉。你没法往直里拉。”
“只能试试看了,”我说。“别的法子弄不出来呀。”
皮亚尼和博内洛的车子只能沿着窄路直直地往前开。我们用绳子把两辆车拴在一起,拉了起来。车轮只是往旁边动了动,顶住了车辙。
“没有用,”我嚷道。“住手吧。”
皮亚尼和博内洛跳下车,走回来了。艾莫也下了车。两个姑娘在路前边大约四十码处,坐在一垛石墙上。
“你看怎么办,中尉?”博内洛问。
“我们接着挖,再用树枝试一次,”我说。我朝路上望去。都是我的错。我把他们领到了这儿来。太阳快从云后边露出脸了,中士的尸体躺在树篱边。
“我们拿他的上衣和斗篷来垫一垫,”我说。博内洛去拿了来。我砍树枝,艾莫和皮亚尼挖掉车轮前和车轮间的泥土。我剪开斗篷,撕成两半,铺在车轮底下,然后垫上树枝,好让车轮不再打滑。我们准备好了,艾莫爬上去开车。车轮转动起来,我们推了又推。但还是没有用。
“该×的,”我说。“车里还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吗,巴尔托?”
艾莫拿了干酪、两瓶酒和他的斗篷,跟博内洛一起爬上车。博内洛坐在驾驶盘后面,在查看中士上衣的口袋。
“还是把衣服扔了吧,”我说。“巴尔托的两个处女怎么办?”
“她们可以坐在车后头,”皮亚尼说。“我看我们也走不远。”
我打开救护车的后门。
“来吧,”我说。“上来。”两个姑娘爬进去,坐在角落里。刚才开枪的事,她们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回头望望那条路。中士躺在那儿,身上穿着脏兮兮的长袖内衣。我上了皮亚尼的车子,便出发了。我们打算穿过一块农田。到了大路穿进农田的地方,我下了车在前头走。我们要是能穿过去,那边就有一条路。可我们就是穿不过去。田里的泥土太软太泥泞,车子没法开。最后车子完全停住了,车轮陷入烂泥中,一直陷到轮毂,我们就把车子扔在田里,徒步向乌迪内进发。
我们上了那条回公路的小路时,我指着路那边给两个姑娘看。
“往那儿去吧,”我说。“你们会碰到人的。”她们望着我。我掏出皮夹子,给了她们一人一张十里拉的钞票。“往那儿去吧,”我指了指说。“朋友!亲人!”
她们听不懂,但却紧紧地抓着钱,朝那路上走去。她们回过头来看看,好像怕我把钱拿回去似的。我望着她们沿小路走去,把披肩裹得紧紧的,惶恐地回头望望我们。三位司机纵声大笑。
“我也朝那个方向走,你给我多少钱,中尉?”博内洛问。
“她们要是被逮住,混在人群里比单独行动好,”我说。
“给我两百里拉,我可以直接回到奥地利,”博内洛说。
“人家会把你的钱抢去的,”皮亚尼说。
“也许战争会结束,”艾莫说。我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赶路。太阳想冲出云层来。路边有桑树。从树林间可以望见我们那两辆篷式救护车陷在田野里。皮亚尼也在回头看。
“他们得修条路,才能把车子弄出来,”他说。
“基督啊,我们要是有自行车就好了,”博内洛说。
“在美国有人骑自行车吗?”艾莫问。
“以前有。”
“在这儿骑自行车可真了不起,”艾莫说。“自行车这东西好极啦。”
“基督啊,我们要是有自行车就好了,”博内洛说。“我可走不了路。”
“是开火的声音吧?”我说。我好像听见远方有开火的声音。
“搞不清楚,”艾莫说。他听了听。
“我想是吧,”我说。
“我们首先看到的会是骑兵,”皮亚尼说。
“他们不见得会有骑兵吧。”
“求求基督,但愿他们没有,”博内洛说。“我可不想让该×的骑兵用长矛把我刺死。”
“你倒是实实在在向那中士开了枪,中尉,”皮亚尼说。我们走得很快。
“是我打死了他,”博内洛说。“我在这场战争中还从没杀过人,我一辈子就想杀一个中士。”
“你是趁他动弹不了的时候打死他的,”皮亚尼说。“你打死他的时候,他并不在飞奔。”
“没关系。这是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我杀了那个××养的中士。”
“你忏悔的时候会怎么说?”艾莫问。
“我会说:‘我的天哪,神父,我杀了一个中士。’”他们都笑起来。
“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皮亚尼说。“他不去教堂的。”
“皮亚尼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博内洛说。
“你们真是无政府主义者吗?”我问。
“不是,中尉。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是伊莫拉人。”
“你去过那儿吗?”
“没有。”
“基督可以证明,那可是个好地方,中尉。战后你来好了,我们让你开开眼界。”
“你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人人都是。”
“那镇子不错吧?”
“好极了。你从没见过这样的小镇。”
“你们怎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直是社会主义者。”
“你来吧,中尉。我们也让你成为社会主义者。”
路在前头向左转弯,那儿有一座小山,在一堵石墙那边,有一个苹果园。沿路往山上去时,他们就不说话了。我们一齐快步往前赶路,想争取点时间。
第三十章
后来我们上了一条通往河边的路。这路上一直到桥边,有一长溜被遗弃的卡车和畜力车。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河水涨得很高,桥被拦腰炸断了;石拱跌入河中,褐色的河水就从上面流过。我们沿着河岸往上走,想找个过河的地方。我知道河上头有一座铁路桥,我想我们可以从那儿过河。小路又湿又泥泞。我们没见到任何部队;只看到被遗弃的卡车和辎重。河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看不见,只有潮湿的树枝和泥泞的地面。我们来到岸边,终于看到了铁路桥。
“多美的一座桥,”艾莫说。那是一座普通的长铁桥,横跨在一条通常干涸的河床上。
“我们还是赶快过去,别等到他们把桥炸掉,”我说。
“没人来把桥炸掉,”皮亚尼说。“人都跑光了。”
“也许埋了地雷,”博内洛说。“你先过,中尉。”
“听听这个无政府主义者讲的话,”艾莫说。“让他先过。”
“我先过吧,”我说。“就是埋了地雷,一个人踩上去也不会爆炸。”
“瞧,”皮亚尼说。“这才叫有脑筋。你怎么就没脑筋呢,无政府主义者?”
“我要是有脑筋的话,就不会在这儿了,”博内洛说。
“说得很有道理,中尉,”艾莫说。
“很有道理,”我说。我们现在临近铁桥了。天上又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桥看起来又长又坚固。我们爬上路堤。
“一次过一个,”我说,动身往桥那边走去。我仔细察看枕木和铁轨,看有没有地雷绊发线或炸药的痕迹,但是什么也没看见。从枕木的空隙往下看,底下的河水又混浊又湍急。而前边,越过湿漉漉的乡野,可以望见雨中的乌迪内。过了桥,我再往后看。河上游还有一座桥。我正看着,一辆黄泥色的小汽车开上桥来。桥的两边很高,车一上桥就看不见了。但是我看到了司机的头,坐在司机旁边的那人的头,还有坐在后座的那两个人的头。他们都戴着德国钢盔。转眼间车子过了桥,驶到树木和被遗弃的车辆后面又看不见了。我向正在过桥的艾莫和其他人挥挥手,叫他们过来。我爬下桥,蹲在铁路路堤边。艾莫跟着我下来。
“看见那辆车了吗?”我问。
“没有。我们都盯着你。”
“一辆德国指挥车从上边那座桥上开过。”
“一辆指挥车?”
“是的。”
“圣母马利亚啊。”
其他人都过来了,我们蹲在路堤后边的烂泥里,望着铁轨那边的那座桥,那排树,那道沟和那条路。
“你看我们是不是被敌人切断了退路,中尉?”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辆德国指挥车打那条路上开过去了。”
“你不觉得有点蹊跷吗,中尉?你脑子里没有什么奇异的感觉吗?”
“别开玩笑了,博内洛。”
“喝点酒怎么样?”皮亚尼问。“就是被敌人切断了退路,还是要喝点酒的。”他解下水壶,打开塞子。
“瞧!瞧!”艾莫说,指着路上。石桥顶上,可以看见德国兵的钢盔在移动。那些钢盔向前倾斜,平稳地移动着,简直像是被神奇的力量操纵着。那些人下了桥,我们才看见他们。原来是自行车部队。我瞧见前两个人的脸。又红润又健康。他们的钢盔戴得很低,遮住了前额和脸侧。他们的卡宾枪给扣在自行车架上。手雷倒挂在腰带上。钢盔和灰色制服都湿了,但却从容地骑着车子,眼睛瞅着前方和两边。先是两人一排——接着是四人一排,然后又是两人,接着差不多是十二人;接着又是十二人——然后是独自一人。他们不说话,不过就是说话我们也听不见,因为河水的声音太喧闹。他们到了路上就消失了。
“圣母马利亚啊,”艾莫说。
“是德国兵,”皮亚尼说。“不是奥国佬。”
“怎么这儿也没人阻拦他们?”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把桥炸掉?为什么路堤上也不架设机关枪?”
“你跟我们说说,中尉,”博内洛说。
我很气愤。
“该死,整个事情荒唐透了。他们炸掉了下面的小桥。这儿却把大路上的桥给留下来了。人都跑到哪儿去了?难道压根儿不打算阻击敌人吗?”
“你跟我们说说,中尉,”博内洛说。我闭口不语。这不关我的事;我的任务只是把三辆救护车开到波代诺内。我没完成这个任务。我现在只要人赶到波代诺内就行了。我也许连乌迪内都到不了。真见鬼,我办不到。要紧的是保持镇静,不要给人打死,或者给人俘虏去。
“你不是打开了一只水壶吗?”我问皮亚尼。他把水壶递给我。我喝了一大口。“我们还是动身吧,”我说。“不过不用急。你们想吃点东西吗?”
“这可不是久留之地,”博内洛说。
“好的。我们动身吧。”
“我们靠这边走吧——免得给人看见?”
“我们还是走上边吧。他们也可能从这座桥赶来。我们可别还没看到他们,就让他们出现在我们头顶上。”
我们沿着铁轨走。两边都是湿漉漉的平原。平原前头就是乌迪内山。山上城堡的屋顶都掉了下来。我们看得见钟楼和钟塔。田野里有许多桑树。我看到前头有个地方,铁轨都给拆掉了。枕木也给挖出来,扔在路堤上。
“卧倒!卧倒!”艾莫说。我们扑倒在路堤边。路上又来了一队骑着自行车的人。我从堤顶上瞅着他们骑过去。
“他们看见我们了,但还是往前走了,”艾莫说。
“我们要是在上边走就会被打死的,中尉,”博内洛说。
“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我说。“他们另有目标。他们要是突然撞上我们,我们就更危险了。”
“我情愿在这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走,”博内洛说。
“好吧。我们沿着铁轨走。”
“你认为我们能穿过去吗?”艾莫问。
“当然能。他们人还不是很多。我们趁着天黑溜过去。”
“那辆指挥车是来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