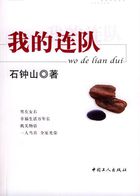(庚)外国人著述
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晋法显、唐玄奘、义净,皆游历印度之高僧。显著有《佛国记》,奘著有《大唐西域记》,净著有《南海寄归传》,此三书英法俄德皆有译本,欧人治印度学必读之书也。] 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可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马可波罗,意大利之威尼斯人。生于1251,卒于1324。尝仕元世祖,居中国十六年,归而著一游记。今各国皆有译本,近亦有译为华文者矣。研究元代大事及社会情状极有益之参考书也。] 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拉施特,波斯人。仕元西域宗王合赞,奉命修国史。书成,名曰《蒙古全史》,以波斯文写之。今仅有钞本。俄德英法皆有摘要钞译本。清洪钧使俄,得其书,参以他书,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为治元史最精诣之书。但其关于中国本部事迹甚少,盖拉氏身仕宗藩,详略之体宜尔也。]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36]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钜,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日本以研究东洋学名家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于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于佛教,内藤虎次郎之于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于古石器,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36]现代欧人关于中国考史的著述,摘举其精到者若干种列下。
(一)关于古物者:Mlünsterberg: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Künste. qqreader-footnote" src="images/note.png" alt="B.Laufer:jade. B.Laufer:Sino-Iranica. B.Laufer:Numerous Other Scientific Papers. Chavannes:Numerous Books and Scientific Papers. Pelliot:Mission Pellioten Asie Centrale. A.Stein:Ancient Khotan. A.Stein:Ruins of Desort Cathay.
(二)关于佛教者: Waddell:Lhasa and its Mysteries. Hornle:Manu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Huth: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oiei. Thomas Watters: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三)关于外国关系者: Blochet:Introduction a une Histoire des Mongloes. Hirth: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Mookerji: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Sta?l—Holstein:Tocharisch und die Sprache 1. V.Sta?l—Holstein:Tocharisch und die Sprache 2. Chavannes:Les Tou—kiue Occidentaux. O.Franke:Beitra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u zur Keuntniss der Turkvo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弆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研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前章列举多数史料,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有相当之技术焉。兹分论之。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见于旧史者,或无须特别之搜集;虽然,吾侪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又如治动物学者搜集标本,仅一枚之贝,一尾之蝉,何足以资研索;积数千万,则所资乃无量矣。吾侪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试举吾所曾致力之数端以为例:
(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迥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
(乙)吾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时,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者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此数。吾因将此百八十余人者,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
(丙)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钞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抟捖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吾又尝向各史传中专调查外国籍贯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殚,突厥人之阿史那忠,于阗人之尉迟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
(丁)吾又尝研究六朝唐造像,见初期所造者大率为释迦像,次期则多弥勒像,后期始渐有阿弥陀像,观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见各时代信仰对象之异同;即印度教义之变迁,亦略可推见也。
(戊)吾既因前人考据,知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此后读《元史》及元代碑版与夫其他杂书,每遇“也里可温”字样辄乙而记之,若荟最成篇,当不下百条,试加以综合分析,则当时基督教传播之区域及情形,当可推得也。
以上不过随举数端以为例。要之吾以为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即其极好模范。惟史学方面,则用者殊少。如宋洪迈之《容斋随笔》,清赵翼之《廿二史劄记》,颇有此精神;惜其应用范围尚狭。此种方法,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欲应用此种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月不有苹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月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能因此而发明蒸汽;此皆由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例如吾前文所举(甲)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云尔;所举(乙)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我国史学界,从古以来,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段,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试举其例:
(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用金。再进而研究钟鼎款识,记用贝之事甚多,用金者虽一无有;《诗经》亦然;殷墟所发见古物中,亦有贝币无金币,因此略可推定西周以前,未尝以金属为币。再进而研究《左传》《国语》《论语》亦绝无用金属之痕迹。因此吾侪或竟可以大胆下一断案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属货币。”若稍加审慎,最少亦可以下一假说曰:“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