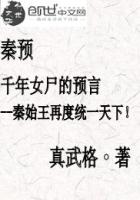H大后山处,看着天边夕阳西下的余晖,我有些迷茫,因为余晖的红光将天与地都是映衬在这如仙境般缥缈之中,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就似乎这片红光是被血液所染红的,给人一种肃杀和颤抖的感觉。
看罢多时,擦了擦眼角就将爷爷交给二叔的盒子缓缓的拿了出来。
这只盒子上面镶刻着古老的花纹,为什么说这些花纹非常古老呢,因为这些花纹我一种都是没有见过,在现在的装饰品种不会出现的。而且说是花纹其实倒是更加的像是甲骨文或者是图腾图画之类的。
这些看不清是文字还是花纹或是图腾的镶刻,布满盒子的四周包括盒盖,并且处处透着诡异。这个盒子的第一部分是一个眼睛一样的东西注视着这个盒子;第二部分是一只手伸向盒子;第三部分是手在盒子旁边;第四部分是一只被打开了的盒子;第五部分是一只充满血丝的眼睛而没有盒子。再往下看就是底部了,底部什么都没有。
我一直很疑惑这只眼睛,它到底是看见了什么?居然能够让它如此恐怖,竟然能够让它吓眼睛上全部布满血丝,这是一直非常疑惑的。其实我不知道它到底是被吓的还是怎么回事,但是此刻我看着的感觉却是那种被吓的感觉。
而其实这盒子除了花纹一般的物件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使得这个盒子变得无比的诡异。那便是一块——拥有六根手指的红色印迹。这块红色的印迹红的就像鲜血一样,给人一种它正在缓缓的往下流淌的感觉。这种感觉似乎在告诉我这个盒子不是好东西,会给我带来厄运。
倘若不是爷爷将它再三叮嘱让我好好保管,我想我现在就算不把它扔了也会将它直接交给二叔。但是我答应了爷爷,那个没有一丝活人气息,处处透着死亡气味的老人。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但是至少在那样的境地之下,我做的是对的。
这只如鲜血一般的手印,就恰恰在第一部分图案与第二部分图案上,而这两部分之间则是打开盒子的开口之处。也就是说想打开这个盒子那么久必须得将这块红色的手一样的印迹分开。
我望着这个盒子却是感觉到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心理,这些图案以及血液印迹一般的红色手印似乎都是在警告着每一个得到这个盒子的人,盒子里面装着一个可怕的东西,不要将这盒子打开,否则他就会如盒子上的那只眼睛一般被血丝所包围。
虽然说我对于这有些未知的害怕,但为了履行对爷爷的承诺,我还是依然决然的将盒子打开了。我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在等着我,但我却坚信爷爷是不会害我的。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二叔之外我恐怕就他唯一一个亲人了。
母亲在生我的当晚因为难产就死在了手术台上,而父亲则是一直视我如仇敌。没没看见我都似乎有一种想要掐死我的冲动,但他却是真的没有这么干,或许是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一个孩子吧。即使这样他也从不和我说一句话,看见我就说我是“煞星”。就这样一直延续到我七岁的时候,他便不知道去了哪里似乎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
此后便一直是二叔和爷爷照顾我,爷爷对待我非常的严厉,感觉似乎好像是受父亲的影响一般。我从两岁的时候,爷爷就开始对我进行近乎魔鬼一般的训练。在这样残酷的训练下,我往往是被弄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每每如此我就想要一个安慰的话语,爷爷给我的却总是——“小剑,你必须在太阳下山前将……完成。”“小剑,你还没完成啊,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跪下!”
在爷爷的身上我小时候得到的却总是打骂与训练,他却是从未关心过我,我受伤了他也只是说一句:“蠢蛋,你不会快一点啊。”“你不会躲开啊。”“你不会拿东西挡一下啊!”之类的话,在他的意识里似乎没有关心这个概念。
但我却是见到爷爷的朋友却总是络绎不绝的往家里来,似乎在他的交际圈中总也不缺朋友。一个朋友走了,另一个朋友又来了,给我的概念似乎就好像爷爷的朋友就是多。这使得我非常的疑惑,一个近乎苛刻的人,怎么会有这样多的朋友的。
一个姓陈的爷爷给了我这样的答复。
陈爷爷的我见过最为活跃的人,他也是经常来我家里玩的最多的人。其实我不明白他这样一个活泼快乐的人,在我爷爷这样一个总是严肃,不容质疑反对的强权主义者下是如何成为朋友的。
“小不点,你是一点也不明白我对你爷爷的崇敬之心,等你以后经历一些事情就会明白了。”
我看着这样一位满头白发,却是依然面色红润如潮的老人,心中充满不解。因为我在他的眼睛中不仅仅看到了崇拜和崇敬,更有一种好像随时可以为我爷爷奉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冲动使命感。似乎我爷爷只要现在叫他去死,他可能就会毫不犹豫的去死,绝不眨一下眼睛,皱一下眉头。
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能够让这样一个比我爷爷甚至都要苍老的人,竟然能够表现出这样的情绪出来。我爷爷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能够让这些和他有着一样家室甚至老的人,心甘情愿的奉献出自己的满腔热忱和鲜血。
我本想再多了解的去问他关于这些的原因,可他每次都是以这些都不是小孩子可以知道的为借口,将我的求知火焰给扑灭。
即使如此我也依然觉得爷爷的不近人情,我是他唯一的孙子,他却是对我如此近乎残酷的折磨,使我的童年备受精神和心理上的折磨。
每当我筋疲力尽的回到家里,向着那父亲紧紧关闭的房门望去时,我就有一股想要冲进去紧紧的抱住父亲粗壮的臂膀哭泣的冲动。然而每一次我都是忍住了,因为我知道我冲进去的结果将会是比现在更加痛苦,那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心灵上的折磨。
从每次他那种看着我近乎是要吃人的眼睛,和两个“煞星”的字,几乎每每都给我一种想要哭死的冲动。他每一次的眼神和每吐出的词语,都使得我才四五岁的心灵抹上了挥之不去的阴霾。
所以我每次经过他的房间门口时,我都会抹着眼泪跑着过去的。即使再跑的时候摔倒我也不会发出一点声音,因为我知道我那样做之后所面对的始终只是冷眼与热讽。所以我宁愿自己在怎么痛苦,也要先跑出父亲的房门,再将心中的苦意吐露出来。
记得有一次我在跑过父亲那段房门时,因为跑得太急居然没注意脚下,一不小心就被一块石头给绊的摔了个大跟头,这个跟头使我我在医院住了将近一个多月。因为这个跟头使我摔断了两条肋骨。
因为我当时才四岁,身体脆弱不堪。若并不是爷爷那近乎残酷的魔鬼训练,我当时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两说。
所以当时我哭的非常大声,这个院子的所有人都能够听见我的哭声。我虽然在哭泣但是眼睛却是紧紧的盯着父亲的房门,希望他能够在听见我的哭声后立即冲出来,二话不说抱着我就往医院跑。
然而我迎来的却是——父亲若无其事的打开门,眯着眼看着我,然后不耐烦的对我说道:“小声点,你没看见现在都晚上十点多了,人家明天还要上班采货呢!”
说完居然狠狠的将房门关了上去,当时虽然全是楼房瓦舍,但仿佛我始终独自的处在空旷的原野上一般。那一句‘小声点’真的是伤透了我脆弱幼小的心灵。
我望着这一幕心中充满了恨意,我对这个陌生而熟悉的人彻底的绝望和失望了。我当时就在想:“你既然如此的恨我,不喜欢我,讨厌我。那为什么还是将我给生出来?将我打掉或者生出来摔死、掐死不是更加的合了你们的心意了吗?为什么要留下我,为什么……”
我的叫喊声虽然引来了父亲的冷嘲热讽,但却又将正在熟睡的二叔给惊醒了。他见我躺在地上抽泣,赶忙跑过去问我怎么回事。可是我当时已经被疼的说不出话来了,所以只能望着他哭。他见我这样便将我鼓起来看是怎么回事,然而在他看见的瞬间,他的脸就瞬间沉了下来。他看见我的身体下方有一块小砖头,而拿手一摸脸上的面色也是立马变了。
他在这时惊慌失措的立马便朝着父亲的方向喊了几句:“大哥、大哥,周剑他的肋骨断了。”
许久父亲这才开门,揉揉眼睛看了看二叔说道:“哦,没死吧,没死就还能够活,这有啥大惊小怪的。”
这时二叔惊讶的望着父亲说道:“大哥,你这是什么话啊,快点打电话叫救护车啊。”
父亲不耐烦的说道:“这大晚上的,叫了也不一定能来啊,还是明天打吧,我现在困得很,有事明天说。”
说着便重重的关上房门。
我在见到父亲这样的情况时,我对父亲的恨意真的已经到了附加的地步了。恨不能现在自己就站起来,用脚踢开父亲的门,用刀子挖开瞅瞅他的心是不是黑色的。为什么如此的铁石心肠。
二叔见状也是无奈正准备抱着我往房间跑,这时爷爷却是从外面走了进来。在了解了情况后,二话不说抱着我就往车里塞,然后开着车就往医院的方向跑。
在跑的时候对着二叔说:“医院现在到这里准备起码也要三十分钟,现在我就开车送小剑去医院,晚了孩子就废了。”
二叔点点头跟在爷爷的身后。
随后又是爷爷对着我说道:“小剑你忍着点,爷爷马上就帮你送到医院了,到了医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想想那时我才发现爷爷还并不是那样的严厉,他的内心还是爱我的。也明白了那种如陈爷爷般奉献生命、鲜血的热枕了,所以即使爷爷对我再怎么严厉我也没恨过他。
就这样我打开了盒子,原本以为里面装着的是什么恐怖的东西,但却是发现里面居然只是装着一个眼球一样的珠子,和一卷残破的书简。
残破的书简上面用大篆赫然的刻了三个醒目的大字——‘罗刹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