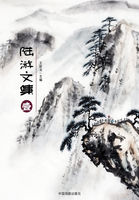“幼贫,多病,出生未几父母双绝,祖父母抚养到三岁也过世,被意大利人皮诺罗收养。”
水晶球是最具现场效果的算命工具,能贴切阐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的精确意思,法力高深的人眯起眼睛对着中心猛看,效果和在国家歌剧院观赏皇家芭蕾舞团表演差不多,坐的还是头等包厢。
那舞台上演出来是霍金少年时毫无表情的脸,他在烹调艺术学院埋头钻研功课,身边一点昏灯,常年如一日穿一件逐渐褪色的卡其外套,以及式样颇为滑稽的杏色绒线帽子。
看到他将近二十岁那一年,在米兰街上犹豫地停下脚步,而后一个俯冲,冲向一辆快速奔驰而来的吉普车车头,奔向这一场意外,如信教者奔向至高真理的光辉。
看到他在医院里悠悠醒来,无人陪伴在侧,因为没有保险赔付,很快被赶出病房。
收养他的人许多年前因为车祸去世,同样的遭遇还发生在所有与他关系亲密的人身上,无论朋友、同学,还是邻居。
稍微深入到霍金生命里的人都不得善终,不得长久。
这是不是他对人世既不防备,也不计较的原因?
狄南美抬头看看霍金,这有着深深法令纹的小个子男人站在厨房里,头顶上有一盏终日开着的暖灯。他静静听着狄南美毫无感情变化的叙述,偶尔耸耸肩表示认同或惊奇,仅此而已。
这些都是过去。
过去云淡风轻,如同一个故事,无关紧要。
我的未来是什么?
狄南美轻轻叹口气,双手按上那水晶球,有白色明亮光芒从她手底下溢出,照亮整个屋宇,随即又暗淡。她向霍金点点头,说:“你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那神色中甚至有温柔。
霍金对这美好的宣言仿佛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
“其他人不是这样说的。”
“其他人说什么?”
“他们一样猜中我的前半生,而后说,我很短命。”
每一个算命师来到利宅,临走的时候都会应利先生的要求,简略为霍金说上几句。
这是霍金提出的要求,他愿以全年的薪酬作为交换——他知道主人请来的算命师大都身价高昂。
利先生欣然同意,但每个月工资照发。
无一例外,算命师们发现,霍金人生的脉络和走向都和利先生有惊人的相似,简直像共同履行一个和命运签署的合同,条款非常不公,执行起来还霸王之至。
狄南美是唯一不走寻常路的那个。
面对霍金的质疑她毫无愠色,只是拂一拂袖,料理台上的东西如来之突兀,瞬息间无影无踪,她跳下来,在霍金的手臂上搭一搭:“本来呢,你是很快要死的,不过别担心,有我在,你呀,就是想死都死不了呢。”
她拍拍胸膛,很豪气地翻着白眼,如此说。
霍金神色如常,既不惊喜,也不意外,只是点点头。
此时已黄昏,天外残阳余色如暗金,利先生的晚饭要在一小时后准备好。
主菜是小牛腰肉,配新鲜芦笋清汤,甜点是提拉米苏,今天利先生忽然有点嗜糖。
之后,她如旧会见算命者,今天的这个来自遥远的罗马尼亚,是神秘的吉普赛世界里最负盛名的流浪者先知。
对于命运,利先生仿佛一直在期待谁能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答案。
利宅会客室整体风格华贵张扬,黄金墙纸熠熠生辉,客人的座椅以整幅豹皮覆盖,纹路如生,咆哮欲出,布置色调如此张扬暴烈,仿佛在和主人的心境做最强烈的反比。
晚饭后,利先生便独坐东北角上她专用的单人椅上等候。穿一件宝蓝色的希腊式长袍,膝盖上覆软毯,搭在外面的一双手修长有力,骨节突出,充满力量感,和养尊处优四个字搭不上关系,更不像美人的手。
她身边的小几上放了一杯咖啡,喝到第三口,加了第二块糖,这举动很罕见,就像她脸上轻松愉快的表情一样。
利先生不是乐天派,从前不是,以后也不会是,这样的人对世情不容易失望,坏处是面对任何狂喜也都难以满足。
也许除了某时某刻,对某人。
可惜那一切那一刻过去经年,迅疾如闪电,恍惚永不复返。
咖啡喝到一半,下人通过隐藏在小茶桌下的门禁系统轻声通报,先知到了。
利先生抬一抬手,会客室通往大厅的门应声而开。
来人着黑袍,个子纤细轻灵,头脸包裹严实,露出瞳仁一色,无眼白眼黑之分,沉寂如永夜或尘封的书卷封面,仿佛是一个在黑暗中万劫不复的瞎子。
但他明显可以视物,径直走到利先生前大约数米的客位坐下,眼球微微转动,幅度非常小,却像把周围事物都已经打量完全。
“你要问什么?”
他,其实是她。嗓音低沉嘶哑,但闻之仍是女人的腔调。
利先生轻轻说:“未来。”
和这位先知相比,她有一双太美的眼睛,明如秋水,蕴如深潭,无丝毫瑕疵。如果非要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可相提并论之处的话,那就是同样没有喜悦或悲哀,没有任何值得纪念与庆祝的情绪流露。
垂一垂她幽黑的睫毛,利先生重复道:“未来。”
吉卜赛人举起手,如同擦拭一副看不到的眼镜般,在自己眼前缓缓来往摆动,而后放下。
凝神思考,许久,又重复一次刚才所做的动作,再放下。
房间内气氛压抑,场面沉闷,她一来一往的动作,外人看上去十足装腔作势,兼且冗长无谓。但利先生毫不动容,只是静静等待着。
如此再三。
吉卜赛女郎终于长长出了一口气,之前端坐的身形塌陷下来,似乎那些手上的小动作已经耗尽了她的全部精力。
然后她说:“我看不清楚。”
利先生微微扬眉:“未来吗?”
“不是。”
“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很快就会消失,但我看不到谁带走了它,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灵魂即将消失,未来如何都与你无关,何必再问。”
这定论真有理。
利先生唇边露出她惯例在算命结束后会有的那一丝微笑,也许今天还往里面微微增添了些许嘲弄。
“失去灵魂?是不是短命的另外一种说法?”
吉卜赛女郎极为庄重,摇摇头:“失去灵魂和失去生命不见得是同一件事。”
她的眼睛比进来的时候更干涩枯槁,眼白处突然之间增加了一缕一缕血丝,而且还在迅速蔓延,整个人些微瑟缩,筋疲力尽。
窥看一个人的未来,显然要耗费极大的能量。
不再理会利先生有什么疑问,她抖抖索索站起来,慢慢离去,走到门口,忽然转头买一送一一句:“带走你灵魂的,不是人,也不是神。”她轻轻摇头,“所以我看不到。”
门轻轻在她身后合上。
利先生唇上的微笑消失了,眼里却燃起一朵奇异的火花,以某种不知名的隐秘渴望作为燃料,熊熊蔓延在她看似古井般宁静的心里。
一天又这样过去。
夜幕刚刚低沉,远处有某一家在疯狂派对,跳舞音乐响彻夜空。
如果站在室外,会忍不住随着那音乐扭动身体,所谓人生的乐趣,就散布在这一类毫无意义但值得享受的时刻里。
曾经利先生也是类似场合的常客,她每年定期远赴那些繁华的城,定制高级晚装,挑选昂贵珠宝搭配,悉数放在巨大的衣帽间里等候轮番出场,随主人一道在衣香鬓影的场合大出风头。
那些了无心事的时光远去之急速,快过你对未来的所有期待或排演。
她静静坐了一阵,准备起身回房,这时候对讲机中传来厨师霍金的声音,说:“利先生,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
霍金是她的厨师,很多年以来都是,这铜色大宅是铁打的营盘,见识过许许多多流水的兵,最后留下来,而且还不依不饶继续留下去的,只有他们主仆二人。
听到霍金说话,她才反应过来,吉卜赛算命师走得太快,竟然没有如往常一般,顺带为霍金也算算。
他说:“噢,我不需要了,我们现在进来了。”
我们是谁?他没有解释,甚至都不问利先生到底情愿与否。
某种东西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在不需要扮演彼此注定角色的时候,可以以单纯的方式相处。
事实上,狄南美并不是他带来的头一个不速之客,更莫名其妙的人都上过利先生家的门,有卖保险的,有卖野猪的,有想去某个舞会却没有一条珍珠链子配小黑裙的……
五花八门。
只要能够逮到霍金,无一不能达成愿望,幸好因为他社交面十分狭窄,这条接近利先生的捷径还没来得及被大规模利用。
他不求任何回报,也没有甄选求助者的原则,糊涂到这个程度的中间人十分罕见,更罕见的是利先生对此从无异议。
唯一今天她没有心思迁就,因此不由分说便加以拒绝。
“失去灵魂”,这四个字还在利先生的脑海里盘旋,意味深长,勾连无数生之片段、死之犹疑,层层叠叠铺陈,要花费整晚时间细细体会。
她简短吩咐:“改天。”
关掉呼叫器,利先生起身沿着会客室通往楼上的楼梯走回卧室,心思重重,至于自己是否会错过什么,她丝毫没有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