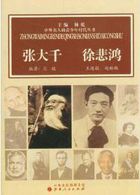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毛泽东极重朋友故旧之情,他深深怀念过去的同学、战友和同事,对那些曾与他同艰共苦、患难相交的旧友时刻铭记不忘,对那些曾经帮助、接济过他或救他脱险的人感怀不已,并设法给予回报。
据王若飞回忆,毛泽东很念旧,不忘老朋友。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飞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到重庆后,他开了一个他过去相熟的新民学会会员名单,叫王若飞去了解老朋友的近况。王若飞很快打听到一位新民学会会员尚在家中赋闲,住在一个山坡上,生活无着,穷困潦倒。“毛主席便亲自去看他,还叫我们事先不要惊动主人。当我们随同主席走进一间低矮潮湿的小屋,告诉主人,毛主席来看望他时,主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久久凝望毛主席,脸上滚下滚滚的热泪,半晌说不出话。屋子矮小阴暗,不便招待客人,毛主席便同他拉过几把旧竹椅,坐到屋外的空地上,款款叙旧……”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过去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乡亲、友人纷纷给他写信,反映家庭生活困难,毛泽东十分同情,或百忙中亲笔写信慰问,叙述旧情,不忘旧谊;或慷慨解囊,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力尽故人之责,倡导仁义之风,表现出高尚的共产主义情怀。
一、郭仕逵北京之行
1950年3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湘潭县良湖乡广福村(今属云湖桥镇见东村)农民郭仕逵,信云:
仕逵先生:
去年十月五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候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郭仕逵(1899—1960),韶山银田寺(今属韶山市银田镇)人,后迁居湘潭县良湖乡,一辈子务农。大革命时期曾帮助毛泽东脱险。此时,郭仕逵接到毛泽东从北京寄来的信,心中异常激动。他的家人亦欣喜万分,感激地说:“毛主席没有忘记我们啊!”
那是1925年2月6日至8月28日,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在他的领导下,韶山成立了“雪耻会”和中共韶山支部,开展平粜、阻禁斗争。韶山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和仇视,他们向当时的湘军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密告毛泽东在韶山一带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赵恒惕遂多次密令其弟、湘潭县长赵恒哲及县团防局逮捕毛泽东。
8月的一天,赵恒惕又一次密令湘潭县团防局会同韶山大地主成胥生,前往韶山逮捕毛泽东,消息传到县政府,有的人对“过激党”恨之入骨,因而幸灾乐祸;有的人同情革命,同情共产党,因而为毛泽东的安全忧心忡忡。同情者中,有这样一个人,他叫郭鹿宾,是韶山银田寺人,当时在湘潭县政府担任议员,负责收发。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同情和支持革命,忧国忧民。他听到赵恒惕密令捉拿毛泽东的消息,迅即将此消息告知曾担任过省学联干事的刘天民。刘天民心急如焚,盘算着如何把这个消息送到韶山去,帮助毛泽东脱险。恰在这时,郭鹿宾的侄儿、共产党员郭仕逵从乡下来叔叔家做客。刘天民和郭鹿宾喜出望外,随即与郭仕逵商量如何把消息送出去,三人密谈了一阵儿,郭鹿宾取出纸笔,急急写了一封信,交给侄儿,嘱咐其当天赶回韶山送交毛泽东。
郭仕逵将信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连忙告别叔父星夜赶回韶山,当即找到了正在冲里一个秘密地点召开地下党员会议的毛泽东,将信面交。毛泽东打开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润之兄:
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派快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反动派不会善罢甘休,看完信,他从容不迫,沉着而又风趣地说:“原来是成八胡子(成胥生的绰号)办的好事!”
毛泽东连忙叫到会的地下党员撤离,再与郭仕逵一道离开了会场,回到上屋场,照常接待了来找他的几位农民兄弟,并对韶山地下党工作做了布置。然后,在几位农民的护送下离开了上屋场。
几分钟后,县团防局大队枪兵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赶到会场,将屋前屋后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破门而入,到处搜查,却毫无收获。接着,又包围了上屋场,仍无所获。
毛泽东和郭仕逵撤离途中远远地看到敌人追来,他们机智果敢地避开敌人,从容离开了韶山冲。毛泽东十分庆幸自己脱险,感谢郭鹿宾这封信帮了忙。他们连夜取道宁乡,向长沙方向走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毛泽东担任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闲居乡间的郭仕逵闻知这一切,异常高兴,几天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叙述了当年为主席送信的情况,并反映家庭生活困难,希望主席替他安排工作。毛泽东接信后,立即亲笔回信。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那封信。
两个月后,郭仕逵手持毛泽东亲笔信,前往北京,谒见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并设宴招待了他。
席间,毛泽东询问了郭仕逵的家庭情况,郭一一做了回答。当问到郭鹿宾还在不在时,郭仕逵说:“叔叔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地下活动,1938年他到了延安。从延安回来后,他从事革命斗争,不久就病死了。”毛泽东听了,说:“郭鹿宾这样的同志,可惜早死了,要是还在的话,我一定请他到北京来做客!”
郭仕逵告诉毛泽东,他住的良湖乡广福村,村里的群众认为“广福”这个名字不好听,过去,国民党并不能为广大人民带来幸福,只有今天,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民才会过上幸福的日子。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出将“广福村”改名“见东村”。
毛泽东问道:“为什么要这样改呢?”
郭仕逵解释说:“‘见东’是见了主席的意思。我代表广福村人民到北京见到了您,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幸福,我们广福的乡亲们都会感到幸福。”
毛泽东摇摇头说:“这个提法不妥,我只是共产党中的一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见郭面有难色,毛泽东又说,“不过,你们要改村名那是你们的自由,我也不能勉强。”
郭仕逵在北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并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郭要回家时,毛泽东赠给他一些钱和礼物。
回到家乡,郭仕逵向当地乡、村干部汇报了在北京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幸福情景,并把主席同意将广福村改为“见东村”的情况告诉他们。乡亲们非常高兴。从此,广福村正式改名见东村。
此后,郭仕逵经常写信向毛泽东汇报家乡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也汇报家庭生活情况。当毛泽东得知郭家尚未摆脱困难时,又给他家寄来了300元人民币。
二、诗友蒋端甫
在韶山杨林,曾经有一位与毛泽东交往密切的教员出身的诗友——蒋端甫。1950年5月,毛泽东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信曰:
端甫先生:
承惠祝词,极感盛意。谨此致谢,兼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这封信写得龙飞凤舞,极为潇洒、美观,连头带尾不到30个字,却写满了一张八行信笺。
蒋端甫(1900—1972),今韶山市杨林乡新溪村人,乡村教师。他自幼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国文功底深厚,熟谙历史掌故,尤其擅长诗词歌赋,还兼教过学生的音乐、算术和珠算等。
20世纪20年代初,蒋氏家族几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创办了自己的族校——“蒋氏听彝学校”,蒋端甫在该校任教。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蒋端甫思想开明,倾向进步,同情革命。他曾和其他进步教员一起编写过族校的校歌:“屏山苍苍,官港泱泱,山高水又长。毓秀钟灵,听彝学校,子弟杰湖湘……全球之上大事业,吾辈要担当。”该歌曲当时在学生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曾广泛流传。
1923年,蒋端甫出任听彝学校校长,聘请蒋梯空、蒋谷风等来校任教,并任董事,师资力量得到加强。学校还决定,凡族内经济困难的学生,一律免费读完四年小学;凡在学校修业期满后考取学校深造的学生,均由族校提供学资。
听彝学校自创办至解放前夕,一直是当地重要的革命活动场所。1925年,毛泽东回湖南开展农民运动,经常去杨林乡做农运发动工作,并以该校为活动场所,向农友宣传革命道理。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该校主要教员蒋梯空积极参加了农运,与毛泽东一起组织成立了“雪耻会”。蒋端甫等其他教师,也参加了这一革命组织。教员蒋谷风还担任了“雪耻会”的秘书。他们积极协助农民夜校,进行革命宣传,并参加农民协会的活动,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运动搞得如火如荼。
在与蒋端甫的交往中,毛泽东深感他富有学识,为人正直,思想较为进步,二人时常一起纵论时局,商讨农运大事。“雪耻会”成立后,蒋端甫常邀毛泽东、蒋梯空等人到家中做客。毛泽东发现他在当地颇有名望,便动员他加入党的组织。但蒋端甫瞻前顾后,未置可否。
一天,毛泽东郑重地询问道:“端甫先生,你能舍弃家庭吗?”蒋端甫感到有些茫然,问道:“润之先生有何指教?”毛泽东说:“我的意思是,你能舍小家为大家吗?”蒋端甫摇摇头。毛泽东动员他离家干革命,他依然沉默不语。
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性,此时的蒋端甫感到革命力量还很薄弱,投身革命,前程未卜。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奉行的是修身齐家、安身立命的准则。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妻室儿女,生活的重负使他过早地衰老了。家难齐何以治国平天下?蒋端甫难以摆脱家庭的束缚,沉默了一会儿,他喃喃地对毛泽东说:“润之先生,我同情革命,非常支持你的事业,但我不能抛妻别子,离开我的家庭啊!”毛泽东理解他的心情,没有责怪他,只是不停地叹息:“你要是能舍弃家庭干革命就好啰!”
这样,蒋端甫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未能投身革命,以致后来遗憾终生。
大革命失败后,蒋梯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于1927年10月英勇就义。蒋端甫因此受到株连,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外出谋生。直到后来“风波”平息,才回蒋氏族校继续任教。
抗日战争时期,湘潭沦陷,日本侵略军盘踞韶山狮子山,闯进蒋端甫执教的私塾,逼他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共荣”的谬论,遭到蒋端甫的拒绝。为了保护学生,蒋先生还拼死与敌人周旋,不为其淫威所屈服。尔后,他携带家眷逃匿他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不屈不挠的品格,在家乡老百姓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新中国成立后,蒋端甫年逾五旬,仍以教书为业。当得知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即于开国大典后的第二天挥笔写下四首七绝,寄给毛泽东,以示祝贺。
蒋端甫的第一首诗写道:
韶峰耸秀毓奇才,古往今来第一回。
引得福星齐降临,云龙凤虎应时来。
这诗中歌颂韶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孕育了一代伟人,表达了对毛泽东的仰慕之情。
第二首是叙旧,表达对故人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曾瞻玉貌在林泉,只隔龙门卅里天。
每忆当年聆雅教,从容态度自悠然。
第三、四首诗讴歌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运动,推翻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使人民重见天日。诗中表达了作者对新中国成立的无限喜悦之情:
推翻专制廿余年,民众犹多苦倒悬。
弊政从今全扫去,一轮红日睹青天。
又:
救国怜贫惠政多,普天同庆尽讴歌。
五星旗帜神州遍,四海升平水不波。
毛泽东接到蒋端甫的诗与信后,甚为高兴,于百忙中给他写了回信。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那封短信。
1950年乡下土改,蒋端甫被划为地主成分。接着,人民政府接收了蒋氏私立族校,并改为公办学校,蒋被辞退,发给大米三百斤作安家费。蒋平时为人师表,恪守修身齐家之道,过去虽是教私塾,但也有益于乡里。对此,他有些想不通,也有人为他愤愤不平,劝他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去找区里负责文教工作的同志“评评理”,并说:“毛主席都祝您教祺——教书吉祥,连书都不让教,何谈吉祥?”蒋端甫犹豫道:“区里大概已经知道我有润之先生这封信了!”又有人劝他再给毛主席写信,请主席发个令,让区里收回成命。蒋端甫却说:“我也这样想过,但我不想写信。”为什么不想写呢?蒋端甫解释说:“古云:同志为友,或曰同党为朋。我和润之先生相交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诗。我不懂共产主义,也没有加入共产党,我们不能称为朋;这么多年来,我没有信仰共产主义,没有参加革命,亦不能称为友。要说写诗为文嘛,我倒会几句,但比起润之先生的鸿篇巨制则是相差万里了!我们最多只能算个诗友。现在,他位居九五之尊,仍不忘旧谊,记得我这个草民诗友,也就很不简单了。如果我再写信向他诉苦,他会很为难的。当然,他也许会念旧情,向区里发个令,聘我任教,料想区里是不会打折扣的。这样,我的问题解决了,可对润之先生来说,就有累于他的清德了。于我,则会有攀龙附凤之嫌!我想,这样的信还是不写为好。”
就这样,蒋端甫失去了最后一次就业机会,再未登上教坛,一直在家赋闲,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默默无闻。
1964年10月,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建成开放。蒋端甫闻之,专程从杨林赶往韶山冲,参观了陈列馆,并挥笔写下一首七绝:
红日青波菡萏开,为游胜地尽流连。
遍观陈列诸文物,便觉胸境顿豁然。
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和对韶山风光的赞美。
1972年,蒋端甫以古稀之年病逝于老家杨林。
三、与刘修豑父子的交往
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1914年春,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该校有几位韶山籍学子。毛泽东同他们常在一起,或游泳、爬山,或切磋学问,或议论时事,探讨革命道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刘修豑便是其中一位。
刘修豑(1895—1947),号继庄,今韶山市如意乡杨荣村人。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编在6班,毛泽东在8班,属同一个年级。刘修豑在校期间,品学兼优。1917年6月,学校开展考查学生德、智、体优秀的“人物互选”活动,全校11个班四百多人参加选举,选出34人,他为其中之一。1918年6月,刘修豑从一师毕业,在该校附属小学教书。在长沙时,刘修豑加入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参加了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和驱张运动。
1921年春,刘修豑应黄笃杰之邀,同毛泽东、言志超、王宏纶、陶诗衡、宫廷璋等先后毕业于湖南一师的湘潭校友,在湘潭昭潭书院内筹组校董会,发起创办新群学校。这七名发起人还自动义捐,凑足1000元作为开办费用。刘修豑曾任该校教员、校长及湘潭县督学、湘潭县参议员等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致信刘修豑,动员他出外参加革命,刘修豑因故未去。毛泽东复致信嘱他留在县里好好教书,培育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韶山革命烈士李耿侯之弟李介侯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询问刘修豑及其家庭的情况。李介侯因数十年在外经商,对刘修豑家的情况不太清楚,无言以对。
1951年,李介侯回乡省亲,一到韶山,即来到刘修豑家,对其女儿说:“毛主席对你家很关心,要你们写个信交我带去。”当时,刘修豑的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长子刘伯强供职于常德市总工会,次子刘德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5军当兵。刘的女儿请来一位教师,以两个弟弟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全家的情况,并就继续工作还是进学校读书好征求毛主席的意见。
李介侯返京后,将此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即于8月10日复信李介侯:“承你转来刘伯强、刘德三二位的信,收到了,请你转告他们,在当地认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
李介侯将毛泽东的信转给刘伯强兄弟,两人读后,深受感动,他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安心工作和服役,努力学习。后来,刘伯强担任过中共常德市委宣传部部长、政协常德市委员会副主席;刘德三担任过涟源市人民武装部副政委、湘潭地区司法局副局长。
四、关怀汤藻贞及其遗属
1949年5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他的书房,发现办公桌上有一封寄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幼年时的同学、现任北师大代校长的汤藻贞教授写来的。信中叙说他与毛泽东早年同窗共读时的情谊及别后数十年的坎坷经历,并向老同学表示祝贺。毛泽东看了信,十分高兴,立即打电话给汤藻贞,向他表示问候,并问道:“现在北京还有哪些老相识?”
汤藻贞在电话中回答说:“我们在北京的老相识还有:北师大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数学系主任傅仲荪,以及国画家齐白石……”
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
汤藻贞说:“我让他们来看你吧。”
毛泽东忙推辞说:“不要,不要,我去看他们。”
随即,毛泽东驱车来到北京和平门北师大宿舍,看望昔日的师友们。
汤藻贞、黎锦熙、黄国璋、傅仲荪等人闻讯,连忙从家中赶去迎接。师友们相见,分外亲切,喜不胜喜。
毛泽东一见面容清癯的汤藻贞,便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老同学,你好!”见到年过花甲的黎锦熙,便疾步迎上前去,连呼:“黎老师,您好!”黎锦熙满面笑容,连连摆手,说:“不敢,不敢!”
汤藻贞叫家里人弄点湖南特产——腊肉招待毛泽东。毛泽东连忙说:“不麻烦你们了,今天我请客。”马上让工作人员叫来两桌酒席,招待大家。
宾主入席,边吃边谈。他们亲切叙旧,谈笑风生。浓重的乡音,浓郁的乡情,仿佛把他们带回到当年那“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岁月……
汤藻贞(1898—1951)亦作璪真,字孟林,韶山市杨林乡人,生于1898年,早年就读于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与毛泽东同窗共读。青少年时期自长沙至北京,两人过从甚密,交情厚笃。1915年,汤藻贞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即今北师大)数理部,参加过五四学生运动,毕业后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并入北师大)任教。1923年去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及莱比锡大学攻读数学。1926年回国,先后在武昌大学、上海劳动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在白色恐怖下,他同情革命,掩护过共产党员脱险。抗日战争时期,汤执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和广西大学,并在广西大学兼任教务长。抗战胜利后,任安徽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8年回北师大任教,并兼任教务长,一度代理校长。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兼任北师大校务委员会委员。曾主持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工作,任过九三学社中央候补理事兼北京市分社理事。汤藻贞多年从事数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数学家,著作有《绝对微分学》(翻译)、《新几何学》、《群论对量力学的应用》等。
分别数十年,毛泽东与这位老同学相聚,心情格外畅快。
此后,毛泽东致力于国事,日理万机;汤藻贞亦潜心于教学与科研,不遑稍怠。二人尽管很忙,但时常互致问候,偶有书信往来,交情益深。1951年夏,汤赴西南地区参加土改。
不幸的是,汤藻贞因长期致力于教学工作,操劳过度,身体每况愈下,9月回京后即患了急性胰腺炎,卧床不起。在他住院期间,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专程到医院慰问他,劝其安心养病。
1951年10月4日,汤藻贞不幸病逝,终年53岁。毛泽东对这位在数学领域卓有建树的老同学的英年早逝,深感悲痛和惋惜,叹息道:“孟林死得太早啊!这是我们国家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当时任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及《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的傅仲荪,对汤的逝世表示哀悼,信云:
傅先生:
汤先生追悼会需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廿三日
这封信,表达了毛泽东对汤藻贞的怀念及对他所从事的数学事业的肯定。
汤藻贞逝世不久,汤的遗孀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家庭生活困难,说丈夫遽离人世,一家人悲痛欲绝;遗有三女二子,最大的才15岁,最小的刚刚8个月;她本人又是家庭妇女,没有职业,无法谋生,而有关方面又立即停发了她丈夫的薪水。她在信中还说:从明天起,米也没有了,煤也没有了。要求将五个孩子免费入托、入学,并给本人安置工作。
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心情沉重,他用铅笔在信上画了许多横杠,然后把信批给秘书田家英:“请你持此信去看此信的作者一次,并去师大找负责人谈一下。汤教授死了,马上停发薪水,对家又无安置,似不甚妥。办法还是要从师大方面去想,才有出路。”
田家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去北师大慰问了汤藻贞遗下的孤儿寡妇,并询问了其经济来源和生活状况。汤家十分感动。田家英还与学校有关负责同志谈了汤的遗属情况,提出了合理建议。不久,汤的遗孀及其五个孩子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1951年11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在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的李漱清之子李介侯,就汤藻贞遗属生活安排问题答复如下:
介侯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汤藻真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五、为张维尽故人之责
1950年9月19日,毛泽东亲笔复信老朋友张维:
张维兄:
来信收读,甚以为慰。令堂大人八十寿辰,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借致庆贺之忱。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
当时,张维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他是湖南浏阳县人,生于1898年,别名张迈宝,字楚行。他早年在长沙与毛泽东有过较密切的交往。1924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获医学博士学位。担任过长沙伤兵疗养院院长、汉口国民革命军兵站总监部预备医院第一分院院长、第44军第2师医务处长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去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公共卫生学研究生,随后兼任北京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保健课主任。1929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学成回国后,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教授。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山城邂逅老朋友张维。故人相见,甚感亲切,畅叙离别之情。毛泽东曾向张维打听罗哲烈士的遗孀曹云芳及其子女下落。张维告知,曹云芳已去贵阳,并重新组织家庭,已有继子及两个女儿。毛泽东听了方感宽慰。
1949年9月起,张维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担任教授。1950年,张维的母亲年届八十,为祝贺母亲八秩大寿,他特写信给毛泽东,请老朋友题写贺词。毛泽东获信后,欣然复信,并题书一联:
如日之升;
如月之恒。
表达了对故人的思念和对老人的恭敬之情。
张维接到毛泽东的书信及亲笔题联,全家人感激不已。
1957年,张维患病,向毛泽东写信,反映病情及家属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十分惦念,亲笔复信,信云:
张维同志暨张夫人:
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于北京
毛泽东关心故旧、朋友,尽故人应尽之责,于此可见一斑。
张维是新中国的现代公共卫生学家、一级教授,解放后曾任华东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系教授、系主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学教研室主任。1975年逝世,享年77岁。他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为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显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