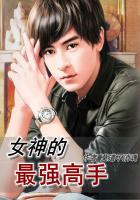问曰:“何为性情?”答曰:“圣人以‘思无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谓也。《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发乎情也。不淫不乱,止乎礼义,性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言此也。此意晋、魏不失,梁陈尽矣。陈拾遗挽之使正,以後淫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杜诗所以独高者,以不违无邪之训耳。”
问曰:“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谢曰:“不佞少时为俗学所忄吴者十年,将至四十,始见唐诗比兴之义;又二十年,方知汉、魏、晋、宋之高妙,而精气销亡,不能构思矣。人之目见者易远,足践者必近,勿相困也。”
问曰:“唐诗六义如何?”答曰:“《风》、《雅》、《颂》各别,比、兴、赋杂出乎其中。後世宗庙之乐章,古之《颂》也。三代之祖先,实有圣德,故不愧乎称扬。汉已後之祖先,知为何人,乐章备礼而已,不足论也。求《雅》于杜诗,不可胜举。而如王昌龄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诸侯。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韦应物之‘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王建为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词》,罗隐之‘静怜贵族谋身易,危觉文皇创业难’,皆二《雅》之遗意也。《风》与《骚》,则全唐之所自出,不可胜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兴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也。‘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赋也。”
朱子尽去旧序,但据经文以为注,使《三百篇》尽出于赋乃可,安得据比兴之词以求远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兴,小则为害于唐体,大则为害于《三百》。
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
诗之失比兴,非细故也。比兴是虚句活句,赋是实句。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许浑诗有力量,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无比兴,说死句也。
明人不知比兴而说唐诗,开口便错。义山之“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言表露试之冶病,可知真伪,讽宪、武之求仙也。白雪楼大诗伯以为宫怨,评曰:“望幸之思怅然。”呵呵!
宋诗率直,失比兴而赋犹存。弘、嘉人诗无文理,并赋亦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