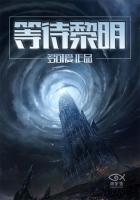却说韩氏闻得忠孝王尚未与刘氏同牀,犹是伴图独宿,心中颇喜,即着女碑取点心出来,令孟嘉龄陪忠孝王同吃。忠孝王曰:“来目拟令刘氏前来请安兼冲喜,或者岳母得以痊安,亦未可定。”韩氏称是。
忠孝王辞别回府。禀明双亲,来日欲令刘氏往孟府冲喜,老王称是。次早刘氏起来梳洗完毕,即便上轿,女婢跟随,来到孟府。家人通报入内,方夫人令开中门迎接,刘氏遵进卧房,见了韩氏,即拜为母,以母女之礼相见。韩氏大喜,即令方氏媳妇请出外厅,只留苏大娘在房内。韩氏细问大娘。方知刘氏夫妻二人,果未同牀。不须臾,筵席已备,方夫人请刘氏入席,直饮至日色斜西方散。刘氏入房,再陪韩氏说了一番言语,方才辞别回府,把孟府相待情形说出,满门欢喜。
韩氏自此以后。日渐沉重,至正月初旬,每到下午,便昏迷不省人事,延至二月初一日,竟昏迷不醒。孟士元满门着急,嘉龄曰:“太侯不能调治。将奈之何?照儿看来,须请郦相来医,或得痊可,亦未可知。”孟士元曰:“果当请郦相方好。”方氏乘势曰::“你父子常说郦相貌似姑娘,待媳妇一看,便知真假。”孟士元曰:“若论容貌﹔明是吾女,但言谈举止,大不相同。况他平目为人端严,从无言笑,官居极品,梁相是他的岳父,权势重大,难以轻言相戏。媳妇少停,亦只为窥视,若妇人出头相见,便是欺侮大臣,罪名非小。”方氏曰:“媳妇非孟浪之徒,怎敢出头露面,不必过虑。”孟嘉龄曰:“不论是男是女,请来救母亲命要紧。”孟士元曰:“正是,我儿当亲自往请,方肯前来。”孟龄称是,即令备下禀折,上马而行,不带执事,只有数名家将跟随。来到相府下马,步入官厅坐下,向门官说明,要求郦相往救母性命。门官通报入内,孟嘉龄恐郦相不往,母亲性命不保,即步出官厅来到穿堂,来听消息。事有凑巧,恰遇荣发有事,正要出来,遥见孟公子吃了一惊,慌忙躲在大门之后,不料孟嘉龄早已认是荣兰,恰遇一个家人在此经过,孟嘉龄指荣发问曰:“那个大叔唤甚么名字?”家人抬头一看,答曰:“这个名叫荣发,乃是郦相的心腹堂官。”孟嘉龄知道必是荣兰改名,遂不再问。
且说郦相方才因百官来贺朔望、送客完毕,方始回后,与素华吃些点心。女婢拿了禀帖,报称翰林院孟学士特来请太师医治伊母病症,必要求太师面见,郦相恐其诈词,即向女婢曰:“可令家人对孟公子说,前日医治太后乃偶尔凑巧,今太夫人病重,须请名医。吾虽则略知脉理,不能医治沉病,何敢领命。”女婢退出,将此言告诉门官,门官转向孟嘉龄说过,嘉龄着急曰:“烦你再报,务请郦丞相出来﹔我有话面议。”门官只得入报与女婢,女婢再报入内曰:“孟学士要求求相出见,有话面禀。”郦相曰:“既如此,请孟学士在书房少待,吾即出来相见。”女婢领命退出。
素华曰:“耳闻令堂大人自上年起病,至今莫非沉重?故公子十分着急。”郦相曰:“家母尚在壮年,即使有病,谅不至十分危险。家父家兄岂是不认得我?只因我行动言语比前不同,故得稍释其疑惑。但平日间我从不与人言笑,故不敢相认。我今若往视脉,恐家母自侍女流,诈称病重,有意乱言,必扯我相认。即欲责他不是,而病狂乱言,亦难见怪。此去必定露出马脚。”素华曰:“谅亦未必。”郦相曰:“姊姊虽如此说,想母亲心中必怪我不孝。且你有所不知,倘一朝相认,即日便有失脸之祸。”素华曰:“如果相认,老爷与夫人当为你遮掩,焉有漏泄之理。”郦相曰:“今且不要争论,随后姊姊自知。”言罢,就换上公服,来到槐竹轩。
孟嘉龄起身迎接,郦相以宾主礼叙坐。嘉龄推辞曰:“卑职怎敢偕坐。”即坐在旁边,遂把母亲垂危,待请老太师相救话说明。郦相恐其诈词,乃曰:“下官年轻,习学有限。太夫人既然病重,当请名医救治,下官不敢前去误事。”孟嘉龄恳求曰:“名医俱已请过,皆是无能救治,故特来请恩相,若不肯前往,家母性命难保,恳求恩相前去救命。”说完连忙跪下。郦相不忍,即扶起曰:“年兄如此过扎,下官何以敢当。”嘉龄曰:“为救老母,理当百拜。”郦相曰:“年兄请回,下官即便前往。”孟嘉龄称谢,出府上马而去。
郦相急令备轿,一面入内。素华曰:“令兄如此着急,太夫人定是病重。小姐速往为妙。”哪相曰:“家兄这等慌张,我自当速往。只是下次再往,必然败露,你方知我有先见之明。”说罢,出衙上轿,前呼后拥,即便起身。
孟嘉龄恐郦相随后便到,急忙回衙。孟士元间曰:“我儿为何许久方回?”嘉龄说明前情,道:“今随后便来。”士元大喜,令女婢速速打扫卧房,烧起好香,对女婢曰:“丞相若到,他乃元宰,你等务必回避。若被遇见女婢,即是侮辱大臣,获罪不小。”又对媳妇曰:“你只好窥探,不可出头。”方氏称是。一时父子忙乱,嘉龄不及说遇见荣兰之事。
须臾间,听得鸣锣开道之声,门役执帖超上前禀曰:“郦相驾到。”孟嘉龄忙令开了中门,喝叫众婢躲避,不许东窃西探、孟士元急穿上公服。奔出大堂,直至滴水檐前站住。仪仗已到,嘉龄奔到轿前,拓躬曰:“卑职不知老太师姻此快驾到,有失远迎,望乞恕罪。”郦相当即伸出右手,向外一拦,道:“下官怎敢劳年兄远接,何以克当。”嘉龄连称不敢,随在轿边,步入后堂,扶了郦相下轿。孟士元早巳降阶迎接曰:“拙内患病垂危,烦劳老太师下轿,何以消受。”郦相约:“下官才疏学浅,多蒙令郎宠召,不得不来。不知尊夫人病势若何?愿其荚详。”士元尊其上坐。郦相不从曰:“老先生乃是前辈,下官恰是后生。行宾席礼已属过份,怎好偕座?”孟士元只得宾主叙坐。嘉龄偏坐在旁。
献茶毕,郦相曰:“夫人病情目下可减轻否?”士元曰:“拙荆病情只是长吁短叹,以前每上午颇有精神。至下午即发热昏晕,不省人事,近日连上午亦昏迷不省,更加沉重。太医速手无法,不能救治,故劳动老太师精神。”郦相曰:“据老先生说来,这令夫人之病是忧思所致。”士元曰:“正是。谚云:‘心病须将心药医’,难怪不能医治。”郦相知是调戏的言语。乃曰:“照此看来,莫非老先生在外边娶了如意夫人﹔故太夫人郁成这病么?”孟士元闻言,暗想我好痴呆,一向只疑郦相定是吾女改装,怎么与我调笑?看来实非吾女。即笑答曰:“老夫素来诚实,并无外遇,拙内向亦深信。”郭相曰:“下官因闻老先生言及尊夫人的病势,此乃伤了七情所致,故出此言。”士元曰:“只因小女无踪,朝思夕念,故得这病。”郦相曰:“下官曾在敝门下的家中见过令爱的形图,有此才貌,怪不得令夫人思念不置。只是令爱画图上诗句明要改易男囊,求取功名。语云:‘有志者,事竟成。’先生可在男子中寻访,就可相会,决不在女子内。今场期在即,老先生可谋为总教?或得与令爱相会,亦未可知。”孟士元寻思,郦相若果是女儿,怎说此话?岂不自泄根由?乃答曰:“郦相所言有理。”嘉龄向前曰:“请郦相入内诊脉。”士元谦逊,郦相先行,自已随后,嘉龄向前引道。
来到房前,父子揭开门帘,恭请郦相入内,移椅坐下。茶毕,孟嘉龄又移椅放在牀前,请郦相坐下,自己拱身入帐内,牵母的左手出张外,与搏相诊脉。郦相见母的手只存一把骨和一重皮,消瘦不堪,情知病重,心实伤感,自料嫂嫂必在旁窥探,不敢忧愁感形于面。用心看过左右酌脉,点头曰:“果是忧愁致病,然病势虽重,命却亦无妨。”士元父子闻言,略得安心。
郦相起身坐在桌前,陶孟士元曰:“尊夫人此病虽不致伤命,然血衰气短,着再忧愁,恐留连牀褥,病根难脱,久之变成疲疾,遂难医治了。”士元曰:“今当劳动老太师精神,若得全愈,感恩不浅。”郦相谦逊曰:“老先生说哪里话来,下官当自用心。”暗想,再来此处﹔必然败露,今当派二剂药方,作两天服下,病就愈了大半,那时别换医生治之容易,自己好推托不来。主意已定,即用心派药。忽闻女婢在外边叫曰:“启上老爷,韩大人前来探病,轿已到门。”士元谓嘉龄曰:“你可引到后衙坐下,令贤媳陪伴。”嘉龄领命退出。郦相开了二剂药方,又写了日期,向士元曰:“头一剂立即煎服,服后若加精神,可得安眠,便是奏效,次早可服这第二剂药,病便可好了大半,即可别请医生。倘首剂服下,精神仍是昏倦,睡梦不宁,便是我的差错,第二剂药方切不可再服,当换名医救治要紧。”孟士元曰:“郦相下药,岂有差错之理。”郦相曰:“医生下药,或脉理差错,或药不对症,岂有不换医生之理。”即辞别起身。士元曰:“候另日稍暇,当备薄酌奉敬。”郦相曰:“后会有期。”即上轿而去。孟士元忙令家人照单配药煎汤。
须臾,韩大人入房探病﹔辞别回去。方氏曰:“我方才躲在屏后窥探,正是姑娘,此前年娇艳多了。公公怎不就认?”孟士元曰:“若是女儿,怎么与我说笑?”方氏曰:“恰是令人不明。”嘉龄曰:“我还有一事疑心。就说遇着荣兰改名荣发之事,方才因在匆忙之际,未及言明。”方氏曰:“如此说来,必是姑娘,恐公公盘诘,故匆匆回去。”士元曰:“你们休要乱道,若果是女,梁小姐嫁他日久,怎无一言吶?”孟嘉龄夫妻乃省悟曰:“照此想来,果然不是妹子。待来日可令赵寿往寻堂官荣发,便知真假。”士元称是,即叫赵寿前来﹔嘉龄说明遇着荣发等情,道:“你来日可到相府寻访你妹子。”赵寿欢喜曰:“来日即往寻访。”此时药己煎好,韩夫人尚是昏睡,即扶起,士元将药与他吃完睡去,将被褥盖好。
郦相回府入内,荣发即请入书房﹔细把遇着公子,躲避门后的事情言明:“看来公子业已看破,如何是好?”郦相曰:“你这不中用的东西,莫道你是相府的堂官,就是相府的一只狗,亦何人敢欺你。方牙若昂然出去,公子只道面容相似,怎敢动问?今已露出了马脚,从今以后,你若出去,必误我的事,我便把你活活打死。少停老爷必使你兄前来探你,你可速去吩附众把门人,说若有人来寻我,只说荣发午间已往江南公干,归期难定。”荣发退出,吩咐众门官不许泄漏,即回来察明。
郦相入内来见素华,说明母亲的病沉重,十分伤感,但我这二剂药服之,病可好了大半。后说及与父亲调笑话,连家父亦不敢疑我是女。素华笑曰:“小姐好伎俩,令人难测。”郦相曰:“可恨荣兰贱婢,已露出马脚。”便将荣发的事说明。又对素华曰:“下次再去,家母服这两剂药病已好了。精神既复,必认得我﹔又倚着有病,且侍女流,只恐弄出破绽。我来夜即宿内阁,诈称办案,过了数日方回,家父等得不耐烦,必定别换医生,我方安静无事。”素华曰:“说得极是。”
且说韩夫人睡到下午,苏醒曰:“今气已不喘,身体爽快了许多。不知何人的药方,如此效验?”孟士元曰:“我见你病重,早间令孩儿恳求郦相前来医治。”韩夫人随向媳妇曰:“你可窥见是女儿么?”方氏道:“我躲在屏后偷看,正是姑娘。”孟嘉龄又说遇过荣兰,令赵寿来日往问,便知备细。韩氏曰:“因何不唤我醒来细看?”方氏曰:“婆婆方才昏迷过甚,如何叫得苏醒。”韩氏叹曰:“可恨一时昏睡,若我苏醒,早已相认了。但不知哪里学习医道,胜过太医。”孟士元曰:“若是女儿,怎么与我说笑?”遂把说笑之言陈明:“况梁小姐结婚,焉能相得?事属可疑。他官居极品,倘一旦面奏主上,这欺侮大臣的罪名恰难顶当。”嘉龄曰:“孩儿已想出一个妙计,未识可行与否?”士元曰:“你且说来。”嘉龄道:“母亲来日接服第二帖药,身体必更加健旺。初三早孩儿再去请求,候他诊脉之时,母亲佯在沉重病状,将他拖住,声声呼唤女儿,任他多大本领,必要露出马脚。若有变更,母亲可和了被头,跌下地来,诈作晕绝,孩儿便抱住啼哭,爹爹亦拖住啼哭,遮住母亲的面容,不怕他还不相认。即便非妹子,变脸奏闻天子,母亲乃是女流之辈,且又是病狂,朝廷亦难责罪,岂不是好。”士元大喜:“孩儿这个计极妙,即不是女儿,而病中狂呼乱语,他亦难认真变脸。贤妻当依计行,必定露出破绽。”韩氏大喜,病亦好了三分。
到了次早,赵寿巴不得要会妹子,即来到相府,见了门官乃作礼曰:“小可乃是堂官荣发的乡亲,烦请荣发出来,有话面说。”岁门官曰:“荣发奉相爷差遣,往江南公干去了。”赵寿曰:“昨早还有人遇见,怎说往江南出差?”门官曰:“昨午方才起身。”赵寿闻言,沉吟一会,问曰:“几时方回?”阿官曰:“出差怎定归期。”赵寿只得回复孟士元父子。
未知后来如何相认,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