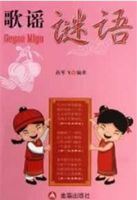三 如此圣洁
如果说,爱情生活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状况的重要尺度,那么,爱情叙事则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品质的重要尺度。在当下的大陆小说作品中,不缺乏“身体叙事”,不缺乏“欲望化书写”,但却很少看到美好的爱情。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巨流河》,却给读者讲了一个至纯至美的爱情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可爱亲切的民族英雄。
在谈论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齐邦媛甚至不能接受用“恋爱”这个热烈的词,而宁愿用“钟情”这个相对内敛的词。她说:自己与张大飞的感情,“在今天来说很难称为恋爱。对我来说,是一种钟情。‘钟情’这两个字在现在当然是很过时的了,可是那个时代,第一见面很难,第二也有很多的顾虑,不是像今天这样交通便利。所以回忆当年就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诚恳,那种钟情因是一生只有一次。人家那么轰轰烈烈的生和死,我很怕别人拿来亵渎,那样亵渎的话,会很对不起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了维护那份“钟情”的圣洁性,齐邦媛拒绝将它改编成电影。有很多导演找到了她。他们甚至做了“一些计划”。但是,“我发现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方式。所以我就公开地说了,在我有生之年不拍电影,我希望我的书先站稳,保持自己的价值。”其实,更内在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害怕亵渎了自己的情感,害怕亵渎了逝者的尊严:“他们一定要把张大飞那个感情写成一个热烈的爱情,因为不这样做电影就不能卖。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二十六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
齐邦媛的叙事上的含蓄和克制,首先表现在她对自己的“爱情故事”的分散化处理上。像这样终生难忘的情感记忆,集中在一个叙事单元,酣畅淋漓地讲述出来,无疑更有助于获得强烈的叙事效果。但是,也许害怕过于热烈的表达,会亵渎那本来就纯净而庄严的情感,齐邦媛便选择了一种更自然的叙事策略,那就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过程,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片段式地呈现在次第展开的章节里,仿佛一条小路,在铺满鲜花的原野上,曲曲折折,忽隐忽现地通向远方。
他们之间的“钟情”,开始于齐邦媛12岁那年。家破人亡、失去家园的张大非(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空军后,改名“张大飞”),常常来齐邦媛家做客,因为,父母经常会在家里招待那些来自东北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名叫牛首山的小山。齐邦媛因为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
然而,平静安闲的和平生活结束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在战斗的间隙,张大飞与齐邦媛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天上的来信”,见证着一个优秀青年为国征战的历程,也反映着他可爱的性格和纯洁的心灵: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
爱情最有韵致的阶段,是在它还不能被称作“爱情”的时候,就像花儿最妩媚的时候,是在它尚未完全绽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彼此见面所说的,也许都是题外的话,都是不相干的话,但那些看似与情感无关的话,其实已经是情话了,——它无疑是最浅最淡的那种,但也是最深最浓的那种,就像最轻最薄的羽毛,往往会飞得最高最远一样: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
江淹在《别赋》里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寻常意义上的分别,已足以让人依依不舍,爱情故事中的永别,就更加令人柔肠寸断。在《巨流河》里,升空作战的张大飞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每一次分手,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依然显得那么克制,依然表现得那么含蓄: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
“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句话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表层,是从哥哥的角度说出的,包含着对小妹妹的成长之快的欣喜,深层,则传达出含着爱意的惊讶,是一句含蓄而又热烈的爱的语言,难怪“我”会把它当做“赞美”,难怪“我”说自己对当时的“心情”,是“忘不了的”。在上引的这段叙述语言里,作者的节奏,是缓慢的,在“我必须走了”之后,写“我”见“他”离去记忆的一句话,则断为四顿,别为两句,仿佛低沉、舒缓的慢板,蕴藉婉转,意味深长。而“一九四三春风远矣”一句,更是语意古雅,耐人寻味:春风虽远,但温暖仍在,记忆永在!
《巨流河》的爱情故事之所以令人震撼,之所以令人觉得美好,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包含着神圣和庄严的宗教情感。虽然爱情,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美好的充满诗意性的,但是,只有当它充满克己利他的牺牲精神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是真正高尚和伟大的。《巨流河》里的爱情,就具有慈悲的情怀、利他的精神和圣洁的宗教色彩。
张大飞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好斗成性的戾气,没有一丝一毫舍我其谁的傲慢;由于天性的善良和对悲苦的敏感,他本来最适合做一个济世利物的行善者,然而,他却不幸生活在一个乱世,不得不参加抵御外侮的战争,不得不做与自己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事情。他的慷慨赴国难的英雄行为,固然令人感念和钦佩,但是,他对生活和爱情的庄严而纯洁的态度,却更加令人感动和尊敬。虽然不幸生活在一个战争年代,虽然他不得不通过暴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有信仰的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家破人亡之际,他将《圣经》当做他“唯一的依靠”。他的爱情与他对上帝的爱,是融为一体的。他把一本“和自己的那本一模一样的《圣经》”送给了齐邦媛。他把爱情和对上帝的爱,一同带给了自己所爱的人。他对“邦媛妹妹”的“祝福”——“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每一个字句里,都充满了宗教的温暖和柔情。
二十六岁的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掩护友机时,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这给齐邦媛带来巨大的痛苦,直到抗战胜利后,她仍然难以摆脱。最终,她终于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这种严肃的纪念方式,赋予了他们的感情以神圣的性质,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哪里有信仰,哪里就有奇迹;哪里有纯粹的爱情,哪里就有神奇的相遇。齐邦媛竟然意外地在南京新街口的教堂前,看到了悬挂在那里的“纪念张大飞殉国一周年”的横幅。横幅上的字,让她心如刀绞,也让她觉得神秘不解:“在雨中,我痴立街头,不知应不应该进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不到十天之前,我刚刚意外地飞越万里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见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圣经》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齐邦媛相信这样的“定期”,相信这样的“定时”。所以,这样的“寻找”和“相遇”,并未结束。七十五岁那年,在五月温暖的阳光里,她终于来到了南京,来到刻有张大飞名字的“航空烈士公墓”。在这次的“重逢”里,作者再次获得了宗教性的启示,明白了《传道书》里“舍弃有时”的象征,而对于所“钟情”过的人,她也再次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和赞美之意:“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巨流河》是一部见证历史的书,是一部抒发漂泊之感的书,是一部赞美温良德性的书,更是一部印证“爱情”的书。因为有生离死别,因为有深哀巨痛,所以,它的笔调,难免染着感伤的色彩,叙事的语调里,也难免含着些微的悲凉,但是,从它的字句之间,你却读不到一丝一毫的消沉和颓唐,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戾气和怨毒。它没有一句爱国主义的高调,却深切地表达了对父母之邦无边的眷恋和至诚的热爱;它无意制造浪漫,但却在平静而敛抑的追怀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浪漫而圣洁的爱情故事。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这是《巨流河》曲终奏雅的最后一句话。
“一切美好的,都将在永恒的平静里不朽;一切仁慈的,都将在永恒的平静里长存。”这是我从《巨流河》读到的更为深刻的昭示。
2011年11月28日,北京平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