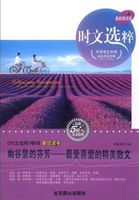文学和科学都不能离开想象,特别是创造性的想象。只是文学的想象是形象的“臆测”,而科学的想象,则是一种抽象的推理;文学的想象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而科学的想象则是排除了感情的,像马克思所说的,是在“纯粹形态”中进行的。科学的想象的特点是严密地概念化的,它的完备形态建立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它的最高生命是货真价实地公式化的,而公式化则可能造成文学种族绝灭的危机。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就这样的区别作过细的分析。本文的任务是进一步提出问题:在文学的想象中,诗的想象又有什么特殊的规律?作者在本文中努力避免作纯概念的演绎,着重就自己所掌握、所涉猎的材料,加以归纳,力图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把具体分析的方法与抽象概括的方法结合起来。
一、诗歌想象的变形律
诗,是反映客观生活的;诗,又是抒发主观感情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想象把二者结合起来。诗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诗就可能失去存在的根据,退化为散文。
达.芬奇说,“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这心灵的镜子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并不等同于生活的原貌,达.芬奇把它叫做“第二自然”。心灵,可以说是感情的发生器、储存器和共鸣器。在这感情发生器中折射出来的生活和无生命没有感情的平面镜是不相同的。在心灵的镜子中的“第二自然”,是诗人的感情特征和生活特征的化合物。一个人是否有诗的才华,就要看他是否善于把生活与感情、客观与主观作奇妙的别出心裁的化合。在现实情况下,有形的生活与无形的感情是很难化合的,只有在想象的作用下,生活和感情才能化合为“第二自然”。正因为这样,想象才被西方许多作家、诗人当作是诗人的特殊才华的标志。
1920年1月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说:
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
把神思飞扬的心灵比作波浪起伏的潮水,这比西方古典文艺理论把它比作镜子要确切多了。自然,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是郭沫若的发明,我国哲学史上,从梁五经博士贺瑒到宋代的程顾都把平静的心情比作水,把感情比作波浪。郭沫若当年曾经醉心于这一派的哲学,不过顺便把它用于文艺罢了。
心灵的镜子是感情的镜子,它是有波浪的,它是不平的,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是变异了的。诗,正是以这种变异了的生活形态,以其异于生活原型的情状和色调,以其比生活原型深邃得多的内涵给读者以惊异、陶醉和启迪。想象,总是出乎意外地把读者带进一个变幻着的神妙境界,正因为这样,追求形似在苏东坡看来,是小孩子一样幼稚可笑的,而那咏物诗中“极镂绘之工”的一类,在王夫之看来是“匠气”的表现。也许,他看那些作品正像我们看某些商品广告画一样感到俗不可耐。
诗,不能像散文那样,仅仅以描摹生活的现实图景为自己的任务,它的优越性在现实的描摹中不能充分发挥。黑格尔认为,诗歌要“摆脱”“散文性现实情况,凭主体的独立想象,去创造出一种内心情感和思想的诗性的世界”。
希罗多德《历史》第七卷载,希腊人抵御波斯入侵。托莫庇来关口是波斯入侵必经之要塞。三百名守卫的斯巴达人英勇不屈,寡不敌众,全部阵亡。希腊诗人西门尼德斯替他们写了一个墓志铭。诗人并没有用散文写实的方法描摹三百烈士英勇献身的图景,而是展开了想象,表现他们似乎并没有死亡:过路人,请传句话给斯巴达人,为了听他们的嘱咐,我们躺在这里。这里写的好像不完全忠实于生活,但是它却更忠实于感情。它的真实是生活的客观形态特征(死亡,躺在大地上)和感情的主观愿望特征(为国献身,永生)在一个交点上的会合(睡眠)。这里既有生活的因素,又有感情的因素,二者自然会合以后,就既不完全是客观的原貌,也不完全是主观的狂想,而是一种奇妙的想象。这里有死亡的特征(躺着),也有永生的特征(听觉仍然在起作用的睡眠,这自然不是现实的生活图景,它是来自于现实,又经过感情的改造的变异形态。
通过想象,生活好像重新投胎一样,获得另一种形态和性状。它失去生活原型的一部分性状,它获得了感情的特征。生活的形象,在想象中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异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规律。这一点也正是诗歌形象的想象性与其他文学形象的想象性能分化的开始。
想象的变异,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冲破描绘对象的外在形态。司空图说:“遗形得似,庶几斯人。”这说明,不拘外形相似,也就是敢于在外形上有变幻,是很少人能达到的境界。雪莱在总结他那个时代的诗歌形象的规律时说,“诗使它能触及的一切变形”。在这方面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理论家赫斯列特说得相当勇敢。他在《泛论诗歌》中说:“想象是这样一种机能,它不按事物的本相表现事物,而是按照其他的思想情绪把事物揉成无穷的不同的形态和力量的综合来表现它们。这种语言不因为与事实有出入而不忠于自然;如果它能传达出事物在激情的影响下,在心灵中产生的印象,它便是更为忠实和自然的语言了。比如在激动或恐怖的心境中,感官觉察了事物——想象就会歪曲或夸大这些事物,使之成为最能助长恐怖的形状,‘我们的眼睛’被其他的官能‘所愚弄’,这是想象的普遍规律。”比赫斯列特早差不多一个世纪,中国清代的诗论家吴乔,在《答万季野诗问》中更为准确、更为生动地谈到了诗歌形象的特点问题:“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日:‘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裁词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这样明确地把诗歌形象的变形和变质作为一种普遍规律肯定下来,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是第一次。它突破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中形与神对立统一的范畴,提出了形与质对立统一的范畴,这就把诗歌形象的想象性能进一步触动了。很可惜这个为《四库全书》总目所重视的观点,在他的《围炉诗话》中并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到了西欧浪漫主义诗歌衰亡之后,诗人马拉美提出了“诗是舞蹈,散文是散步”的说法,与吴乔的诗酒文饭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歌形象的变异是一种规律,当然,像任何规律一样并不是绝对无条件的。因为诗歌中也不乏白描的手段。而且,在诗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每当想象的形象脱离生活成为一种倾向时,白描的手法常常还能为诗歌带来新的生命,为诗歌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途。像汉魏乐府,陶渊明的大部分诗作,“五四”初期的白话诗作就曾起过这样的历史作用。但是变异的想象性的意象,无疑在整个诗歌中占据相当的优势,而且这种意象变幻的规律,较之白描手法有更大的重要性。正是这种意象变幻使诗与散文划清了最后的界限。在诗歌史上每当诗歌的领域遭受散文的侵犯,诗为大量现实图景描绘所困的时候,想象形象的变幻,常常使诗歌艺术发生划时代的跃进。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屈原的出现,他以一整套崭新的想象性的形象,一整套象征的形象体系突破了《诗经》的写实手法和比较简单的幻想,把我国古典诗歌艺术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明显的莫过于郭沫若和闻一多、戴望舒的出现,是他们把新诗从生活现象的罗列和情感直抒,提到艺术想象的境界,为新诗艺术拓开了广阔的天地。全部诗歌历史证明,诗歌艺术的发展,常常与想像力的发展分不开,而想像力的发展又常常与想象变幻生活原型的新趋向、新时尚、新特点分不开。诗歌史上新的流派、新的风格常常带来了想象形象新的变幻。
如果诗歌只能白描,只能准确地捕捉客观生活的特征,那么,作为二种抒情文学,它所获得的自由还是相当有限的,而且这种有限的自由中,还有一部分是近乎散文的自由,还不完全是诗歌艺术本身所将有的自由。光会写“心事数茎白发”,而不敢写“白发三千丈”,诗歌艺术的本质还不能充分显示出来。光会描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不善于将形象变幻,使之含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诗歌艺术的优越性还不能充分发挥。同样一个对象,用纯白描的方式描绘出来,和以想象的变异手法抒写出来,二者的艺术效果是并不一样的。苏东坡和他的朋友章质夫都以扬花为题材写了《水龙吟》进行唱和。章质夫的如下:
燕忙鸳懒花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阔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入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苏东坡的如下: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两首词都是表现思念远离家乡的丈夫的贵族妇女的伤感情绪,感叹青春像杨花一样地消逝。章质夫对杨花形态的描摹可谓曲尽其妙,其中还有些前人所未曾达到的那种微妙之处。但是,他基本上用的是写实的手法,在他笔下,杨花始终是扬花,他不敢突破杨花的固有形态,不敢让它发生变异,他只是在杨花固有形态的范围内施展他的华彩的语言功夫。而在苏东坡笔下,杨花带上了更强烈的色彩,它不完全是现实中杨花那个本来的样子了,苏东坡一开始就这样写:“似花还似非花”,又是杨花,又不是扬花。到最后,则干脆宣称:“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扬花变异了,变成了眼泪,客观的对象变成了主观的感情,这种变异只有在想象中才是合理的。苏东坡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想象大大超过了章质夫。而这种勇敢地突破事物原始形态的想象,正是构成诗人才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诗人的想象不同于科学家的想象之处。科学的想象以客观的准确性为原则,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没有以主观感情通过想象去使客观对象发生变异的权利。而这也正是诗歌的想象不同于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之处。小说、戏剧(一部分散文)中也有想象的虚构,但是,除了神话、童话、科学幻想小说以外,事情的内在联系、因果关系、逻辑关系是作者突破真人真事重新虚构的,但是事情、人物本身的动作、语言则都只能是现实的。小说家、戏剧家的想像力在于从一个动作,一句话,一个习惯,乃至一次微笑中,看出这是该人物全都性格、环境的一次暴露。而诗人却可以把这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微笑,一个习惯变成另一种形态,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感情。